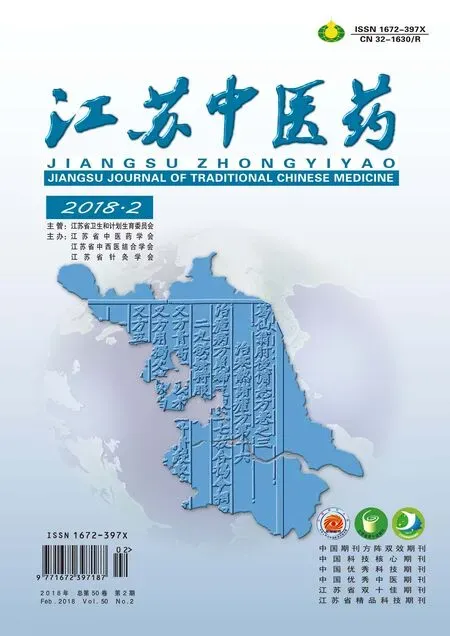虛不受補芻議
熊乙霓 郭 旭 陳明明
(遂寧市中醫院腫瘤科,四川遂寧629000)
現代人生活節奏較快,環境及飲食污染較重,生活方式不良,使許多人身心處于亞健康狀態,出現疲憊、失眠、乏力、情緒低落、納差等癥狀,這些都是體虛的表現。又由于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民眾對健康要求的提高,出現了濫用人參、冬蟲夏草、阿膠等補益藥的風氣,辨證不準,補不得法,非但達不到補虛扶正之目的,反而導致一些不良反應,如流鼻血、便秘、腹脹、痤瘡等。“虛則補之”是中醫的基本治則,但在臨床上,我們越來越多的發現以上“虛不受補”的情況。
“虛不受補”最早見于清·陳士鐸《本草新編·十劑論》,他說:“或疑需用補劑,是虛病宜于補也。然往往有愈補愈虛者,豈補劑之未可全恃乎……補中而增消導之品,補內而用制伏之法,不必全補而補之,更佳也。”即虛證之人,在給予補益藥之后,非但未達到補虛目的,反而加重病情,其原因是患者機體功能不全,對于大補滋膩之品不能受納運化和吸收,發揮藥效,反而壅滯于體內,阻礙氣機,加重機體負擔。清·吳鞠通撰寫的《俗傳虛不受補論》一文提到:“俗傳虛不受補,便束手無策,以為可告無愧。蓋曰非我之不會補,彼不受也。不知虛不受補之癥有三:一者濕熱盤踞中焦,二者肝木橫穿土位,三者前醫誤用呆膩閉塞胃氣、苦寒傷殘胃陽等弊。濕熱者,宣其濕而即受補;肝木橫者,宣肝絡,使不克土即受補;誤傷胃氣者,先和胃氣即受補矣。和胃有陰陽之別、寒熱之分。胃陽受傷,和以橘皮、半夏之類;胃陰受傷,和以鮮果汁、甘涼藥品之類。隨癥類推,惟胃氣絕者不受補,則不可救矣。”筆者在溫習古代醫家文獻基礎上結合臨床,探討如下。
1 虛實夾雜,宜消補兼施
吳鞠通已指出,脾胃虛弱日久,運化失常,氣機升降失調,易造成濕熱內生,盤踞中焦。濕熱之邪,其性重濁粘膩,當宣其濕,去其熱,若一味給予補益滋膩之藥,久虛之脾胃無法有效攝納、吸收、利用,導致補益之藥沉積于中焦,阻礙脾胃氣機升降,加重濕熱壅滯,致使脾胃更虛。同理可推,對于多病久虛之人,多虛實夾雜,不僅濕熱夾雜,還常與外邪、痰濁、瘀血、食積夾雜,故治療當辨證論治根據實際情況,結合化瘀、活血、消積等,消補兼施,切忌一味補益,防止閉門留寇,病程纏綿難愈。《證治準繩》中健脾丸健脾和胃、消食止瀉,方中人參、山藥補益脾氣,白術、茯苓健脾滲濕,再少予黃連清熱燥濕,全方補重于消,消補兼施,補而不滯,消而不傷正。
2 肝木乘脾,當先疏肝絡
“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即病在肝臟,肝失疏泄,臟腑氣機失調,影響脾胃的運化功能,脾胃無法正常運化水液、食物,即導致飲食水谷的攝納、運化、吸收和轉輸出現障礙,即會在肝病基礎上,表現出脾虛癥狀,如腹部脹滿、納差、乏力、便溏等,因此治療時,若投補益之品,藥物壅滯中焦,反而會加重阻礙肝臟之疏泄及脾胃的運化,使病情加重。治療上當疏肝絡,予逍遙散等加減,使得肝氣條達舒暢,心情愉悅,其中柴胡疏肝解郁,使肝氣得以調達;白芍酸苦微寒,柔肝緩急;薄荷少許,疏肝郁結之氣;白術、茯苓、甘草健脾益氣。諸藥合用,使肝郁得疏,血虛得養,脾弱得復,有助于進一步治療[1]。
3 真實假虛,切勿投補益
真實假虛者在臨床上較常見,大實時表現出虛弱的假象,如熱結旁流者,邪熱積聚于腸胃,腹滿硬痛,邪熱無出路,逼迫大腸,瀉下臭穢稀水;小兒食積性腹瀉、婦女瘀血內阻而出現的崩漏下血者皆為真實假虛,且病因只有邪實,即“大實有羸狀,誤補益疾”,故忌予補益之藥,否則犯了虛虛實實之戒,如火上澆油,使邪氣更盛,導致病情快速惡化[2]。故在辨證之初,首當準確辨明是虛證還是實證,勿投補益,否則導致病情惡化,甚至危及生命。
4 脾胃閉塞,應和胃健脾
吳鞠通認為若接診患者,已因前醫一味用滋膩柔潤之品,阻礙脾胃運化,導致脾胃虛弱,或者本為脾胃久虛之人,因前醫辨證不夠全面,誤投滋膩之品,加重閉塞,影響脾胃氣機升降,加重脾虛。此時用藥,基于滋陰之品膩膈礙胃,需糾正前醫用藥之弊,酌加理氣和胃健脾香燥之品,減少脾胃負擔,靈活變通,隨癥加減,務使補氣不壅中,養陰不礙胃,才能補而得效。如一貫煎中集生地黃、北沙參、麥門冬、枸杞子一派滋潤之品,配以少量川楝子,性雖苦燥,然于大量的甘寒養陰藥中,則不嫌其傷津,反借其疏泄肝氣,調和胃氣,以消中壅之弊而為通利之用[3]。
5 結語
綜上,臨床上診治虛證,當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全面分析,而非見虛即補,妄投補益滋膩之劑,避免發生“虛不受補”的情況。“虛則補之”是中醫的基本治則,但補虛也應得法,才能達到滿意療效。
[1] 王永譽,王浩,方堅.“虛不受補”之辨證論治[J].新中醫,2016,48(5):1.
[2] 李智煜.基于中醫傳統理論探討“虛不受補”內在理論[J].光明中醫,2016,31(2):176.
[3] 張華津.淺析虛不受補[J].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29(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