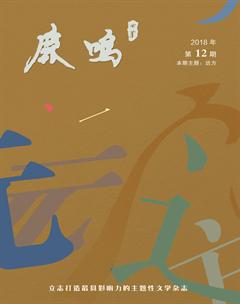寄居和平里
蔡曉安
雪中的斷裂
筆直的大樹
以轟然倒下的
折斷的身軀
發出
沉重而堅實的嘆息
透過細密的窗紗和模糊的玻璃,正好可以看到那棵筆直的大樹。它的葉子已經開始泛黃,風吹過來,嘩嘩啦啦地在空中搖擺。一部分依然頑強地擁抱著枝干,另一部分終于無奈地飄落。但是,生者和逝者都在努力地抗爭,直至最后一刻。它們的目光深情地相互碰撞,它們緊挽的手臂緩緩脫離。呼呼的北風中,它們在唱著只有同伴才能聽懂的歌。而那堅挺的軀干和皴裂的枝柯,就像一只擎天的手!在夜幕和寒冷的侵襲下,總是在掙扎,想要抓住些什么。我看不見它的根,但我分明就能感覺到,它們正在地底下,慢慢地茁壯,無限地延伸……
從我搬進和平里這間出租屋的第一天,我就被這棵樹深深地吸引,深深地感動著。它讓我想起了我的少年時光。
那時候,我租賃的小屋外面,也有這樣的一棵大樹。每天,我從樹下經過。它默默地站在那里,從不開口。我去上學,它目送我漸漸離去;我從學校回來,遠遠就看見了它的恭迎。它像一個忠厚持重的老仆,更像守護在我身旁的親人。它聽我歡歌,看我落淚。它見證了我奮發的歷程,也目睹了我最初的愛情。
現在,當我看著眼前的這棵樹,我才知道,原來它早已在我的心中默默地扎根了十余年。可是,這扎根了十余年的大樹,卻在2003年的第一場雪中,被迫改寫了自己的歷史。
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樣收拾完畢,準備出門趕往方莊的出版社上班。腳剛踏出門,一股冷風就灌進了衣領。眼前一片銀白。小區的屋頂,圍墻的墻沿,近處的幾輛小車,遠處的各種招牌,凡是目力所及的地方,到處都蓋滿了厚厚的積雪。后來看了報道才知道,這是近幾年北京入冬下得最早,同期內也下得最大的一場雪。
在這幢樓不足十米的地方,就是那棵大樹一直堅挺的位置。我不知道它昨夜遭受了怎樣殘暴的蹂躪。我只看見昨天還剛健高聳的它,現在只剩了小半截身子。它的撕裂的傷口上,也早已墊上了雪。它的身旁,曾經與它血肉相聯的部分,靜靜地躺著,在白雪的覆蓋下,似乎還在瑟瑟地抖動。在它的周圍,幾個工人緩慢地揮動鐵鏟,然而,這遲到的救援于它終歸是沒有任何的幫助了。
一夜的大雪封鎖了很多條馬路,到單位的時候已快中午了。一路上,眼前都晃動著那棵樹的影子。它在轟然倒下的那一刻,到底保持了怎樣的姿勢?它是否想到過,這折斷的歷史將是永久的傷痛?
然而我想,雪縱然可以壓斷它的枝柯,風縱然可以折損它的軀干,可是即使只剩下最后的小半截身子,它不也依然昂揚著筆挺,依然用最堅硬的信念,托舉起那道永恒的傷口么?
十字路口的川菜館
親人
只作為一條偶爾思戀的藤
在記憶的懸崖邊
風雨飄搖
剛來北京,首先不適應的就是飲食。朋友是地道的北京人,口味與我大不一樣。每頓在他那里敷衍過后,肚里還是空空,所以總要偷偷出來,想要找家正宗的川菜館。我們所在的小區位于東直門。把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都找了一遍,卻又犯了難。川菜館不是沒有,反是檔次都不低。朋友相聚偶爾進去幾次,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工薪階層,要一日三餐地泡在里面,終究不是辦法。雖然有些惱火,好多次都想在附近找到一家更實惠的小店,結果每次都在怏怏中無功而返。
搬到和平里以后,情況似乎有了一些轉機。周末出去閑逛,在離住處很近的地方竟然發現了三家川菜館!第一家正好位于我所在的這幢樓的左前方,地方不大,頂多十余平方。從這家再往左,是一個十字路口,又一家川菜館占了個絕好的地勢,剛好位于十字路口的東南角。第三家則在它的對面往南,再拐向西的一條小巷子里面,也不大,只比第一家略寬敞了一點。三家的口味都去嘗了一下,比較起來,十字路口的那家稍稍純正一些。
所以說是“稍稍純正”,是因為從我的口味辨別來看,它的廚藝還算不上上乘,沒有把川菜中的精髓挖掘出來。這似乎是一個矛盾。在北京,檔次高一些的川菜館味道大抵也要好一些;而檔次稍低的味道也跟著下來了。我無法像在重慶時那樣,出去轉上一圈,隨便就能找到好多家既經濟實惠,又味道上好,真正體現了川菜特色的菜館來。
重慶的火鍋自不必說了,麻、辣、燙是它的本色,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常識了。單說解放碑好吃街上的酸辣粉,就足以讓外地的觀光客好好地爽上一把。遠遠地便看見幾個平方的小小店面外排了長長的隊伍,東彎西拐,逶迤下去。生意特別好的時候,即使好不容易擠進了隊伍,最后等上一二十分鐘還沒有嘗到新鮮也不足為奇。看著前面隊伍散去的人群各自端了滿滿的一碗,香氣襲來,往往免不了要暗暗地吞下幾口口水。
終于輪到了自己,迫不及待地嘗上一口,卻又馬上恨不得把剛吞進去的全都吐出來,可是真要吐出來時卻又舍不得了,于是只管哇哇地尖叫幾聲。一面緩解它的強烈的刺激,一面不由自主地盛贊它的美好。——酸辣粉就是這樣,它的酸可以直酸到你的骨子里,它的辣也可以直辣到你的心上去。無論怎樣地酸,怎樣的辣,所有走近它的人還是愿意親口去嘗一嘗。
在重慶學習和工作的幾年,總是要趁周末的晚上去好吃街上遛達一圈。似乎只有在那里,一個人的目的和意愿才變得那樣簡單而純粹。
實際上,在我的家鄉云陽還有另一道別具風味的小吃董氏包面。包面在我們這里也叫抄手,在北京其實就是混沌。董氏包面的門面非常小。在老云安的時候,屋子里只能擺放一張大桌子,來這里的人們常常只能站的站,蹲的蹲,門里門外,兩個三個地東散一堆,西擠一群。到了新縣城,門面稍稍有些擴展,但也只能放下三四張小桌子。這樣一個看上去十分不起眼的去處,生意卻出奇地好,來店里的人總是絡繹不絕。
每年的春節回家,總要去這店里看看,嘗一嘗久違的董氏包面。慢慢地品味它的香與軟,甘與酥,心中總會萌生一種念頭。其實,無論是包面還是人,無論你看起來是多么不值一提,可你的味道果然很好,人們又怎么會失去品嘗的雅致,好好地享受一番呢?
凡要去方莊上班的早晨,我必到十字路口的那家川菜館去吃早餐。幾個包子,一碗稀飯,或者一碗湯圓,小碟泡菜。到了周末,也是要去那里坐坐。雖然它的味道并不怎么好,可是在北京,在遠離重慶千里之外的和平里,能夠安閑地坐下來品嘗幾道家鄉菜,已經是很奢侈的事情了。
每次,我都選擇離供菜窗口很近的地方就坐。在那里,可以很清晰地聽見廚師和服務員之間交流的家鄉話。我會利用這短暫的停留,拋開工作、事業、謀生、名譽、前途等等一切的概念。我只需要一會兒,就一會兒安靜的時間,喝著稀飯,吃著泡菜,咬著包子,想著我重慶的親人和朋友……
公交站牌下
漫天的雪片
凌空招展
看啊,這末路的狂歡
從十字路口的川菜館穿過斑馬線,在一個很小的郵政書報亭的左側,是807路的公交停靠站。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這里乘坐這一路公交車趕到方莊的出版社上班。和平里在北邊,方莊在南邊,兩地到底相隔有多遠,我從來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單趟所花的時間通常都在一個半小時左右,如果碰上塞車,慢慢騰騰轉上兩三個小時也不奇怪。也就是說,在正常的情況下,我每天去來所花在路上的時間一般都不會低于三個小時。這種行車的節奏與工作的節奏極不協調,但也有它的好處。我通常都會利用這難得的三個小時閉上眼睛,美美地補上一覺。這樣的機會也不是每天都能碰到,因為并不是每天我都有那么好的運氣,可以占到一個座位。即使是站著,因為人多,你挨我我挨你地相互擠著,閉上眼睛養一會兒神,居然也不用擔心會跌倒。這已是十二月的北京。從十一月初到現在,已經下過好幾場大雪了。二十幾年來,一直習慣著南方的溫潤與恬適,從來不曾經歷如此凜冽的風雪的洗禮。但生命是多么奇特,它那超乎想象的頑強與韌勁,完全使一個人變成了另一個人。也許,只有在風雪中,只有在更為艱苦的環境里,生命的質地才能得到真正的驗證。
現在,在807路公交車的站牌下,在漫天的風雪中,我靜靜地站著。我在等待。
我在等待。我每天都在經歷著這樣等待的煎熬。我已經數不清,在這等待的煎熬里,我的心到底歷經了多少次激烈的沸騰和無奈的冷卻。但是,無論它怎樣的冰冷,甚至冰冷到地老天荒,我依然在等待。我傾盡我全部的熱血,一生的智慧,玩著這致命的賭博。
因為我知道,我等來的不只是這寒冷的風雪,陰霾的流云,一定還有人心的溫暖,永恒的友情。
那天,我打點好行禮,和同學一起來到學校外面的公交站牌下。我將從這里坐車,經過二環,到達火車北站,再乘坐晚上七點的火車趕往重慶。這是我畢業離校之際在成都呆的最后一天。
乘車的同學十分擁擠,行禮都特別多。很多人相互擁抱,相互話別,相互垂淚。來送我的同學因為還有一些別的事情需處理,所以要晚些時候才能離校。等他幫我把行禮安頓好,我才好不容易擠上了車。
車開始起步。車上、車下到處都是揮動的手臂,祝福的喊聲和瀅瀅的淚花。就在這時,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已經徐徐前行的車上突然躍出一個輕盈的身影,她就像燕子一樣飛出了車窗……
然而,這只美麗的燕子將從此失去她迷人的雙翅,在藍天白云下,在那個平凡的夏日,在所有人驚疑的目光中,永遠地、輕輕地閉上自己的眼睛。
事后才知道,原來她來送同學的時候,離這趟車發車的時間還比較早,車上幾乎沒有什么人。兩個人于是選了靠后的座位坐下。同學幾次勸她下車,她都依依不舍,想在離別的時候把許多的知心話都掏給對方。車上的人越來越多,最后擠得水泄不通。等到車已啟動,她才意識到自己不得不下車了。喊了兩聲司機,可惜人聲太嘈雜,司機沒有聽見。情急之下,考慮到車才剛剛起步,她選擇了從窗口跳下。
幾年來,每每站到公交站牌下,我的眼前就會滑過那燕子一樣美麗輕盈的身影。她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把人世間真的友情演繹到了極致。每當我遇到人情的冷暖,每當我對這個世界充滿懷疑,我都會記起那個平凡的夏日。逝者用她決絕的身姿告慰生者:相對于友情,死亡又算得了什么!
而相對于死亡,所有的流浪與漂泊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至少現在我還有車可坐,而且車里還安裝著空調。
出租屋里的溫暖
我知道在最寒冷的冬天
除了寄望于四通八達的暖氣設備
窗內和窗外
我還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
房東一家三口。孩子在讀中專的外語學校。太太最初是一家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后來下崗做了一陣茶葉生意,現在在給一家私營企業打工。丈夫的運氣似乎不大好,找了好多次工作,都沒結果。這家的房子其實并不寬,一個主臥,一個偏臥,客廳很小,但還是兼了飯廳。幾間屋子的總面積加起來也不超出60平米。在北京,這大概是一般百姓家最普遍的居住條件了。
我住在偏臥。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有座墊的背靠椅,是房東給我安排的全部家當。雖然簡陋,但這些東西已經完全可以滿足我的所有工作和休息需要。在這小小的空間里,我像不知疲倦的蜘蛛一樣編織著夢想的絲網。
因為我的到來,這并不寬敞的空間似乎更顯得局促而狹小了。房東一家三口只能共擠在主臥里面,孩子則睡在半新半舊的長沙發上。這種居住方式很讓我歉疚了一陣。也曾向房東太太提議,她的孩子可以跟我睡一間屋。
那哪兒成?她立即謝絕了。你是租的我的房,我的孩子跟你住一塊兒,你不吃虧了么?
她的臉色稍稍有些黯然。實話告訴你吧,小蔡,如果不是想著明年要供孩子到國外去留學,你也看見了,就這地兒,哪還能往外出租啊!
但很快,她又欣悅了。明年,只要明年一過,我們家日子就好過了。
這末了的一句話,似乎是說給我聽的,但也像是說給她自己的。我沒有再堅持自己的意見。我想這位母親是幸福的,也是自信的。不但因為自己可以與孩子一起相依為命,還因為孩子就要有更加美好的前程在不遠處等待著。
我通常都睡得很晚。先要把白天沒有改完的稿子改完,然后還要看點書,寫點東西。有時候凌晨兩三點了出去洗漱,才發現原來我隔壁的燈也依然還亮著。我想那一定是太太的孩子還在燈下用功。我以為自己是這靜夜里唯一向上攀沿的靈魂,但看著那燈光,看著那燈光里模糊的投影,我才發現,在我的周圍,在無數平凡的屋檐下,其實還閃動著那么多雙渴盼的眼睛,在文字的巷陌里默默逡巡。
一旁的父母,該是多么的甜蜜和自足啊。
這時候,我會想到我的母親。雖然從小到大,先是因為父母的兩地分居,后來又因為我的在外求學,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候總是不多。但每次團聚,她都會傾盡她的所能,將她的愛悄悄地融進默默無聞的行動中。1998年的冬天,我因為嚴重化膿性口腔炎住院,九天沒有進食。后來才知道,母親為了照顧我,不忍心看著我一個人挨餓,竟然也陪著我整整九天沒有吃東西。結果,我的病剛剛好轉,母親卻又病倒了……
來北京以后,每個周日的晚上,母親都必定要打電話過來。雖然也沒有什么大事,都不過說些無足輕重的閑話。但在這寒冷的冬夜,在這異鄉的出租屋里,聽著母親的閑話卻格外地親切。
正這樣想著,門外響起了輕輕的敲門聲。打開,原來是房東太太。她手里捧著滿滿的一杯熱茶。累了吧?這是我前幾年沒賣完的茶。兒子要喝,也順便給你泡了杯,解解乏。
我還沒有來得及喝下這熱茶,一股熱氣騰騰的暖流卻早已深入我心。我想,生活無論怎樣的艱辛,風雪無論怎樣的猛烈,都無法擊碎,這小小的出租屋里美麗動人的記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