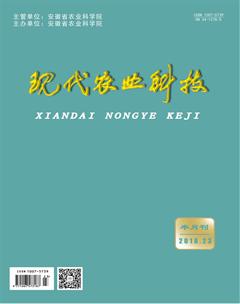蘋果樹生物質炭對土壤團聚體含量及穩定性的影響
尚杰
摘要? ? 生物質炭在農業土壤中的應用是近年來新興的土壤改良技術,具有多重農業和環境效益。本研究通過田間試驗,將限氧環境下(450 ℃)由蘋果樹樹干、枝條熱裂解所得的生物質炭以不同用量水平(0、20、40、60、80 t/hm2,分別計作C0、C20、C40、C60、C80)施入農業土壤耕作層,研究其對土壤團聚體含量及穩定性的影響。結果表明,與對照C0相比,施用生物質炭后,處理C20、C40、C60、C80 >0.25 mm機械穩定性團聚體含量均有所增加,處理C60達到顯著水平,增幅2.73%;>0.25 mm水穩定性團聚體含量均顯著增加,增幅分別為31.15%、31.11%、34.85%、35.17%;干篩條件下的平均重量直徑均有所增加,其中處理C60達到顯著水平,增幅為24.39%;濕篩條件下的平均重量直徑除處理C40外,其余施炭處理均達到顯著水平;土壤團聚體破壞率和土壤不穩定團粒指數在施炭處理后均顯著降低,但施炭處理之間差異不顯著;從水穩性團聚體的分布可以看出,大團聚體含量明顯增加,小團聚體含量顯著減少。說明施用蘋果樹生物質炭后,土壤團聚體含量及穩定性均顯著增加,進而改善了土壤的物理特性。
關鍵詞? ? 生物質炭;土壤團聚體;平均重量直徑;團聚體破壞率;穩定性
中圖分類號? ? S156.2? ? ? ? 文獻標識碼? ? A? ? ? ?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8)23-0184-03
生物質炭(Biochar)一般指農作物秸稈、木材及植物的其他組織等生物質在完全或部分缺氧和相對低溫(<700 ℃)條件下熱裂解而形成的固態產物,其形態疏松多孔且富含有機碳[1]。由于其能與土壤形成頑固的土壤碳結合體、材料來源廣泛、物理性狀良好等因素,成為了當今農業與環境等領域的研究熱點[2]。此外,生物質炭的抗降解能力非常強(包括生物降解和非生物降解),能夠在土壤中相對長期穩定地封存,具有巨大的碳封存潛力[3]。來自巴西亞馬遜河流域中部黑土的研究發現,富含木炭(生物質炭)的土壤具有更高的肥力和良好的物理特性,并且其在土壤中保存已有成百上千年的歷史[4]。
有研究表明,生物質炭本身的疏松多孔性可以增強土壤的通氣性能和持水性能[5],進而促進了良好土壤團聚體的形成[6],增加土壤的比表面積和孔隙度,降低了土壤容重[7],改善了土壤結構[8]。因此,一般認為,土壤團聚體作為土壤團粒結構的基本單元,其穩定性是反映土壤結構狀況的重要指標[9],其含量的多少是土壤肥沃程度的標志之一。本研究以關中塿土為載體,在正常種植作物的情況下,研究蘋果樹生物質炭的施用對土壤團聚體的影響,以期為生物質炭在農業土壤中的應用提供理論依據。
1? ? 材料與方法
1.1? ? 試驗區概況
試驗區設在陜西省楊凌示范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試驗田,位于北緯34°16′,東經108°04′,海拔458.6 m。該地區年均氣溫11~13 ℃,年均日照時數2 196 h,年均降雨量500~700 mm,屬溫帶大陸性易旱氣候區。
1.2? ? 試驗材料
本研究所用生物質炭由蘋果樹枝條、樹干熱裂解所得,制備條件為450 ℃的限氧環境。生物質炭的理化性質:比表面積86.7 m2/g,pH值(水土比為10∶1)10.4,C、O、H、N元素的含量分別為72.4%、23.8%、2.6%、1.2%,硝態氮0.5 mg/kg,銨態氮1.9 mg/kg。
供試土壤為褐土類,塿土亞類。土壤的理化性質:容重1.3 g/cm3,pH值(水土比為5∶1)7.3,硝態氮18.2 mg/kg,銨態氮15.9 mg/kg,有效磷12.4 mg/kg,速效鉀193.0 mg/kg,全氮0.7 g/kg,全磷0.4 g/kg,全鉀19.6 g/kg,有機質15.0 g/kg。
1.3? ? 試驗設計
將制備好的蘋果樹生物質炭磨細,過1 mm篩,根據設計用量均勻撒施于土壤表層,通過淺翻,與耕層(0~20 cm)土壤混勻。生物質炭用量設5個水平,即0、20、40、60、80 t/hm2,分別記作C0、C20、C40、C60、C80。其中,C0作對照(CK),即不施生物質炭。采用隨機區組設計,3次重復。除生物質炭用量不同外,氮、磷、鉀肥均作基肥于種植前施入,折合用量分別為純N 225 kg/hm2、P2O5 180 kg/hm2、K2O 150 kg/hm2。試驗期間根據天氣及作物生長狀況適量灌水,以滿足作物正常生長發育所需。
1.4? ? 測定項目與方法
機械穩定性團聚體采用干篩法測定:用DM180型土壤團粒分析儀,振蕩2 min,頻率300 r/min,篩分、稱量,干篩法共分8級(<0.25 mm、0.25~0.50 mm、0.50~1.00 mm、1.00~2.00 mm、2.00~5.00 mm、5.00~7.00 mm、7.00~10.00 mm和>10.00 mm)。
水穩性團聚體采用濕篩法測定:用TTF-100型土壤團聚體分析儀,共分6級(<0.25 mm、0.25~0.50 mm、0.50~1.00 mm、1.00~2.00 mm、2.00~5.00 mm和>5.00 mm),根據干篩各級團聚體質量百分比含量配比土壤樣品50 g進行濕篩,振蕩20 min,頻率40 r/min,于105 ℃在烘箱中烘干至恒量,然后置于室內空氣中自然吸濕2 h,稱量。
式中,wi為第i粒級團聚體質量所占的百分含量;Ri為某級團聚體的平均直徑;WT為供試土樣的總質量。
1.5? ? 數據處理
數據采用DPS 7.05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Excel 2007軟件進行圖表繪制。采用LSD法進行多重比較,利用One-way ANOVA分析土壤團聚體指標對不同生物質炭用量的響應,P≤0.05。
2? ? 結果與分析
2.1? ? 對>0.25 mm土壤團聚體含量的影響
DR0.25和WR0.25的百分含量可以很好地說明土壤團聚體數量和分布的變化,較好地反映生物質炭不同用量處理下土壤的團聚狀況。由圖1(a)可以看出,施用生物質炭處理的C20、C40、C60、C80的DR0.25較C0(CK)分別增加了0.02%、0.56%、2.73%、1.34%,其中C60與C0(CK)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DR0.25隨生物質炭用量的增加先增加后減少,C60達到最高。由圖1(b)可以看出,施用生物質炭處理后WR0.25均較C0(CK)顯著增加,C20、C40、C60、C80的WR0.25較C0(CK)分別增加了31.15%、31.11%、34.85%、35.17%,C80增加幅度最大,但施用生物質炭的各處理之間無顯著差異。說明蘋果樹生物質炭的施用明顯提高了>0.25 mm土壤團聚體的含量,當生物質炭施用量達到60~80 t/hm2時>0.25 mm土壤團聚體含量最高。
2.2? ? 對>0.25 mm土壤團聚體平均質量直徑的影響
MWD是反映土壤團聚體大小分布狀況的常用指標,MWD值越大,表示團聚體的平均粒徑團聚度越高、穩定性越強。由圖2(a)可以看出,施用生物質炭處理C20、C40、C60、C80的MWDd(干篩條件)較C0(CK)分別增加了15.12%、13.94%、24.39%、14.73%,其中C60與C0(CK)相比達到了顯著水平,其余處理與C0(CK)相比未達到顯著水平;整體而言,MWDd隨生物質炭用量的增加先增加后減少,C60達到最高。由圖2(b)可以看出,除了C40處理外,其余處理的MWDw(濕篩條件)均較C0(CK)顯著增加,處理C20、C60、C80的MWDw較C0(CK)分別顯著增加了36.82%、36.43%、46.12%,C80增加幅度最大,但施用生物質炭的各處理之間無顯著差異。由此說明,干篩和濕篩條件下,施用生物質炭都增加了>0.25 mm土壤團聚體的MWD,但與生物質炭施用量也有一定的關系,當生物質炭施用量達到60~80 t/hm2時土壤團聚體MWD達到最大。
2.3? ? 對土壤團聚體穩定性的影響
PAD和ELT隨土壤退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可以較好地反映土壤結構的穩定性[10]。由圖3(a)可以看出,隨生物質炭施用量的增加,PAD明顯降低。處理C20、C40、C60、C80的PAD較C0(CK)分別顯著降低了17.74%、17.34%、17.95%、18.97%,其中C80的PAD降幅最大。由圖3(b)可以看出,隨著生物質炭施用量的增加,ELT顯著降低。處理C20、C40、C60、C80的ELT較C0(CK)分別顯著降低了15.64%、15.62%、17.49%、17.65%,其中C80的ELT降幅最大。可以看出,在土壤耕作層施用生物質炭后,PAD和ELT都顯著降低,說明土壤團聚體穩定性顯著增強,而且隨著生物質炭用量的增加,土壤團聚體穩定性有明顯增強的趨勢。
2.4? ? 對土壤水穩性團聚體分布的影響
土壤水穩性團聚體分布可以很好地反映施用生物質炭后土壤團聚體的團聚情況。由圖4可以看出,與C0(CK)相比,施用生物質炭后,>5 mm的團聚體含量顯著增加,處理C80含量最高;2.00~5.00 mm的團聚體含量也顯著增加,處理C60含量達到最大;1.00~2.00 mm團聚體含量也有一定增加趨勢,處理C80增加相對較大;0.50~1.00 mm的團聚體含量也顯著增加,處理C40含量相對最高;0.25~0.50 mm團聚體含量,處理C20、C40、C60都較處理C0明顯增加,而處理C80明顯減少;<0.25 mm的土壤團聚體含量在施用生物質炭后顯著較少,并且隨生物質炭含量的增加,<0.25 mm的土壤團聚體含量逐漸減小。由此說明,不同粒級土壤團聚體分布在施用蘋果樹生物質炭后發生了較大變化,施用生物質炭可以改變土壤團聚體的團聚狀況,進而增加了土壤大團聚體的含量。
3? ? 結論與討論
研究結果表明,施用生物質炭后,土壤中>0.25 mm的機械穩定性團聚體含量、>0.25 mm的水穩性團聚體含量、土壤團聚體平均質量直徑顯著增加,團聚體破壞率、土壤不穩定團粒指數顯著降低,土壤團聚體的含量和穩定性明顯提高。綜合來講,當蘋果樹生物質炭施用量為60 t/hm2時效果最佳。
前人研究了生物質炭形成土壤團聚體的機理,表明影響土壤團聚體含量和穩定性的內在因素是形成土壤團聚體的膠結物質[11],而生物質炭中的細小顆粒具有多孔性和吸附性[8],這本身就屬于一種膠結物質。此外,生物質炭具有與土壤顆粒形成土壤團聚體和有機-無機復合體的活性功能[12],施用生物質炭直接提高了土壤有機質含量[13],間接增加了土壤的微生物量[14],刺激土壤生物活性增強,因而產生更多的分泌物,會對土壤起團聚作用。
有學者研究了生物質炭在森林、草原和農田土壤團聚體中的分布狀況,發現生物質炭在土壤中不僅僅以自由顆粒存在,還可存在于微團聚體內部并在團聚體內富集(<53 μm)[15]。黃? 超等[16]通過試驗研究發現,50、200 g/kg的生物質炭處理顯著提高水穩性團聚體含量,與本研究結論一致。可見,土壤中施入生物質炭以兩方面因素造成了土壤團聚體的形成與穩定:一方面是生物質炭的穩定性和特殊的理化特性,另一方面是因團聚體自身特性的保護作用從而長期固持。
4? ? 參考文獻
[1] LEHMANN J,GAUNT J,RONDON M.Biochar sequestration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A review[J].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Global Change,2006,11:395-419.
[2] 陳溫福,張偉明,孟軍.農用生物炭研究進展與前景[J].中國農業科學,2013,46(16):3324-3333.
[3] GLASER B,HAUMAIER L,GUGGENBERGER G,et al.The ‘Terra Pretaphenomenon:a model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humid tropics[J].Naturwissenschaften,2001,88(1):37-41.
[4] GOLDBERG E D.Black carbon in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Wiley,1985.
[5] 高海英,何緒生,耿增超,等.生物炭及炭基氮肥對土壤持水性能影響的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11,27(24):207-213.
[6] GASKIN J W,STEINER C,HARRIS K,et al.Effect of low-temperature pyrolysis conditions on biochar for agricultural use[J].Transactions of the ASABE,2008,51(6):2061-2069.
[7] BUSSCHEI W J,NOVAK J M,EVANS D E,et al.Influences of pecan biochar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a Norfork loamy sand[J].Soil Science,2010,175(1):10-14.
[8] NOVAK J M,BUSSCHER W J,LAIRD D L,et al.Impact of Biochar amendment on fertility of a southeastern coastal plain soil[J].Soil Science,2009,174(2):105-112.
[9] LE B Y.Aggregate stability and assessment of soil crustability and erodibility I.Theory and methodology[J].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1996,47:425-437.
[10] 宮阿都,何毓蓉.金沙江干熱河谷典型區(云南)退化土壤的結構性與形成機制[J].山地學報,2001,19(3):213-219.
[11] 史奕,陳欣,沈善敏.有機膠結形成土壤團聚體的機理及理論模型[J].應用生態學報,2002,13(11):1495-1498.
[12] GLASER B,LEHMANN J,ZECH W.Ameliorat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ighly weathered soils in the tropics with charcoal-A review[J].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2002,35:219-230.
[13] 花莉,張成,馬宏瑞,等.秸稈生物質炭土地利用的環境效益研究[J].生態環境學報,2010,19(10):2489-2492.
[14] LIANG B,LEHMANN J,SOHI S P,et al.Black carbon affects the cycling of non-black carbon in soil[J].Organic Geochemistry,2010,41(2):206-213.
[15] BRODOWSKI S,JOHN B,FLESSA H,et al.Aggregate-occluded black carbon in soil[J].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Science,2006,57(4):539-546.
[16] 黃超,劉麗君,章明奎.生物質炭對紅壤性質和黑麥草生長的影響[J].浙江大學學報(農業與生命科學版),2011,37(4):43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