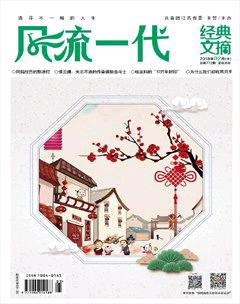重識“典當”
崔猛
典當行即當鋪,其經營業務就是收取衣、物、首飾等諸般實物作為質押,放款給典當人。典當人要按約定期限到當鋪贖取實物并支付貸款本息,如遇逾期未來贖取者,當鋪就沒收其所抵押的實物,變賣以償貸。
典當的歷史
典當業是中國最古老的金融行業,中國典當業的出現比西方要早近千年。《大英百科全書》認為:“典當業在中國兩三千年前即已存在,西方則可追溯到中世紀。”中國史籍關于典當活動的零散記載最早見于漢代,但由于在當時并沒有產生大規模、成氣候的典當活動,只能認為是隨機性的行為。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貸”為“以物質錢”。南朝宋的范曄在《后漢書·劉虞傳》中也提到過“典當胡夷”。凡此種種,說明兩漢時期的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以物質錢的活動,雖然此間并未出現典當機構,但社會中“典當”行為的逐漸活躍,也促進了中國典當業的萌生。
中國典當業發端于南朝的佛寺,當時被稱為“質庫”或“長生庫”。南朝寺院質庫是以濟貧救世的慈善面目出現的,正所謂“佛物出息,還著佛無盡財中”。這“回轉求利”“出息取利”的“無盡財”,既可生息積財事佛,又是解決貧民一時窘急而行的慈善救助之舉。隨著南北佛寺質庫的產生以及質錢活動的不斷發展,經過一定時期的演變,社會上一個專門從事以物質錢的借貸行業———典當逐漸形成。
唐朝時期,國家繁盛,社會穩定,生產力得到巨大發展,典當也從單一的寺庫質貸發展成為官營、私營和寺營三種形式并存的興盛局面。《舊唐書》卷一八三記載:“籍其(指太平公主)家,財貨山積,珍奇寶物,侔于御府,馬牧羊牧田園質庫,數年征斂不盡。”《全唐文》卷七八中也說道:“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典當業的出現促進了經濟發展,方便了市民生活。
宋代是中國都市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時代,這就為與之關系密切的典當業得以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新的歷史契機。宋代典當業的資本性質同唐代大體相似,即官當、商(民)當和寺院質庫并行于世。不過,宋朝官、商典當行業的經營規模和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已經遠遠超過了同期的寺院質庫。
金代歷史雖短,其典當業發展卻頗具特色。在唐、北宋兩代的基礎上,金代典當業的經營管理及實施的相關政策、法規日臻完善。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63),朝廷頒布了一部管理完備的典當法規,其中規定:當本按當物估值七成折價;利息規定月利一分,當期規定“經二周年外,又愈月不贖即聽下架出賣”。即當期二年,允許超期一個月,到期不贖便可變賣;當物損失應由當鋪承擔賠償責任。
元代仍持續著唐宋以來僧俗并舉的局面,并且寺院的質貸活動依舊活躍。如《元典章》卷三三《禮部·僧道教門清規》記載:“(皇慶二年江浙行省言)各處住持耆舊僧人,將常住金谷掩為己有,起蓋退居私宅,開張解庫(即當鋪)。”
明代中國的典當業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而繼續發展,但基本上都是商人資本、民間經營,并進一步突出了皖、晉、閩等地緣性行幫與地域性商業文化傳統。有清以來,典當業興旺,無論資本、鋪數還是規模、類型,其發展勢頭都是空前的,是以往歷代所難以相比的。
中國典當業在經歷了明清兩朝的繁榮興旺之后,于清末民初逐漸衰落。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進行公私合營的改革,典當業在大陸銷聲匿跡。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一度消失30多年的典當業又在溫州、沈陽等一些大中城市悄然復活,得以新生。據統計,到2013年5月底,中國內地共有約7000家典當行在運行經營中。
當鋪的特色
舊時的當鋪,其外觀給人的印象大體如此:極大的一個繁體“當”字懸掛在門口,氣勢奪人。走進當鋪之后,兩米多高的柜臺中間留有一個貓洞似的小窗口,周圍皆用鐵柵欄釘死;高高的柜臺用堅固的榆木制成,外邊鑲著富有韌性的竹條,再釘上釘子。可以想象,昏暗的店堂,高高在上的窗口,典當人從漆黑的大門進來,走不到兩步,仰視這窗口,心里那份忐忑和虛弱,即便是體型高大、生相威猛的漢子,在這里也不由自主地顯得渺小了。
1922年冬,魯迅在為其第一部小說集《吶喊》所作的自序中回憶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比我高一倍,我從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誣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買藥。”著名畫家豐子愷曾創作過一幅《高柜臺》的漫畫: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孩子,踮著腳,抬頭看著當鋪柜臺前的朝奉,左手扶著柜板以求站穩,抬起右手向上舉起一包要當的東西,然而那被高高舉起的當物還尚未夠及柜臺的上沿。盡管畫上的柜臺并非魯迅筆下的那樣,但也比漫畫中男孩子的個頭高出一半。日本學者宮尾茂在其著作《支那街頭風俗》中介紹到中國當鋪時,也注意到店堂前七八尺高、帶圍板的大柜臺,當客舉起手還僅僅伸到距離柜臺上沿一尺多遠的地方。
明清之際的典當建筑,因其地域及行業因素形成了相對不同的地域性、功能性特征。例如北方因氣候比南方干燥,便不像南方典當行那樣特別強調防潮問題;而南方冬季遠沒有北方寒冷,所以無需備有北方典當行所需的保暖設施。還有,因典當業內多儲藏來往的錢財和細軟,防火、防盜是首先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所以當鋪的建筑、設施要盡量堅固、完備、合理。有的當鋪為了防盜,還專門建有值更守夜的鼓樓。清代人顧張思所著《土風錄》的卷四“鼓樓”條記載:“城隅有樓曰鼓樓,典質家亦起樓置鼓,以守夜。”出于安全考慮,歷史上許多典當建筑都修建得像軍事堡壘一樣堅固,成為中國建筑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典當的招幌文化
所謂“招幌”,即“招牌”與“幌子”的復式通稱。典當業的特有標志不僅有高大、森然的營業柜臺,還有別具一格的典當招幌。典當招幌分為兩類:一是文字招幌,二是象形招幌或標志幌。
文字招幌是將直接表現本行業經營內容的“典”“當”“質”“押”等單字醒目地掛于墻、屏或招牌上,以招徠顧客。如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趙太丞家”對過巷中那座解庫門面上的“解”字。明清時期,由于質鋪多被稱為“典當”或“當鋪”,所以在鋪門前掛兩面大書“當”字的“一字招”木牌,成為當時的行業習慣。木牌四角用銅片包飾,“當”字之外間或書以小字鋪號。清代因迫于政府律令而以小字在牌下端標示“軍器不當”字樣。清末民初,廣東典當因不實行當時的領當帖繳帖稅制度而實行繳餉銀,因而其文字招幌則多寫為“餉按“”餉押”等字樣。另外,舊時有些講究的當鋪不用木牌,而是用銅制字牌,以示莊重。
象形招幌或標志幌主要流行于北方,而且兼以字幌為輔助幌,其中北京是比較典型的。楊肇遇在《中國典當業》一書中提到:“北平頗為特異,其他之典當,墻上并不大書其當字,惟門前懸特制巨大之緡錢兩貫。初至者,往往誤以為錢鋪,實則為典當之標記耳。此因習慣不同,而設備以異也。”
典當招幌是典商用以標示經營內容、規模和招徠顧客的特殊標志,也是一種具有特殊意義的裝飾。典當招幌是否醒目、莊重,對當鋪的生意有直接的影響,因而一向為典商格外看重,并形成相應習俗。典當招幌的演變軌跡,基本上是由簡到繁,再由繁而簡的,但無論如何變化,其功能、特性則始終如一。
典當業在歷史上是一個時間跨度很長的融資行業,從古代的解百姓燃眉之急到如今作為銀行融資的補充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經濟發展史、社會生活史中都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