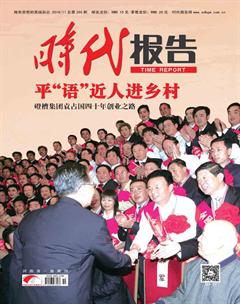默克爾,謝幕倒計時
陳樹

“有一天,大家會厭煩默克爾的風格;有一天,黨內將不再支持她,屆時大家將會看到默克爾卸下總理的職務。”在《默克爾傳》結尾,作者德國記者斯蒂凡·柯內琉斯這樣寫道,“當時代潮流轉變之時,就是默克爾謝幕之際。”
不到五年,預言變成了現實。
10月29日,安格拉·默克爾出現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CDU)的新聞發布會上。像以往一樣,她身著寬松的單色西裝和西褲,短發梳得一絲不茍,面色看不出喜怒。這位領導基民盟18年、執政13年的總理,被稱作“穩定和連續性的象征”——在此期間,意大利換了七任總理,愛麗舍宮三度易主。
“今年12月,我將不再參與基民盟黨首的競爭,在2021年總理任期結束后,我也不會參與2021年的總理大選。”她強調,自己將“徹底退出政壇”——不會競選德國聯邦議員,也不會在歐盟或者聯合國機構任職。
這是一場出人意料的告別。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她沒有退縮,僅用一年時間就帶領德國度過危機,重現繁榮;在歐債危機期間,不滿福利削減的希臘人搞炸彈恐嚇,她沒有妥協;2015年那場“改變歐洲”的難民潮襲來,她也沉穩面對壓力和批評,沒有被擊敗;去年第四次當選總理后組閣舉步維艱,她依然不言放棄。
但這一次,她準備離開了。促使她作出這個決定的,是基民盟及其姊妹黨、聯合執政黨近一個月在傳統優勢州遭遇的一系列慘敗。德國特殊事務部部長海格里·布勞恩說,這是由于執政聯盟中高層內訌造成的,但默克爾把失敗歸咎于自己。
“我所在的基民盟可以在漢堡的黨代表大會上選出一個新的領導層,制定新的計劃,為我的離開做好準備。”她以典型的“默克爾式”平靜語氣說道。成為總理之前,默克爾曾表示自己期待能體面地離開:“當我退出政壇時,我不想成為一具半死不活的殘骸。”
只是,她能如愿“功成身退”嗎?
“我們能做到!”
并沒有多少人能準確地意識到,2015年的那場難民潮,會給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帶來如此深刻的負面影響。對當時的默克爾來說,那也不過是她任期中諸多危機的其中之一。
正如柯內琉斯所寫的那樣,“危機是默克爾任上的主題曲”。她沒有自己的“政治導師”、前任總理赫爾穆特·科爾那樣的好運:在國泰民安的時期治理德國,順應歐洲自由革命的正向動力,將德國帶向統一與繁榮。
默克爾的任務是抵抗與防御,敵人則是衰退。2008年,她上任的第三年,一場全球金融危機就使得德國遭受重創。一些歐盟國家則陷入債務危機,瀕臨破產。
迅速走出危機的德國成為了處理歐債危機的主角。“理性”,她強調,并隨身攜帶著一份列著每個歐洲國家的薪資成本和負債曲線的圖表,不斷提出強硬的經濟政策,想要說服深陷危機的南歐國家接受。
盡管被南歐國家的反對者斥責為“納粹”,但她光芒四射的“女英雄形象”頻頻出現在各種政治雜志的封面上。2014年烏克蘭危機時,她又率領歐洲作出回應。到了2015年,她的個人聲譽幾乎到達頂峰,德國也被視作“歐洲事實上的外交領袖”。
也正是在2015年,中東危機加劇,來自敘利亞、黎巴嫩、約旦等國的難民為躲避戰爭,乘坐擁擠的小船跨過地中海,沿著高速公路長途跋涉,希望在德國、瑞典這樣的富裕國家尋求避難。無數悲慘的故事由此發生,占據著主流媒體的頭條:死去的3歲敘利亞難民小庫爾迪面朝下地躺在海灘上,就像睡著了;奧地利高速公路一輛貨車里,警方發現了71名死去的難民……
匈牙利右翼總理維克托·奧爾班卻堅持當“惡人”。他拒絕讓難民進入奧地利,那是抵達德國前的最后一站,越來越多難民滯留在布達佩斯的凱萊蒂(Keleti)火車站。
但在這個時候,默克爾點頭了。通往德國的大門打開了,提著破舊的編織袋、滿臉疲憊的男女老少到了慕尼黑。迎接他們的,是德國志愿者的掌聲、歡呼聲以及歡迎橫幅。德國的城市和小鎮舉辦了一場又一場的街頭歡迎派對,倉庫里堆滿了捐贈的食品和衣物,為難民特別建造的小樓也立起來了。
“德國人深深陶醉在他們新獲得的國際聲譽里。”有媒體這樣寫道:“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邪惡形象,也不是欺負南部歐元區經濟弱國的經濟巨頭。現在,德國是歐洲人道主義精神的代表。”
有分析師認為,默克爾的“開放大門”的決定不過是順應民意,也有人說,從經濟角度考慮,引進年輕的難民可以緩解德國的老齡化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仰賴“理性”的默克爾在再三權衡后,相信情況是可控的。
“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前環境部長諾伯特·羅特根說,“對于默克爾來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做法,基于事實作出決定——德國能夠處理好這些難民。”
“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默克爾喊出這個口號,并不斷重復。她訪問了德國境內多個難民收容所,微笑著與難民合影。到了2015年11月,德國確認登記96.4萬難民,成為整個歐洲接收難民人數最多的國家。
但情況逐漸失控。其他歐盟國家對德國的“開放大門”政策議論紛紛,并忽視了默克爾的提議——將難民在歐盟國家間平均分配。盡管有成千上萬努力工作的志愿者,德國仍然難以整合數量如此龐大的難民——當年11月底,僅柏林的社會服務中心每天就需要接待500到600人。
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天,一樁犯罪事件讓德國徹底陷入了對于難民的恐慌中。在科隆的新年倒計時慶祝活動中,數百名女性遭到一群男性的性騷擾甚至是侵犯。警方描述,“嫌疑人看上去具有阿拉伯血統”。
默克爾遇到了大麻煩。“我們能做到”,她還在堅持。但下滑的支持率顯示,相信她的選民越來越少。基民盟在地區選舉中遭遇了兩次羞辱性的失敗,其中一次還是在默克爾的家鄉梅克倫堡,黨派內部出現了“更換默克爾,否則下屆大選將失敗”的聲音。此時的默克爾,在德國媒體筆下“疲憊而孤立”。
“自由”世界的總理
在科隆集體性侵事件發生幾周前,盡管飽受爭議,默克爾還是得到了一個好消息:她當選了《時代》周刊2015年度風云人物,成為30年來第一個獲此頭銜的女性。《時代》稱,默克爾在歐洲主權債務、難民和移民、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內政等危機期間,展現了“出色的領導能力”。
這也大概是為什么默克爾在經歷過難民危機后,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2017年8月,默克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時是一個非常時期,出于個人的政治和人道主義理念,我基于我眼中的正確做出了決定。即便現在再給我一個機會,我也會作出和2015 年時同樣的決定。”
“在難民問題上,默克爾的立場堅定不移。”BBC記者安妮·希爾寫道,“她似乎已經逃脫了這場災難,但也許這依靠更多的是運氣而非判斷。”
她留了下來,并開啟了自己的第四個任期。事實上,對于是否再次參選,默克爾考慮了很久,百萬難民涌入德國后,聯盟黨內的劇烈政治動蕩險些讓她落馬。
“她敢于冒著風險再次參選,常常被解釋成不只是為了德國。”德國之聲在2017年大選專題中寫道,“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離歐盟以及歐盟危機、右翼民粹主義抬頭等政治事件面前,她被認為是不確定時期的穩定點。默克爾或許認為自己有義務在困難時期留下來。”
“我們必須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默克爾確實開始了放棄依賴美、英的傳統聯盟,重新尋找、創造穩定且全新伙伴關系的“旅程”。經常和特朗普“對著干”的她,被《紐約時報》稱作“歐洲最后的強大捍衛者”。
世界已經變了
但有著慘痛歷史教訓的德國,也沒能躲過歐洲新一波民粹主義浪潮,如同歐洲其他國家議會,民粹政黨話語權越來越大。早在2015年難民大量涌入時期,主張德國民族主義的極右翼黨派德國另類選擇(AfD)就開始在各地活躍,吸引了一批反對難民的支持者。隨著各類惡性犯罪事件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媒體頭條,不少人流向AfD。到了2017年德國大選,在上一屆選舉中席位為0的AfD一下拿下94個席位,一躍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三大黨。
而默克爾所在的中右翼政黨基民盟,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溫和傳統黨派一樣,無可避免地衰退了。2017年的大選中,基民盟僅斬獲200個議會席位,遠低于成為執政黨所需要的底線(355個)。這意味著,基民盟必須與議會中的其他黨派合作,組建一個聯合政府。默克爾因此飽受質疑,聯盟內外再次響起“默克爾必須走人”的聲音。
171天后,“史上最長組閣”終于完成。今年3月4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SPD)表示,社民黨成員們投票支持與總理默克爾所屬保守派(基民盟與基社盟)組閣。確認“四連霸”的默克爾,票數卻不太好看——反對票達到了315張,僅比贊成票少49張。
分裂卻遠未終結。盡管社民黨總體上支持基民盟的政策主張,但保守派內部卻矛盾不斷——基民盟和自己的“姐妹黨派”基社盟(CSU)已經貌合神離。比基民盟更為保守的基社盟,黨首霍斯特·澤霍夫也是內政部長。
澤霍夫在難民問題上十分強硬,主張德國政府遣返任何未在本國登記的難民。事實上,涌入歐洲的難民數量在近兩年來已大幅減少。據《紐約時報》報道,2015年10月,通過海路抵達南歐的難民數量超過22萬人,而2018年5月,這個數字只有1萬。
但這個世界已經變了。難民問題不僅是事實層面的問題,更是與政治意識形態緊密相關的問題。“被恐懼塑造的文化和社會是無法掌控未來的。”一場活動中,當一名女性提問總理會采取什么措施防止“伊斯蘭化”時,她答道。恐懼是默克爾謹慎而小心對待的一種情緒,也是民粹主義通向成功的一把鑰匙。
也許默克爾也意識到了這種改變。7月2日,她做出上任以來關于難民問題的最大妥協。這一天她宣布,德國未來將在邊境修建“過境中心”,新抵達的難民需要先接受檢查,如果此前已在其他歐洲國家尋求難民身份就會被遣返。此外,為了阻擋難民入境,德國與奧地利之間的邊境監管也將大大加強。
就像大多數時候那樣,默克爾作出這個決定花費了好幾個月,經過多次協商、探討和比較。這種謹小慎微的執政風格,曾給期待“只要和諧,不要沖突”的德國人帶來極大的安全感。然而在這個崇尚領導人魅力的年代里,這卻是“默克爾老了”的佐證。
不僅是執政風格的落伍,這位被加州前州長施瓦辛格稱作“全世界最強大的女人”,不論在自己的黨派還是聯盟內部,已經越來越被孤立。和多數強人一樣,她意志堅定,有時候甚至固執而多疑。“她的缺點是許多身居高位者所共有的,我在科爾身上也曾看到過它。”基民盟議員博斯巴赫說,“當有人提出不同觀點或是質疑時,比如希臘危機或是難民問題,即使表示‘我站在你這一邊,她還是會覺得難以接受,質疑你的忠誠。”
即使作出讓步,默克爾保守派政府的內部裂痕依舊越來越大。不滿難民政策的澤霍費爾甚至在9月提出辭職,并嘲諷道:“我應該和極右翼一起去游行示威。”他堅稱,“難民是德國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
最終,基民盟因內訌在10月28日黑森州的選舉中,得票率創下1966年以來的最差成績。盡管表示自己會完成第四個任期,在2021年卸任總理一職,但失去基民盟黨首地位的她,權力將大大削弱。一些德媒甚至認為,她能否如愿堅持到三年后,還是個未知數——社民黨稱,若執政聯盟不能取得預期成績,其將退出大聯合政府。這意味著聯盟黨需要重新尋找聯合政黨,或是提前大選。
如今,默克爾時代正在畫上句號,她身后是一盤殘局。《衛報》認為,“默克爾的離開,將使歐洲的政治穩定和共識,陷入二戰以來最危險的時刻。歐洲政治將陷入真空”。
但也有分析認為,默克爾的“以退為進”,可以避免黨內“逼宮”,也可能給德國帶來不一樣的可能。“德國需要某種刺激,這是一件好事。”丹麥《于爾蘭郵報》評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