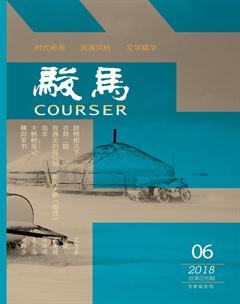延安放歌
董聯聲
延安,中國革命的搖籃。
延安,中國革命的心臟。
有多少仁人志士向往革命圣地延安。
有多少抗日軍民寄希望于延安。
“我要去延安”,這是時代的吶喊。
“我一定要去延安”,這是我心靈的涌動。
我同樣向往中國革命圣地延安,朝思暮想,夢繞魂牽。
2016年金秋時節,作為東北方言研究者、中國漢語方言學會會員,我有幸被邀請參加在延安大學舉辦的“第七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國際學術研討會”。從大興安嶺東麓素有“塞外蘇杭”之稱的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扎蘭屯市出發,一架銀白色的中國民航客機穿越連綿起伏的黃土高原,飛過奔騰不息的母親河黃河,來到心馳神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偉大詩人白居易有詞云:“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而這里我要說,“歲月滄桑今勝昔,中國革命換新天,誰不想延安?”
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沖破國民黨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克服人類幾乎不能克服的艱難困苦,血戰湘江、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激戰臘子口。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重新確定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1935年10月,紅一方面軍與陜北紅軍在吳起鎮勝利會師。楊家嶺,便成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總部的初始駐地。在這里,中共中央指揮中國工農紅軍和億萬抗日軍民以“小米加步槍”的英雄氣概,同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進行殊死的斗爭,開展統一戰線,同國民黨蔣介石反動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抗爭。延安楊家嶺,便成為中國革命的心臟和指揮中心。
如今的延安小城,同樣是高樓林立,街道寬闊;同樣是汽車如流水,霓虹燈閃爍,儼然是一座現代化城市,完全沒有了昔日印象中黃土裸露、窯洞破舊寒酸的舊模樣。
金秋九月,本應該秋高氣爽,艷陽高照。而黃土高原腹地的延安小城,卻是淫雨霏霏,連日不開。
楊家嶺——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的初始駐地,同樣籠罩在濛濛細雨之中。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等人的辦公室兼臥室舊址舊居星羅棋布地散落在楊家嶺半山坡。今日對外展出的窯洞外貌雖已裝飾一新,但仍然難掩當年破舊不堪、簡陋寒酸的舊貌;條條崎嶇的黃土小路雖然已被現代化水泥臺階替代,但仍然難掩當年黃土裸露、泥濘不堪的容顏。孔孔窯洞風格幾乎一致,依山為屋,鑿洞為室,狹窄陳舊,不過數米,桌椅殘破,床榻簡陋;油燈一盞,電話一部。被國民黨蔣介石稱為“朱毛赤匪”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辦公兼臥室的窯洞,也不過多了幾張破舊的躺椅而已。如今漫山遍野蒼翠欲滴、郁郁蔥蔥的芳草樹木,從各窯洞陳列展出的舊照片中不難看出,當年也是荒山禿嶺,黃土裸露,溝壑縱橫,崎嶇不平。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部、統戰部等中央領導機構的辦公窯洞,幾乎與中央領導人的辦公舊址毫無二致,只不過多了幾孔窯洞、幾張破舊的桌椅而已。中共中央大禮堂曾召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當年召開大會時懸掛的會標以及破舊的長凳、墻上張貼的標語口號都保持著當年的舊模樣。
就在這斗屋陋室里,就在如豆的油燈下,毛澤東揮動如椽的巨筆,寫下了《中國革命向何處去》《論持久戰》等鴻篇巨著,指揮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程。
徜徉在楊家嶺的土路上和窯洞間,不禁浮想聯翩、感慨頗深。就在這黃土坡上的窯洞里,就在這簡直不可想象的斗屋陋室間,就在這艱苦卓絕的條件下,中共中央是以怎樣的博大胸懷、凜然氣勢,指揮著億萬抗日軍民同窮兇極惡、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軍進行浴血抗戰,怎樣同數倍于我、裝備精良的國民黨反動派斗智斗勇,直至奪取全國勝利、“進京趕考”……
在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聲中,在涌動的人流間,我的腳步蹣跚;綿綿細雨中,我的思緒在升騰,在翻滾……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駐地由楊家嶺移駐棗園。棗園革命舊址風格與楊家嶺革命舊址大體一致,唯一不同的是,這里的窯洞較之楊家嶺的窯洞面積大了些,庭院寬敞了些。令人不解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局舊址”既無一部電臺陳列,也沒有一部電話陳列。真不知在那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黨中央發出的封封重要電報、全國各地地下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發往延安的情報黨中央是如何接收的。
延安革命紀念館建筑規模巍峨宏大,毛澤東主席巨型塑像聳立在紀念館前空地。遠望之、近觀之,敬佩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延安革命紀念館即王家坪革命紀念館,以圖片、實物、圖表、雕塑等多種形式,展出了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壯大、從秋收起義到紅軍的建立、萬里長征、抗日戰爭等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壯大和成長過程。漫步其間,目不暇接,思緒翻滾,步履蹣跚。這里展出的不僅僅是延安革命史,更是中華民族革命史。它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縮影,它是中國革命的史詩。世界偉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言談舉止、外貌長相、性格特點,都是通過《毛澤東》《開國大典》等電影、電視劇中獲知的、看到的、領悟的,如今在幾座革命舊址中都一一得到了驗證。
寶塔山、延河水,早已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標志和象征。寶塔山與延安城近在咫尺,無論日觀夜賞,均可一目了然。而夜觀寶塔山,朦朧夜色中,金黃色的燈光籠罩的寶塔山熠熠生輝,格外耀眼。寶塔山下發生的故事,任憑人們述說、遐想、憑吊……延河水在山腳下日夜流淌,向人們述說著昔日激情燃燒的不朽歲月。寶塔始建于唐朝大歷年間,跨越幾千年,到了近代延安成為革命圣地才真正有了名氣。凝望著巍峨的寶塔,耳畔中響起陳毅元帥的詩歌,由遠而近,逶迤飄來:“延安有寶塔,巍巍高山上。高聳入云端,塔尖指方向。紅日照白雪,萬眾齊仰望。塔尖喻領導,備具莊嚴相。猶如豎戰旗,敵軍膽氣喪。猶如過險灘,舵手平風浪。又如指南針,航海必依傍……”革命詩人賀敬之更有詩贊曰:“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作為延安標志性建筑的寶塔,成為革命圣地的象征,像一座閃爍的燈塔,吸引著無數進步青年,不畏艱險,跋山涉水,來到延安尋求民族解放的真理。“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無數詩人為之作詩放歌,無數畫家為之揮毫作畫,無數歌唱家為之引頸歌唱。
距延安城百里外的延川縣梁家河村,是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插隊落戶當知青的地方。一孔孔破舊的窯洞,一盤石碾,一口水井,一泓淤壩……留下了習近平及其他北京知青昔日戰天斗地、度過知青生活的痕跡。我也曾經是一名知青,我也曾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歲月。然而,萬千知青默默無聞,碌碌無為,成為蕓蕓眾生,而成大器者、成為領袖人物者能有幾人?望著那似曾相識的景物,回想近五十年前的知青生涯,我不禁思緒萬千。
延安為什么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到底有什么魅力?是八十年前土窯洞里的燈光?是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是巍峨的寶塔山?是滾滾的黃河水?還是習近平總書記住過的那一孔窯洞?我一時無言以對。假如沒有當年延安張開那寬闊的臂膀接納疲憊不堪但信念堅定的中央紅軍,假如黨中央沒有將指揮中心設在延安,假如當年陜北沒有付出巨大的代價支援中國革命……沒有“假如”,有的只是歷史的必然。無需找到正確的答案,魅力永遠屬于延安。尋此軌跡,我終于讀懂了延安的華彩樂章,讀懂了它優秀的品格魅力。
我崇敬延安。
我景仰延安。
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