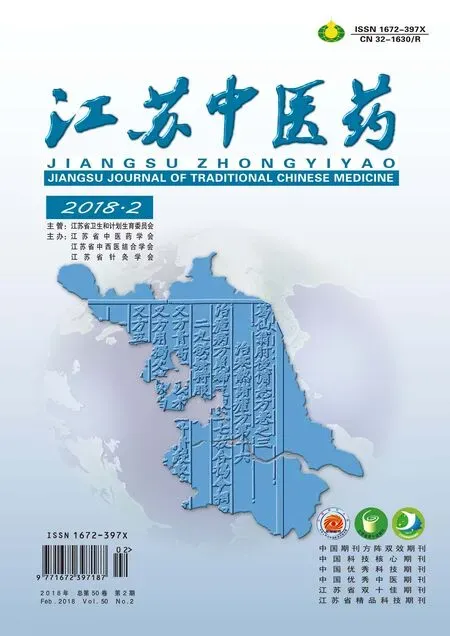朱璉興奮針法聯合耳尖放血輔助治療小兒風熱型外感發熱40例臨床觀察
莫智珍 岳 進 陳明明 韋立富 馬 玲 劉 旋
(1.南寧市第七人民醫院,廣西南寧530012; 2.南寧市中醫醫院,廣西南寧530022)
外感發熱是小兒臨床常見癥狀,常因外感六淫所致,可分為風寒型、風熱型、暑濕型等,其中以風熱型較為多見。相當于現代醫學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約90%以上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少數可由細菌和支原體引起[1-2]。西醫常規采用藥物或物理降溫治療,方法單一且副作用大,易引發肝腎損害、消化道損傷、過敏性皮疹等不良反應[3],而中醫療法安全多樣,采用針藥結合治療,退熱快速而平穩,不易反復,又可減少長時間、反復口服藥物的副作用。本研究旨在觀察藥物治療基礎上采用朱璉興奮針法聯合耳尖放血治療小兒風熱型外感發熱的療效,并與單純藥物治療作對照,現將相關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3年2月至2017年5月南寧市第七人民醫院、南寧市中醫醫院針灸科門診及住院的發熱患兒80例,以患兒就診順序編碼后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40例。治療組男21例,女19例;年齡1~6歲,平均年齡(3.4±2.3)歲;病程3~15d,平均病程(9.4±5.63)d;平均體溫(38.9±1.3)℃。對照組男23例,女17例;年齡1~5歲,平均年齡(3.3±2.1)歲;病程4~15d,平均病程(9.1±5.84)d;平均體溫(38.8±1.2)℃。2組患兒性別、年齡、病程、體溫等一般資料比較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全國醫學院校系列教材《兒科學》[2]制定。
1.2.2 中醫辨證標準 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4]制定。主癥:發熱或高熱,微惡風,有汗。次癥:(1)鼻塞;(2)流濁涕;(3)噴嚏;(4)咳嗽痰稠;(5)口干咽痛。舌脈及指紋:舌苔薄黃,脈浮數或指紋紫。主癥必備3項,次癥符合1項及以上,結合舌脈、指紋即可確診。
1.3 納入標準 (1)符合上述診斷標準的患兒;(2)體溫在37.4℃以上者;(3)年齡1~6歲;(4)性別不限;(5)患兒監護人同意參加試驗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4 排除標準 (1)年齡小于1歲或大于6歲者;(2)合并有心腦血管、肝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疾病;(3)各種原因導致不能配合治療者;(4)正在參加其他臨床試驗者。
2 治療方法
2.1 對照組 予小兒豉翹清熱顆粒口服(濟川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批號:1301024),3次/d,2g/次。體溫達38.5℃及以上的患兒配合采用布洛芬混懸液口服(上海強生制藥有限公司,批號:130125373),5~10mg·Kg-1·次-1,2次/d。
2.2 治療組 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予朱璉興奮針法聯合耳尖放血治療。取穴:大椎、曲池(雙)、合谷(雙)、足三里(雙)、三陰交(雙)。
朱璉針刺具體手法:取0.25mm×0.25mm毫針,用快速捻進法進針,醫者拇、食、中三指持針柄,針尖平穩而輕盈地停在皮膚表面后快速捻轉迅速刺入,當針尖透過真皮后,用朱璉興奮Ⅰ型手法運針,即快速均勻地捻轉,捻捻停停,停停捻捻,結合少許提插手法,使針感向下傳導,醫生握持針柄搗針3次后立刻出針,不予留針。2次/d,每次取6~8個穴位進行針刺。
耳尖放血療法:取雙側耳尖穴位,男左女右,男患兒先從左耳開始施治,女患兒先從右耳開始施治。首先醫生以拇指、食指揉搓患兒耳廓,由下至上,均勻有力,反復揉搓,搓至患兒耳廓發熱充血后,不要放手,直接對折耳廓,耳尖最高點即是穴,予穴位消毒,用一次性注射器針頭(4號半針頭)快速點刺,出血后反復擠壓,以酒精棉球擦拭,一擠一擦,反復進行,直至血流停止,穴位再次消毒,治療完畢。1次/d,治療時機選擇在晚上,當患兒體溫升至較高時,即可進行耳尖放血治療。
3 療效觀察
3.1 觀察指標
3.1.1 體溫 對照組從第1次口服小兒豉翹清熱顆粒開始計時,治療組從針灸治療及第1次口服小兒豉翹清熱顆粒后開始計時,測量2組患兒治療前及治療后第1h、6h、24h、48h、72h這5個時間節點的體溫。
3.1.2 臨床癥狀及體征 觀察并記錄治療前及治療后第24h、48h、72h 2組患兒咳嗽、流涕、咽喉腫痛、舌象、脈象等癥狀、體征的變化情況。
3.2 療效評定標準 痊愈:體溫在24h內降至正常(體溫降至37.4℃以下,不再回升),咳嗽、流涕、咽喉腫痛等臨床癥狀及體征消失,輔助檢查恢復正常;顯效:體溫在24~48h內降至正常,其他臨床癥狀和體征明顯好轉,輔助檢查明顯改善;有效:體溫在48~72h內降至正常,其他癥狀和體征部分消失或有所好轉,輔助檢查有所改善;無效:治療72h后體溫、臨床癥狀、體征及輔助檢查無好轉或加重[5]。
3.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處理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進行t檢驗,以(-x±s)表示,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4 治療結果
3.4.1 2組患兒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1。
3.4.2 2組患兒治療后不同時間段體溫比較 見表2。
4 討論

表1 治療組與對照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小兒風熱型外感發熱屬于中醫學小兒感冒的范疇,屬風熱型感冒。小兒臟腑嬌嫩,形氣未充,腠理疏松,衛外不固,外邪容易入侵,正氣與之相搏,正邪交爭,或熱毒內蓄,引起氣機紊亂,導致陽氣偏盛,即“陽盛則熱”,故見發熱癥狀。

表2 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后第1h、6h、24h、48h、72h體溫比較(x-±s) ℃
小兒豉翹清熱顆粒具有疏風清熱、解表散邪之功效[6]。當患兒體溫達38.5℃及以上時加用布洛芬混懸液口服治療,以預防持續高熱可能造成的機體損害。
朱璉(1910—1978),現代針灸家,1960年創辦南寧市針灸研究所,著有《新針灸學》一書,此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針灸醫著。朱璉認為針灸之所以能治病,是由于激發和調整機體內部神經系統的調節機能及管制機能,病灶的信號過于興奮,就用抑制法治療,病灶的信號過于抑制,就用興奮法治療。所以治療方法就分為興奮法和抑制法,兩種手法通過進針手法、行針手法、出針手法、留針時間、取穴多少、刺激量等因素來區分。相較于其他針法,朱璉針法最大的特點有四個方面:進針手法、行針手法、留針時間及刺激量。進針手法:為快速捻進法,針尖平穩而輕盈地停在皮膚表面后快速捻轉迅速刺入,大腦皮層收到短促而強烈的刺激信號,大腦立即反應,患兒得到一個短促而強烈的體會。行針手法:以朱璉興奮Ⅰ型手法為主,即短促有力的捻轉結合高頻率的提插,患兒感受短促而強烈的酸、麻、脹、痛及觸電感,給大腦皮層一個強烈的刺激,這種強烈的刺激能通過局部穴位皮膚傳導至大腦皮層,能興奮對應的大腦皮層點,興奮信號通過神經路徑,由大腦皮層又傳導回局部穴位,引起局部穴位皮膚的興奮,故取名興奮法[7]。針感極其強烈,持續時間短促,在興奮法分型中此手法為興奮Ⅰ型手法。出針手法:在給予患兒足夠的刺激量之后,握持針柄抖動3次立刻出針,不留針。朱璉興奮型手法以短促而強烈的針感,調動人體的生理機能,解除過度抑制,喚起機體興奮,故每次針刺之后患兒都大汗淋漓,確能達到宣肺解表、疏風清熱的作用。
聯合耳尖放血療法,從中醫角度說,耳尖位于人體相對最高處,醫者發現患兒發熱的部位多集中于頭部,經反復揉搓耳廓,使耳廓發熱充血,有引熱走耳的作用,把患兒體內的熱邪通過揉搓引導至耳尖后點刺放血,因勢利導,使邪有出路,高熱得解。耳尖放血的時機,通常選擇在患兒體溫升至較高時,因夜間營衛入于陰,陰陽交爭,導致體溫升高,故選擇夜間放血,抓住時機,及時泄熱。熱邪隨血而出,不留于內;正氣內強,邪不敢留,故邪出徹底,從而使患兒高熱退后不升,病情不反復,快速恢復健康。
本研究結果表明藥物治療基礎上采用朱璉興奮針法聯合耳尖放血治療小兒風熱型外感發熱,能減少長時間、反復口服退熱藥的副作用,減少抗炎、抗病毒藥物的使用,在短期內有效降低患兒體溫,降溫效果持久而平穩,避免反復發熱的可能。本研究以針刺及放血為輔助治療手段,治療方法有痛感,讓部分患兒及家屬存在畏懼心理,因此治療方法的設計有待進一步改進,且本次研究樣本數量偏少,今后有待于進一步開展大樣本多中心聯合研究以明確療效。
[1] 汪受傳,虞堅爾.中醫兒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74.
[2] 張玉蘭.兒科學[M].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1:109.
[3] 黃從付,黃列虎,盧仕仰,等.小兒常用退熱藥的作用機理及不良反應[J].現代醫院,2011,11(5):40.
[4]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S].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74.
[5] 馬雪琴,李鵬.小兒豉翹清熱顆粒治療上呼吸道感染發熱療效分析[J].中國藥物與臨床,2013,13(S1):88.
[6] 袁斌,鄒建東,汪受傳,等.小兒豉翹清熱顆粒治療兒童感冒風熱夾滯證260例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J].中醫雜志,2017,58(3):228.
[7] 朱璉.新針灸學[M].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