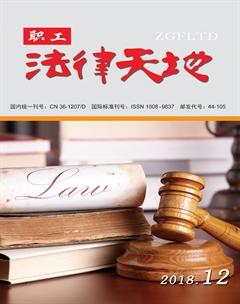論法治理念與法律思維
廖嘉怡
摘 要:法治原則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成為一種合理的文化共同體。這是現代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式的一個重要標志。法治原則是指在處理法律社會糾紛時,必須按照法律邏輯進行思考和決策。與其他思想相比,法律思維有重要區別,即以權利義務為線索,普遍性高于特殊性,合理性高于客觀性,形式理性高于實體理性。
關鍵詞:法制;法律至上;平等的權利;社會自治
一、法治原則和文化法治原則
在現代治國方略中被廣泛采用。它界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采取的基本形式,在這一點上,人們已經做出了一致的理解,然而,為了從根本上理解什么是法治,法治意味著什么,還必須從文化層面上講公理。
法治原則不能僅僅從制度層面來理解,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的角度,效果表明,現代文明是不同于以前的文明形式,在法治措施公認的社會成員之間,已成為一個基本文化的公理,維護社會合作,規范社會關系,社會糾紛和表達社會理想[1]。
法治作為一項基本的文化公理,體現了現代人類文明形式對公共生活規范和秩序的特殊理解。任何社會都需要一套通用的規則來規范人們的行為,需要建立公共權利來確認,制定和實施這些規則,它還需要一些保護和救濟手段。為個人追求其合法利益提供必要的機會。人類文明的所有形式在這些方面都是相同的。現代文明是獨一無二的,作為一般規則的法律和公共權利和個人權利,一個新的定義,使得權,利,法律三個基本的主題關系相互平衡,當前和過去的文明處于完全不同的狀態。
二、法律具有最高權利
在現代文明中,法律已不再是政府的秩序,而是一種具有社會慣例性質的共同規則,表達社會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相應地,權力不再顯示舊的政府對于一切事物的主導地位,使政府成為依靠法律的力量的主體,因此,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力量至上,成為政府的主人和存在的基礎。
(1)所有行使公共權力的機構都必須以法律為基礎進行思考和行動,權利在法律面前不是責任豁免的原因。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義務。其次,法律批準政府的力量,權利的依據及標準,即為法律,各種各樣的公共權利和行使權力的限制范圍完全取決于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慣例,需要有人來維護和執行公共機構和權力是必要的,合理的存在,尤其是因為它們保護和執行社會公約的必需品。如果權力違反法律,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2)在法治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將判斷社會問題,所有訪問成為公共權利保護和制裁任何恒定的標準。同時,所有的管理權力必須依法設立,依法行使評估和監督。因為法律是所有人的主人,因而我們都是自由平等的人[2]。
三、平等的權利
在過去的文明形式,權利是國家的控制器。其對個人的控制,取決于個性,價值理念同情心和社會形勢。在現代文明中,權力制度存在一個常數,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法律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此外,現代文明中權力的定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權力意味著法律上的平等對待,等級特權不是權利。因此,應當根據原則分配每個公民平等的權利。從而使他們能夠參與社會合作,體現法律的基本地位,和競爭法制原則。法律作為一個統一的標準,應當對所有人的利益行為和期待做出同樣的反應。這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公理。事實上,法治理論與法律基礎權力的概念有著內在的基本聯系。權利本位原則是現代法律制度有別于封建法律制度的根本標志。它要求平等權利的承認和保障。法律不是來自權利的限制與否定。而是來自權力的認識與肯定。馬克斯曾說,正如萬有引力定義不是運動的否定,而是運動的條件。所以定律不是自由的否定,而是自由的存在方式。因此,可以說在法治社會中,法律的本質不是壓制和約束,而是為平等權利的共存而創造條件。法與權的關系是流與源的關系。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3]。義務就是權力的物化。公共權利就是義務的物化。
四、社會自治
如果有人認為法治的實施是盡可能多的用法律來規范社會生活,盡可能廣泛地實施統一的強制性標準。那么他從根本上就誤解了法治的概念。雖然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但他并不意味著完全使用法律強制標準來排除當事人的獨立決定和協議。相反,法治需要建立在適當程度的社會自治的基礎上。所謂的社會自治,就是組成了社會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會主體這私人事務中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獨立行動,彼此不受外部因素影響干預。社會自治也被稱為私人自治:法治的概念是將社會事務分為兩個類別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在公共領域法律標準的強制性特征更多。至于在私人領域的標準,往往是領導的指導規則。社會作為私人主體的總和,完全處于公共權力和公共結構的控制之下[4]。
五、法制即為思維方式
法律之上體現了現代文明對法律的尊重,權利的平等和社會的自治。這就引出了什么樣的法律才是具有最高權威的問題。如果最高法是一個充滿差別精神待遇的法律或者是排除人的自治的法律。那么它只能是“法治”。也就是說有些人用法律來治理別人,而不是法治本身。從事物的外表來看,法治首先是社會治理的一種方式。然而,從文明的內在機制來看,法制應該如何實現?這存在于是否存在一種特定的社會生活方式,即在社會交往過程中,法律至上,平等權利,社會自治成為一種普遍的行為方式。法治只有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才能成為社會治理的相應方式。法制可以直接取得成功,取決于社會公眾和私人決策者普遍接受,適應法治概念思維模式。可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形成預期采取行動,評價,報酬是否承認和尊重按照結論形成的這種思維方式。尤其在結論計劃以及我們意志和利益沖突當中。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如果這些問題不能給予肯定的答復,只能說明法治的概念并沒有真正被這個人或者這個社會所接受。
參考文獻:
[1]王冠菲.論法治理念及其對當代中國的意義[D].海南大學,2017.
[2]田夢然.論法治思維與法律思維的關系[D].上海師范大學,2016.
[3]鄭齊猛.論法治思維[J].公民與法(法學版),2013(02):8-10.
[4]張靜煥.法治思維研究[D].吉林大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