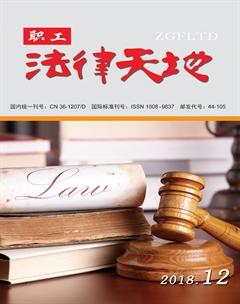對強制賠禮道歉的可行性探析
張洪智
摘 要:賠禮道歉作為社會人際關系的潤滑劑,可以對受害人精神損害的彌補及社會正義的弘揚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隨著適用范圍的擴大,也會因涉嫌對侵權人人格權的侵犯而遭到諸多詬病。尤其是在強制執行過程中,經常出現對侵權人人格侵犯和其他過激行為,有違賠禮道歉的初衷。
關鍵詞:強制;賠禮;道歉;可行性
賠禮道歉原本屬于道德范疇,是日常生活中常見而又重要的人際交往形式,它主要功能是使暫時破壞了的人際關系得到修復,而作為民事責任承擔方式的賠禮道歉被我國《民法通則》吸收后,使它穿上法律的外衣,浸透著法律的力量,讓它不在表現為生活中的一句輕松的“對不起”。眾所周知,法律責任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但是“賠禮道歉”這一民事責任在現實中如何實踐以及評判標準是什么?是否應當強制執行以及如何強制執行?這引發學界的激烈爭論。
一、賠禮道歉責任方式的內涵及立法意義
將賠禮道歉作為人格權受侵害時對受害人實施救濟的一種責任方式,是我國民事法律的創設。我國《民法通則》第120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的,適用前款規定。”
根據前款規定,我們可以看出,賠禮道歉是自然人和法人因人格權受侵害時,侵害人通過向受害人公開承認錯誤、表達歉意、請求原諒的方式來彌補受害人精神創傷的一種行為。筆者認為,賠禮道歉本質上屬于道德范疇,將其規定為一種民事責任,是為道德行為披上了一層法律的外衣。立法者將賠禮道歉規定為一種責任形式,是因為我國存在適用“賠禮道歉”的價值基礎。人們普遍認為,金錢并不能補償所有的損害。當一人的不當行為侵害了另一個人的身心時,人們的良心首先會對這個人的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而通過侵害人向受害人賠禮道歉這一責任形式,可以修復受害人因侵權行為造成的心理創傷,進而平復受害人憤恨的情緒,滿足大眾對于社會平衡狀態的期待,并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侵害人的負罪感和內疚情緒。事實上,“是與非”往往也是社會全體最為關注的,許多訴訟的產生并不是為了獲得經濟賠償,而在于通過訴訟,特別是通過賠禮道歉等責任形式,使得受害人找尋一定的心理平衡。從另一方面講,賠禮道歉責任形式也具有道德指向功能,它能通過個體效應引導社會成員自覺遵守社會規范、并積極向善。
二、賠禮道歉適用的法律困境以及能否強制執行
賠禮道歉作為一種責任形式,能否強制執行?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對此有頗多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賠禮道歉責任的功能及其合憲性或合理性兩個方面。
(一)關于賠禮道歉的功能實現方面
1.反對的觀點
(1)強制賠禮道歉違背了人民內心意思自治。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自由,在我們每個人侵犯到他人合法權益的時候,有多種懲罰方式可供選擇,如金錢賠償及其他方式,并非一定要通過賠禮道歉這一方式進行,有多重替代方式可供選擇。如強制要求加害人賠禮道歉,顯然違背其內心自由,同時,即使其通過其違背內心自由所作出的與內心相違背的道歉方式,也未必能達到受害人和社會大眾想要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2)道德歸道德,法律歸法律,強制賠禮道歉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按照我國法理學的相關觀點,法律與道德往往存在極其模糊的界限,如生活中常見的“見死不救”及近年來屢見不鮮的“旁觀者冷漠”的相關案例,我們往往無法用法律的手段去解決此類問題,畢竟法律不強人所難。但是如果把生活中常見的“對不起”上升為法律,要求強制賠禮道歉,那么就有可能把原本屬于道德范疇的道歉上升為法律,導致法律與道德界限不明,導致實務中無法適用。
(3)強制賠禮道歉沒有實現其救濟功能。如前所述,賠禮道歉如果是發自內心,真誠道歉,那么受害人可能會感受到加害人的真誠悔過而平復內心的憤恨,但是現實生活中,當法院判決賠禮道歉的時候,加害人是不愿意道歉,這個時候法院的強制執行手段是將該判決文書登錄報刊。其實這種方式未必能夠實現其救濟功能,相反還讓受害人不堪,更甚至于增加受害人的憤怒情緒,并未能實質性的解決社會矛盾,相反還會讓社會矛盾再升級。
2.支持的觀點
(1)賠禮道歉具有正當性。最好的法治是對權力進行最大的限制,而對人們自由進行適度的限制同樣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任何一個公民,當你的行為構成了對他人的侵害,勢必會受到相應的懲罰,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所以雖然強制賠禮道歉會侵害到加害人的自由,但是該強制手段是在法律規定的正當性范圍之內,也是在老百姓可容忍的范圍之內。故從這一角度出發,賠禮道歉就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也即可認同其強制的正當性。
(2)賠禮道歉的功能不容否認。雖然反對者認為,強制的賠禮道歉違背了加害人的內心自由,強制的賠禮道歉違背其內心,即使道歉,也是不真誠的,相反會給受害人二次傷害。但是,支持者認為,即便如此,強制賠禮道歉對于受害人和社會的效應依然存在。其認為,強制賠禮道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復受害人的心理創傷,對其精神損害是一種救濟,同時,對侵權人來說,賠禮道歉具有自我補償和道德恢復功能,為其悔過提供了一個表達的場域。對于社會來說,賠禮道歉具有道德整合、法律權威再建、懲罰和教育的功能。有的學者認為可以強制執行,現實中有的法院將富含賠禮道歉內容的判決書刊登在報刊等媒體上視為執行,筆者不贊同這種方式。賠禮道歉的特殊屬性使其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具有了以下兩層含義:第一,既然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那么賠禮道歉就具有了法律責任的強制力。侵害人不能自動履行時,受害者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第二,雖然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但究其本質仍是一種道德色彩濃厚的身份行為,因此只能由侵害人本人以話語形式親自(包括口頭、書面形式)向受害人作出,若侵害人不能自覺履行,法院不能強制執行,否則侵害了加害人的思想和良心自由。但是若無執行力,僅得依靠當事人的自覺行為實現,那么賠禮道歉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的意義將逐漸衰退。這也是賠禮道歉遭遇的法律困境。
(二)關于強制執行賠禮道歉是否違反合憲性及合理性方面
1.支持的觀點
我國憲法里專章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進行了描述,法理學上對于法律與道德也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根據上述兩個板塊的內容,有些學者認為,強制賠禮道歉違背了人權,侵犯了作為人權最基本的良心自由和表達自由,系對他人內心世界和道德觀念的強制。
2.反對的觀點
反對者認為,在這個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金錢賠償未必能夠實現人們所欲追求的保護利益。即便是金錢賠償了,也還是需要其作出賠禮道歉。實踐中更有一些案例,受害人不要金錢賠償,只需要賠禮道歉,而加害人只愿賠償金錢,不愿賠禮道歉,因此,雙方矛盾不斷升級。反對者認為,用賠禮道歉的方式更能讓受害人接受,平復內心。當然,賠禮道歉的執行不一定能夠達到受害人追求的效果,但是法律的強制履行更多的時候還是通過民眾的認同和自覺來完成。
3.折中的觀點
除了前述兩種觀點外,理論上還有另外一種觀點,基于二者之間,稱為折中的觀點。他們認為,賠禮道歉作為一種民事責任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實踐操作中,應慎之又慎,應嚴格限制其適用條件和界定范圍。比如,付翠英教授建議,判決賠禮道歉必須獲得侵權人的同意,并且非經其同意不得采用公開方式,此外,它僅能適用于主觀惡性大的案件。王利明教授也認為判決賠禮道歉應以侵權人自愿以及過錯嚴重為條件。
綜上,筆者認為,賠禮道歉基于其特殊性,不僅具有道德的屬性,同時也具有法律的相關屬性,但是,歸根到底,其仍是一項具有法律外殼的道德,必須依靠行為人的自愿行為才能完成,如強制執行,未能能實現其所欲追求的效果。若完全不尊重加害者的意思自由,強迫一方向另一方作出賠禮道歉的意思表示,則與市民社會所尊崇的意思自治原則相悖,市民社會也因此可能會陷入法律信仰的危機。因此,筆者認為,賠禮道歉必須是出自加害人自愿的。如果不考察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是否還有可能適用這一責任形式,而不顧一切強制加害者對受害者賠禮道歉,那么,即使懾于法律的權威或出于其他因素的考慮,由侵害人冷冰冰地對受害人說一聲“對不起”,那么當事人之間的怨恨并未因此而減少,相反,受害人獲得了不適當的心理滿足,對道歉者而言,則容易促使其形成功利主義的道歉觀,進而會培養出一批無信仰、無責任感和玩世不恭的偽君子,這是與賠禮道歉責任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馳的。
三、賠禮道歉責任方式的定位
鑒于賠禮道歉的特殊性質,應將賠禮道歉定位是一種補救性或者輔助性責任形式,可以單獨或者與其他責任形式并用。但是在與其他民事責任并用時,應慎之又慎,否則,不僅不能發揮賠禮道歉的作用,同時還會破壞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
首先,賠禮道歉的主張應當由受害人提出,在特殊的情況下,加害人也應當有一定的選擇權利。如前所述,賠禮道歉兼具法律與道德的雙方屬性,由受害者提出更符合其作為民事責任的法律功能。如在受害人未提出該請求時,人民法院則應該以不告不理的民事訴訟法的原則,依職權主動適用。但是,如果受害人在起訴時一旦提出,法院在審理前應征詢被告意見,同時,結合全案綜合考量后作出裁判,盡可能的在雙方自愿的情境下去選擇賠禮道歉的這一民事責任。
其次,人民法院在審理原告提起的要求賠禮道歉的訴訟時,應給結合全案證據,在明確責任劃分的時候,鼓勵被告自愿的賠禮道歉。盡量避免用強制執行的方式。雖然我國民法總則里規定有賠禮道歉的強制執行方式,但是,強制的賠禮道歉并不能實現其應有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價值。因此,在實務中,應對鼓勵當事人自愿履行,因為只有過錯人真誠的道歉,執行才有其應有之義,否則,背離其立法目的。
再次,賠禮道歉的執行,在征得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可選擇非公開場合進行。如受害人要求公開的,法院也應積極做其思想工作。因為賠禮道歉的功能實現是基于道歉者的真誠,這完全可以在僅有受害人和道歉人雙方在場的情況下進行,不一定要公開。因為人都有羞恥之心,如果強制道歉者進行公開道歉,那么其會產生抵觸情緒,相反會反目成仇,矛盾升級,不利于糾紛的解決。
最后,情節輕微不應成為賠禮道歉責任的適用條件,其應適用于主觀惡性大的行為。而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來看,卻恰恰是未造成嚴重后果的,法院可根據相關情形判令對方賠禮道歉,如最高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規定。由此可以看出,在立法者的眼里,賠禮道歉是相對較輕的一種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而現實生活中,大部分的當事人卻將賠禮道歉的承擔方式為“重罰”,特別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加害人,更愿意選擇金錢賠償來了解案件。
四、結語
綜上所述,賠禮道歉作為社會人際關系的潤滑劑,立法者將其作為一種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寫入法律,有其積極作用的一面,如可以對受害人的心理創傷進行修復,對社會的公平正義起到弘揚效果等。但是,通過全文分析和實踐中的相關案例來看,我國現階段對于強制賠禮道歉的這一民事責任的適用應慎之又慎,不僅應考慮加害人的情節和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心理,同時還應發揮裁判者的司法能動。避免其適用過寬或適用不當引發負面效應,從而積極的發揮其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李由義主編.民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頁.
[2]王利明主編.民法學[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頁.
[3]王利明主編.民法總則研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版,第299頁.
[4]張新寶主編.侵權責任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 373頁.
[5]黃忠.賠禮道歉的法律化: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實踐[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2期.
[6]王立峰.民事賠禮道歉的哲學分析[J].判解研究,2005 年第2 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頁.
[7]付翠英.論賠禮道歉民事責任方式的適用[J].河北法學,2008年第4期.
[8]王利明.侵權責任法研究上卷[M].中困人民大學出版社,20l0年版,第6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