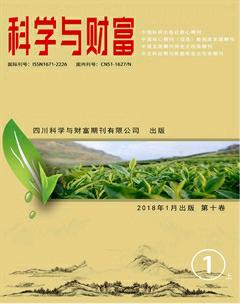杜詩之抑揚頓挫
裴巧麗
摘要:唐朝,尤其是盛唐,是詩歌發(fā)展的巔峰。生長在詩歌繁榮的唐朝的杜甫,不僅是唐詩的集大成者,還是唐詩的變革者。在詩歌的體裁上,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在詩歌的風格上,他“或清新,或奔放,或恬淡,或華瞻,或古樸,或質(zhì)拙,并不總是一副面孔,一種格調(diào)”; 在詩歌的語言上,他全面繼承了漢魏以來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精髓,在繼承中又有發(fā)展和變革,為唐詩藝術(shù)達到巔峰和唐詩的持續(xù)發(fā)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杜甫在對唐詩的發(fā)展與變革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沉郁頓挫”的風格,在詩歌語言表達上體現(xiàn)為抑揚頓挫的特點。
關(guān)鍵詞:杜甫;詩歌;抑揚頓挫
杜甫之前的唐詩,音調(diào)流亮、氣韻流暢是最重要的審美標準之一,也是代人作為唐朝詩歌風格的標志之一。唐朝詩歌發(fā)展直至杜甫,詩風為之大變,杜甫以“沉郁頓挫”風格自詡,“沉郁頓挫”也成為了后世詩壇對杜甫詩歌的公論。杜甫詩歌首創(chuàng)了違反常規(guī)的語言敘述方式,使詩歌失去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詩歌語言所追求的流暢性,而成為一種后人稱為的“澀”或者說是“沉郁頓挫”的風格,更加迂回生拗。杜甫的詩歌中多見語詞的倒裝,尤其是顏色字的倒裝。杜甫詩歌中的顏色字的倒裝有利于藝術(shù)的直覺沖擊,能起到突出第一眼的效果。倒裝的運用也有利于加強詩歌氣勢,追求打破詩歌流暢性,形成“沉郁頓挫”的藝術(shù)效果與藝術(shù)風格。
無論是杜甫自己,還是詩壇的的評價,論及杜甫詩歌的風格,都是以“沉郁頓挫”概括。那么,什么是“沉郁頓挫”呢?沉郁指的是文章的深沉蘊藉,頓挫則是指感情的抑揚曲折,語氣,音節(jié)的跌宕搖曳,沉郁的文章背后的情感通過頓挫的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出來。本文將探討杜甫詩歌語言的抑揚頓挫在詩歌語詞上的表現(xiàn)。
一、將中心詞置于句首
縱觀杜甫的詩歌,他的詩歌中描繪景物顏色所用之詞皆是常用詞,離不開“紅”、“綠”、“碧”等。杜甫每次將這些描繪景物顏色的常用詞置于句首,都能融化入境,成為點睛之筆。這得益于杜甫詩歌表達手法上的變幻多姿,以顏色詞置于詩句的第一字正是其中的一種。
比如:
翠深開斷壁,紅遠結(jié)飛樓。——《曉望白帝城》
青棤峰巒過,黃知桔柚來。——《放船》
我們來看這兩句詩,詩句中的顏色詞“翠”、“紅”、“青”、“黃”,皆是顏色詞中的常用詞,杜甫將這些顏色詞放于句首,達到了突出了所描寫的事物的特征的效果。而且,顏色詞位于句首,對閱讀者來說,造成了閱讀的新鮮感。若將“翠深開斷壁,紅遠結(jié)飛樓”詩句中的顏色詞調(diào)換位置,不將顏色詞放于句首,改為“深翠開斷壁,遠紅結(jié)飛樓”,詩句“青棤峰巒過,黃知桔柚來”亦然,改為“棤青峰巒過,知黃桔柚來”,詩句便少卻了在閱讀第一時間帶給讀者的氣勢和視覺上的沖擊,流于平庸化。
在杜甫的詩歌中,提至句首的不止顏色詞,也有副詞、形容詞之類。
比如:
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不寐》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奉岑參補闕見贈》
楊枝晨在手,豆子雨已熟。——《別贊上人》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杜甫運用倒裝手法,改變了敘述的語序,將有價值、有表現(xiàn)力的詞語置于句首,下筆有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又有新鮮的美感。杜甫的這種倒裝,將中心詞前置,使詩句的起首詞成為詩句的重心所在,使詩句的表達更具力度,這也是杜甫詩歌的一種創(chuàng)造。
二、將長句變?yōu)槎叹?/p>
杜甫的詩歌中,倒裝手法的運用還體現(xiàn)在將原本較長的敘述句,通過倒裝手法變?yōu)槎叹洹_@多體現(xiàn)在律詩中,使律詩的表達更加集中,詩句顯得短促有力,音節(jié)也顯得頓挫有致。
比如: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倦夜》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遣意》
在上面例舉的詩句中,“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原本正常的敘述順序為“螢暗飛自照,鳥水宿相呼”,是兩個完整的敘述句。而杜甫運用倒裝,將動作詞前置,使一個順暢的敘述句變?yōu)閮蓚€短句,“(螢)暗飛”和“(螢)自照”,句式的變短使表達上更為有力強勁,同時打破了傳統(tǒng)詩歌句式敘述的流暢。
同樣在詩句“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中,我們通過閱讀理解便可知道,詩人也是將原本“黃鳥囀枝近,白鷗泛渚輕”的敘述順序改變,變?yōu)椤埃S鳥)囀枝”和“黃鳥近”,“(白鷗)泛渚”和“白鷗輕”的敘述短句。
除此之外:
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觀李固》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中宵》
失學任愚子,無家任老身。——《不離西閣》
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法鏡寺》
杜甫詩歌中的此類倒裝,數(shù)量不在少數(shù)。這類詩歌的創(chuàng)作原因,除了格律上的要求以外,也是詩人創(chuàng)作時的藝術(shù)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人,在具體詩句上尋求氣勢的強勁,語句的鏗鏘。
三、改變閱讀順序,制造閱讀障礙
杜甫的詩歌中,倒裝手法運用的頻繁,改變了詩句語詞敘述的順序,打破傳統(tǒng)詩歌句式敘述的流暢性,改變了閱讀順序,制造了閱讀障礙。杜甫詩歌中倒裝手法的運用延長了讀者的閱讀心理認知時間,造成詩歌語言的“陌生化”效果。
比如:“重碧拈春酒,輕紅挈荔枝”(《晏戎州》),詩句原本的敘述順序是“拈重碧春酒,挈輕紅荔枝”,傳統(tǒng)的流暢性敘述順序是主謂賓,但杜甫偏要將其倒置,使其違反慣常的敘述順序,詩句讀起來十分拗口。但詩人這樣做,一方面是詩歌格律的要求,另一方面延長了詩歌的閱讀認知過程,使原本流于平庸的詩句具有了回環(huán)不盡的美感。“拈重碧春酒,挈輕紅荔枝”,固然具有傳統(tǒng)詩歌敘述上的流暢性,但敘述的流暢清晰,使讀者讀來一目了然,閱讀認知過程也隨之縮短,詩句流于平泛。而詩句“重碧拈春酒,輕紅挈荔枝”,將“重碧”“輕紅”置于句首,這種語序上的調(diào)換形成了閱讀上的困難,使杜甫的詩歌有“古拗”之稱。這不僅是音律上的拗,還有反常規(guī)的敘述順序所造成的閱讀認知過程中的艱澀。“重碧拈春酒,輕紅挈荔枝”,對傳統(tǒng)詩歌敘述流暢性的破壞,改變了傳統(tǒng)的流暢性敘述順序,也打破了讀者慣常的閱讀順序,形成了閱讀認知障礙,讀者對詩歌的閱讀認知過程被拉長,。這不僅延長了閱讀認知過程,延長了閱讀認知時間,還增加了詩歌詩句的審美價值,形成詩歌語言上的“陌生化”效果。
嚴羽評價盛唐詩歌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唐代詩歌整體上表現(xiàn)為玲瓏剔透,和諧典雅的特征,這也是傳統(tǒng)詩歌所追求的和諧典雅美。而杜甫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經(jīng)常使用反常規(guī)的敘述順序,形成了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既下筆有力,又造成語序,語意上的曲折,延長讀者的閱讀認知過程。因為杜甫對詩歌格律和詩歌創(chuàng)作中用詞有力與語調(diào)鏗鏘的追求,傳統(tǒng)詩歌中的流暢性敘述順序被打破,唐詩中原有的對音調(diào)的流亮,內(nèi)在氣韻流暢的要求在杜甫這里得到了時代性的變革,這也成就了杜甫詩歌“沉郁頓挫”的風格。
沉郁頓挫。沉郁,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的解釋為:形低沉郁悶;頓挫,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的解釋為:動(語調(diào)、音律等)停頓轉(zhuǎn)折。“沉郁頓挫”在文學史上指杜甫詩歌的風格特征。杜甫詩歌的“沉郁”,通過“頓挫”的藝術(shù)形式表現(xiàn)。杜甫的詩歌,蘊含著一種厚積薄發(fā)的感情力量,每欲噴薄而出時,杜甫的仁者之心,儒家涵養(yǎng)所形成的中和的處事心態(tài),便將這種欲要噴薄而出的感情抑制住了,使他變得緩慢回環(huán),跌宕起伏,使他的詩歌變得緩慢回環(huán),跌宕起伏,是為沉郁頓挫,是為抑揚頓挫。
參考文獻:
①張忠綱.《杜甫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8.第83頁.
②方慧穎.《杜甫詩法研究》.廣西師范大學.2008.4.
③王歡.《錢謙益與杜甫詩法淺探》.復旦大學.2007.5.
④諸舒鵬.《杜甫與唐代唱和詩演變》.西南大學.2016.4.
⑤趙相仲.《論宋詩話對杜甫詩學思想的接受》.山東師范大學.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