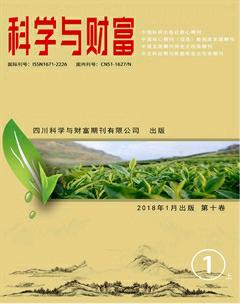橫看成嶺側成峰
王徐
摘要:王士禎是清代著名的詩論家和大詩人,論詩倡導“神韻”說,并在此理論上創作出大量“神韻”詩,開創神韻派,從而改變了清初詩壇依傍前人,在學唐或是學宋問題上爭論不休的風氣,主文壇近五十年,被譽為“一代宗匠”。本文擬從語言及主題兩個層面來探究王士禎的詩歌是如何體現“神韻”說的。
關鍵詞:“神韻”說;清秀;朦朧
引言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他是清代著名的詩論家和大詩人,“在康熙朝,號稱一代宗匠,以神韻倡導天下者,近五十年,以論其詩,則所謂興到神會之作”。所選《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獨以王維壓卷。錢牧齋曰:“貽上之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
一、語言流暢清秀
(一)韻律
王士禎的詩歌讀來往往朗朗上口,顯得韻律和諧,流暢通達,這與他在音韻學的造詣是分不開的。他至今流傳于世的詩律專著有《律詩定體》和《古詩平仄論》。他在這方面的揣摩研究使得其詩歌擁有“鏗鏘的聲調和圓美的旋律”,如“而今明月空如水,不見青溪長板橋”(《秦淮雜詩》其十二)、“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秋柳四首》其一)、“江鄉春事最堪憐,寒食清明欲禁煙”(《真州絕句》其五)等。陳衍曾說“(漁洋七古)湊成一種新聲調,無一首不鏗鏘可聽,故能震蕩一時。”他認為王士禎的七言絕句之所以讀來這么可愛,都是因為它擁有激揚的音節。
(二)意象
王士禎的詩歌之所以能給人清秀的感覺主要體現在意象的選擇上。
王士禎七言絕句中“秋”的意象特別多,其中有許多直接用到“秋”字的詩句,如“揚子秋殘暮雨時”(《江上望青山憶舊二首》其一),“煙雨秋深暗白波”(《江上二首》其二)等等,有時也寫到春天,卻有“濃春煙景似殘秋”(《秦淮雜詩》其一)的感慨。秋天常給人清爽的感覺,故秋天常稱“清秋”。與“悲秋”的詩人不同,王士禎詩歌中常借秋天的寂寥來抒發時光消逝的淡淡悵然感。
王士禎七言絕句中“細雨”意象也常出現,如“寒雨秦郵夜泊船”(《高郵雨泊》)、“長樂坡前雨似塵”(《灞橋寄內二首》其一)等,詩中多為蒙蒙細雨,而非狂風驟雨,讓人感覺到“清”的意味。
為了給人以“清”的感覺,王士禎還多愿意選取具有“清香”的花和具有“清音”的鐘聲,如“一樹寒梅作意香”(《絕句》)、“撐船直入花深處,云葉當頭山雨來”(《滸山濼二首》其二)和“疏鐘夜火寒山寺,記過楓橋第幾橋”(《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其一)等。
這些意象的共同特點是清新淡雅,而閑適干凈的意象就是構成詩歌“清秀”的載體之一。
二、主題朦朧含蓄
“神韻”說最大的特點就是主題的朦朧含蓄,所以王士禎的詩歌到底在寫什么歷來是后人爭論的焦點。
趙執信曾在《談龍錄》中抨擊王士禎《南海集》中諸詩“詩中無人”。對此,有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王士禎“詩中無人”主要表現在“詩中很少出現抒情詩人的自我形象,很少表現詩人獨有的性情面目,讀者很難從其詩中窺見其內心生活的深層內容”。
在那個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一個普通人尚且謹言慎行,更何況是王士禎?作為一個與前朝遺老有諸多瓜葛的人,一舉一動都不得不謹小慎微,這大概是王士禎詩歌主題撲朔迷離的原因之一吧。
秋柳四章(其一)
秋來何處最銷魂?殘照西風白下門。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煙痕。
愁生陌上黃聰曲,夢遠江南烏夜村。
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王士禎作《秋柳四章》之后,一時和者“數百家”,和作“幾千首”,各種注釋不勝枚舉。但詩歌背后的寓意數百年來各家一直爭論不休,尚未定數。
認為此作抒發的是故國之思的論者援引前朝事跡對上面詩句逐一加以引申論證,而對此觀點持否定者則認為此作僅是詠物之作或認為其抒發的是歷史的盛衰之感。有人說它是憑吊故國滅亡之作,也有人說它是感慨良辰易逝,又有人說它是嘆息佳人淪落,還有人甚至說它關涉抗清斗爭……
論者認為其中可取的觀點是王利民所提出的“由故國之思泛化而來的兆示著詩風轉變的盛衰之感” 。當時他和許多名士在濟南大明湖聚會,見湖畔“楊柳十余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乃“悵然有感,賦詩四章”(文據《菜根堂詩集》引)。詩人作此詩時,正值雙十年華,他以青春的浪漫才情將憔悴的自然景物賦予傷逝的人生悲戚之嘆,使此詩顯得意旨隱晦而情韻深遠。詩中既表現了對前朝風流的追慕,又有意識的將追慕之情淡化,反映出“歷史轉折時期詩人對現實政治若即若離的心態” 。
然而各種說法都很難真正坐實。但王士禎恰恰是有意用這種朦朧的表現形式,讓人將作品看不真切想不明白,從而引起多方讀者的想象,使之產生共鳴,以此吸引應和者和解讀者。當時不僅徐夜、顧炎武等遺民詩人紛紛唱和,連王路卿、李季嫻等閨閣詩人都有和作,可見這場清初詩壇的大唱和可謂空前絕后。這樣的境況使得王士禎一時無兩,名聲大噪,此時他就可以推出他的“神韻”說了。
冶春絕句(其七)
三月韶光畫不成,尋春步偞可伶生。
青蕪不見隋宮殿,一種垂楊萬古情。
此詩上句熱情謳歌了揚州的美麗風光,下句又情不自禁地感慨逝去的隋煬帝。但它所表達的卻是一種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代代的王朝就好像過眼云煙,類似于“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之悲涼無奈感。
對此,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認為:“漁洋在揚州期間的創作,一個潛在的主題乃是青春和才性。作者在詩中正面描寫是眼中的江南山水,然而那歡欣的意趣、那如夢的意境、那流動的韻律當中讀者感受到的不恰恰是對青春的歌頌么?這也是一種感覺的世界,是作者心里的青春情懷與外在的明麗風光相對應后產生的藝術世界。”
而王利民卻在《王士禎詩歌研究》中表明:“《冶春絕句》歌詠的就是‘衰亡與新生,它用駘蕩的春色掩蓋墓園和戰痕,擺脫了惆悵的情調,描繪了一個賞心悅目的煙花揚州。” 王利民認為王士禎是想借助這些文化符號,將故國之思消弭在對前賢的文采風流的想象中。
驪山懷古(其七)
不復黃衫舞馬床,更無片段荔支筐。
只余今古青山色,留與詩人吊夕陽。
王利民曾在《王士禎詩歌研究》中表明,“王士禎的懷古七絕借鑒了李商隱對事理與情景的處理方式,寓理于事,寓情于景,饒有情味” 。而這首《驪山懷古》,表面上是用輕松的語氣調侃歷代君王的風流韻事,而實際上卻能品味出詩中的諷刺意味。
王士禎在構建懷古詩歌時,常常將懷古的悵然之感與蒼茫自然景觀融合在一起。顯示出自然的無盡、歷史的流逝和人類的渺小。詩歌同樣以自然景致作結,寓理于事,寓情于景,營造出了情韻深遠、余味無窮的審美體驗。
結語
王士禎以“神韻”說主持清初詩壇數十年,“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開創神韻派,從而將清初詩壇激烈慷慨、“分唐界宋”的風氣引上新的道路,代表了當時詩歌發展的主流,其對語言及主題的要求同時也對后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王小舒:《神韻詩學論稿》,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民:《王士禎詩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3]朱則杰:《清詩選評》,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4]李維:《中國詩史》,長春:吉林出版社2013年版.
[5]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趙執信:《談龍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7]錢謙益:《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