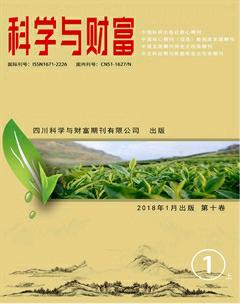論作家背景對文本的制約
李玉潔
摘要:一篇文章內容,立意,選材都是離不開作者生活的社會歷史背景,在社會歷史的大環境下,作者的思維會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政策、以及文學史的壓力的影響,所以一篇文本不論從選材、立意和社會影響等各個角度來看,都是由作者所處的生活大環境所決定的,《詩大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行于言”。作者的思想決定文本的內容,而作者的思想又是經過社會歷史環境塑造出來的,所以,作家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會制約影響著文本的方方面面。以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為例,不論是其選材,立意以及社會影響等哪一個方面,都受王羲之所處的時代背景(東晉)的影響。
關鍵詞:立意;選材;社會影響;東晉玄學歷史背景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提出過文學活動由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個要素組成(《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各要素之間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中作者是文學生產的主體,他不單是寫作作品的人,更是以自己對世界的獨特審美體驗通過作品傳達給讀者的主體,文學活動也是一種作者的感情表現活動。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學批評方法也是以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為核心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作者的經歷、背景對文本的題材、立意、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都具有很強的影響。
首先,作者的所處的時代背景對文本的選材方面有深刻的影響。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的選材是選自于文人雅士做禊禮這件事(也就是古人的一種春游活動),整篇文章使在記敘這件事,為事而著,進而抒發自己的一些人生體悟,這樣的文章與作者所處的事件的事實息息相關,所以紀實是一大特點。后文中提到的“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等等對于生命哲學問題的探索都與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深刻的聯系。其一,作者身處東晉時期,東晉時期清談之風盛行,有了這樣的社會風尚所也文人雅士才會常常聚在一起討論文學哲學等方面的內容,這樣的社會背景給《蘭亭集序》的選材提供了事實基礎。其二,東晉時期,文人雅士由于對政治的失望而轉向崇拜老莊哲學,所以,文中會出現對生命問題的探討,流露出“豈不痛哉”、“悲夫”等情緒。所以,作者所處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應時而生的社會風尚或者是引發的社會事件為文章的寫作提供了一個素材,而這樣的素材,往往能夠制約影響一段時期或者是一個朝代的作家的創作風格。
其次,作者所處的社會背景會影響文本的立意。《蘭亭集序》當中,作者王羲之為什么由開始的“信可樂也”的“樂”轉向后來的“痛”與“悲”,這樣一個情感變化也與作者所處的歷史時期有著直接的關系。作者的文本立意在于對生命宇宙問題的探索,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探索呢,為什么又會有情緒的不斷變化呢,首先,經歷了正始太康時期政治局面的變化,文人雅士由開始的積極報國建功立業的心理滿滿轉向對政權的失望,變成“隱士”,但是這樣的隱士并不是真正的出世的超脫的心理,所以,內心的追求與現實的巨大的反差讓這些心懷天下的文人內心極度的苦悶,他們轉向對老莊哲學的推崇,轉向對生命問題的探討,但是這樣的內心與老莊真正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唯一”的超然世外的生命態度還是有差別,所以作者會因為“所之既倦”、“所欲已陳”、“終期于盡”而悲嘆。其次,正是因為心理的矛盾,不能真正的融入老莊哲學的原因,才會有“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這樣的頓悟。顯然,作者這樣的思想是與莊子“齊物我”“齊生死”的生命觀是相悖的,《莊子逍遙游》中提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齊物論》當中也提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殀,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唯一。”這樣的生命觀在《德充符》、《大宗師》里面也多次提到過,那么既然崇尚老莊哲學,鐘情于超脫的世界觀,那么作則為什么又要提到“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呢?這個其實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文人對政權的失望,在文人階層迷漫著消極悲觀的情緒,而作者在文本中也提到了各種令人悲痛的事實,但是,王羲之卻沒有沉淪下去,他的思想在這一刻有了頓悟,從虛妄的空談當中超脫出來了,他認為人生不應該消極悲觀,而應該積極進取才能幸福快樂。《古文觀止》提到關于《蘭亭集序》這篇文章是這樣說的“: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上,只為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死生齊彭殤,無經濟大略,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曠達人,故雖蒼涼感慨之中,自有無窮逸趣。”所以作者的悲哀的情緒并不失消極的,而是立足于當時社會的現狀以及自己的經歷而產生的一種超脫的頓悟。
最后,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還會影響文本的社會影響。一篇問能能否引起社會的共鳴,能否流傳千古與其社會影響息息相關,如果一篇文文章沒能夠引發當時的或者是后來的人的情感共鳴,是不可能對社會、對歷史產生多的影響的,王羲之在文本當中提到過:“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這樣的預測并不是空談的,因為在后來的文章中就已經有了印證,作者的思想與后人產生了共鳴,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就提到:“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這樣一種感嘆時光流逝,這種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的感慨在世世代代的文人騷客的思想中都是存在的,每個時代有著不同社會歷史背景,有著不同的風俗民情,但是對生命哲學的探討,卻是古今文人的一個共同點,在安樂的太平盛世,這樣對生命的思索可能會少一點,但是在國運艱難,政權動蕩,社會理想普遍失落的年代,這樣對生命的探尋更是不乏其例。王羲之為東晉人士,兩晉政治恐怖,統治集團內部互相傾軋、殘殺現象時有發生。士大夫不滿,普遍崇尚老莊,追求清靜無為自由放任的生活。玄學盛行,對士人的思想,生活以及文學創作都產生了很復雜的影響。文學創作內容消沉,出世入仙和逃避現實的情調很濃。王羲之卻一反“清虛寡欲,尤善玄言”的風氣和追求駢體的形式主義風氣,抒寫了這篇情真語篤,樸素自然的優美散文《蘭亭集序》,又是與文人賢士們聚會之作,有著“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傳播基礎,自然一寫出便能在當時的流傳出去,而文人們普遍的消極情緒,在看到《蘭亭集序》這篇情感真摯的散文時,自然能夠引發不少人心中的共鳴,所以,這篇文章能夠有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流傳甚廣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遺失在歷史的洪流中國,并且在當今時下,也是一片中學生必學的文章之一。
參考文獻:
1.《詩大序》
2.《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
3.《蘭亭集序》王羲之
4.《莊子逍遙游》中華書局
5.《齊物論》中華書局
6.《德充符》中華書局
7.《大宗師》中華書局
8.《古文觀止》
9.《滕王閣序》王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