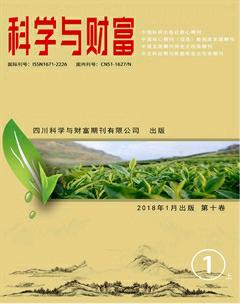淺析《詩經》棄婦詩中的棄婦形象
江莎莎
摘要:本文主要是具體分析《詩經》棄婦詩中的棄婦形象,并進一步探求其成棄婦的原因以及從中展現出《詩經》時代女性的社會處境。
關鍵詞:《詩經》;棄婦詩;棄婦;原因;女性地位
《詩經》,原稱《詩》或《詩三百》,它總共收錄了三百零五首詩。據相關資料考證這些詩歌創作于西周早期到春秋中葉。在三百零五首詩中,被古今人判定為棄婦詩的至少十四首以上,在《詩經》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且《詩經》作為棄婦詩的源頭,我們以此作為切口探尋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態,尤其是當時女性在社會中的狀態。
一、《詩經》中的棄婦詩
《詩經》中的棄婦詩篇歷來就存有爭議,筆者認為《詩經》中有十五首棄婦詩--《小雅·我行其野》、《小雅·黃鳥》、《小雅·谷風》、《小雅·白華》《小雅·何人斯》,《秦風·晨風》,《鄭風·遵大路》,《衛風·氓》、《衛風·河廣》,《王風·中谷有萑》,《召南·江有汜》,《邶風·綠衣》、《邶風·日月》、《邶風·終風》、《邶風·谷風》。
以上多采用《毛詩序》對《詩經》棄婦詩的界定,部分內容引后世學者之言加以論證。
二、棄婦形象分析
(一)委曲求全
《鄭風·遵大路》,清人郝懿行對該詩的理解是:“民間夫婦反目,夫怒欲去,婦懼而挽之。”(《詩問七卷》)詩中女主人公不斷苦苦地哀求:“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無我魗兮,不寁好也”,乞盼丈夫回心轉意。《邶風·終風》的女主人公面對丈夫的拋棄也依舊還懷有僥幸心理希冀丈夫回心轉意,思念之下輾轉難眠,妄想著“愿言則嚏”,“愿言則懷”。《邶風·谷風》也是如此,詩中女主人公被丈夫趕出家門,臨行前她還念叨著“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希冀丈夫改變心意--“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二)敢愛敢恨
《邶風·日月》,女主人公呼天告地,申述自己的感情沒能得到丈夫的回應,怨恨丈夫不把自己放在心上,譴責丈夫心志回惑、三心二意、“德音無良”、品行不端。《小雅?何人斯》中的女子,在長夜不眠、焦灼“反側”之中,對負心人更是發出痛徹心扉的詛咒:“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醌面目,視人罔極。”《召南·江有汜》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子。她直截了當地預言:丈夫如今的背棄行為,往后勢必在感情上遭到自我懲罰,即“其后也悔”、“其后也處”、“其嘯也歌”。
(三)認清現實,尋求新生。
《衛風·氓》中的女主人公,回憶同氓從相識(“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相戀(“及而偕老”,“信誓旦旦”)、相思(“抱布貿絲”,“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談婚論嫁(“來即我謀”,“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迎娶(“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三歲為婦勤勤懇懇的勞作發家致富到丈夫三心二意的不幸遭遇,最后果斷的做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定。她為自己失去的愛情而發出哀怨,但是她沒有一直沉浸其中,沒有絕望。她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告別自己上一段愛情和婚姻,新的生活已悄然開始,日子還得繼續過下去,并且要活得與過去不同,活得精彩、活得有價值。又如《王風·中谷有萑》中這位女子也是擇偶失慎,終究被丈夫無情地拋棄了。被丈夫拋棄后,她并無一味地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體悟了“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教誨,對人生進行深刻的反思。她所體悟到的正是對過去不幸婚姻生活的決斷,也是對今后新的生活的警示,同時也是對其他女子的提醒。
三、從被棄的原因看當時女性的地位
從《詩經》棄婦詩中我們可看到女子被棄原因主要是是女子年老色衰,男子喜新厭舊。如《衛風·氓》,漢代《毛詩序》云:“刺時也。宣公之時,禮儀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奔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它把《氓》中的女主人公說成咎由自取,只不過是替男子辯護罷了。從《衛風·氓》原文出發去解析,他們的婚姻是有感情基礎的,且禮儀上是通過明媒正娶的,也就不存在淫奔之說,明顯氓在家庭漸富時暴露了他真實的面目--“士二其行”“士也罔極”,喜新厭舊本色暴露無遺。
(一)男子出妻特權
從《詩經》棄婦詩的大量出現可以看出女子在社會上處于弱者的地位,受男權社會的束縛。從奴隸社會開始,男子在社會上的地位與日俱增,男權制度不斷加強鞏固。男子處于支配地位,而女子成為男子的附屬品居于從屬地位。女子的經濟地位不獨立,生活空間被束縛,她們依附于男子,往往顯得十分癡情。《鄭風·遵大路》、《邶風·終風》、《邶風·谷風》等篇目中女主人公希冀丈夫能夠回心轉意的癡情也就不難理解了。《小雅?斯干》就有“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之語。從出生的時候,男女就分別被貼上了尊卑、貴賤的標簽,享受著不同的待遇男為尊,女為卑。于是,即使男女間的婚姻有自由相戀的感情作為基礎,但男女性別的權益差別無法消弭,因此由愛情出發所凝結的婚姻很大程度上也會以失敗告終。那時的男子可以多娶與再娶,可以任意休棄妻子,這就造成了一出出家庭悲劇。《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從《詩經》中的棄婦詩中,我們可以看到男子輕易就可以出妻,出妻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齊國宰相管仲,為限定仳離,《管子?小匡篇》有“士三出妻,逐之境外;女子三嫁,入于舂谷”的規定。由此可見當時男子出妻有過于泛濫之嫌,朝三暮四、喜新厭舊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引發了社會問題,齊相管仲不得不以法令的方式限制此現象。
(二)女子相對自由
《詩經》時代對女性的束縛遠遠不如后世嚴酷,那時沒有“三綱五常”的嚴苛束縛,也沒有處女崇拜的貞潔觀念。“自由戀愛”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許的,女子被棄后也是可以再嫁而不受歧視的。《周易·咸卦》云:“咸,亨利貞,取女吉。”《周易·彖》云:“咸,敢也,柔上而則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我們從《周易》中可見,男女結合為夫婦是男女你情我愿的結果,是以雙方情感為基礎的,而非后世傳宗接代的社會義務。《詩經》中大量的愛情詩,敘寫男女之間相識、相戀、相愛。當時的女性對于愛情是大膽而主動的,如《摽有梅》中的女主人公直言“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那時的男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自由戀愛,《鄭風·溱洧》描寫了男女相會的場所,男女自由接觸,互表愛慕之心;《衛風·氓》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同氓先了解彼此,然后才相戀,再到談婚論嫁。《衛風·氓》中的女主人公婚后認清了氓的真實面目敢于下定“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心,她哀嘆已經逝去的愛情,怨恨氓的“二三其德”,但是她沒有對婚姻絕望,對自己的人生絕望。我們可以思考她能有這樣的決心反而是女性自主意識的體現,不因被丈夫背棄而委曲求全、痛不欲生,離開氓自己照樣能好好生活,離開氓反而是對“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這樣不幸生活的解脫。
參考文獻:
[1]王秀梅譯注:《詩經》,北京:中華書局,2015.9。
[2]陳奐:《毛詩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6。
[3]方玉潤:《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2。
[4]金性堯:《閑坐說詩經》,北京:中華書局,2004.1。
[5]黃仕忠:《婚變、道德與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7。
[6]陶琳:《詩經》中的女性形象,博士學位論文,浙江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