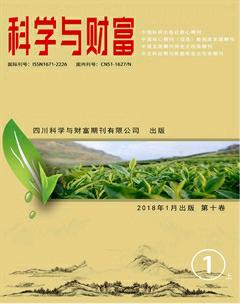關于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及權利實現機制的研究
曹熙喆
摘要:對于胎兒民事權利的討論,事實上是一個對人身權的延伸法律保護問題的重要法理問題。明確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胎兒應有的民事權益。文章介紹了法律上的“胎兒”的含義和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法律性質,分析了胎兒民事權利的實現機制,希望能為相關人士提供一定參考。
關鍵詞:胎兒;民事權利;機制
前言
隨著我國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風險因素在逐漸增多,司法實踐中胎兒損害賠償案的數量也在逐年上升,所以,保護好胎兒的合法利益是非常有必要的。現階段,我國對胎兒民事權利保護還在理論階段,還存在諸多的不足。所以,相關人員需要結合我國的國情,將胎兒的民事權利范圍及救濟途徑等內容進行明確,進而給予胎兒應有的權利保障。
1“胎兒”的含義
1.1各種辭書中“胎兒”的含義
第一,《中國醫學百科全書》中將“胎兒”解釋為自孕前末次月經的第一天算起,處于8周以內的孕體可以成為胚胎,8周-足月的可以成為胎兒。當孕體處于胚胎階段,起器官結構均已完成分化。在胎兒期間會繼續發育,直至成熟;第二,《人類學辭典》中將“胎兒”解釋為除產卵動物之外的哺乳動物在母體子宮內發育期間已經形成各主要器官和組織原基的胚胎。然后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育,自妊娠第六周后胚胎開始呈現人的形態,至第八周后開始稱為胎兒;第三,《中國百科大辭典》中將“胎兒”解釋為受精卵發育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兩周內稱為孕卵,2周-8周稱為胚胎,8周-分娩前為胎兒;第四,《人口科學辭典》中將“胎兒”解釋為孕后8周-娩出前胚胎所分化成的初顯人體規模的幼體;第五,《衛生學大辭典》中將“胎兒”解釋為從妊娠3個月-出生前這一斷時期的懷孕產物;第六,《心理咨詢大百科全書》中將“胎兒”解釋為從懷孕的第三個月開始直到出生,在母體內發育著的個體;第七,《麥克米倫百科全書》中將“胎兒”解釋為妊娠9周-出生前在母體子宮內生長的嬰兒;《兒科學辭典》中將“胎兒”解釋為受孕-娩出之前的小兒。
1.2法律上的“胎兒”的含義
現階段,對于“胎兒”的定義解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雖然“胎兒”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上是一個法律概念,但卻未對胎兒的含義進行明確規定。有法學辭書將胎兒界定為“尚未脫離母體的未來的民事主體”。雖部分地闡明了胎兒的法律屬性,但卻未揭明胎兒的任何客觀物質屬性。所以,法律上胎兒的界定需要理清胎兒的本質屬性:第一,胎兒的始期。從受孕開始,即標志著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法律對胎兒利益的保護,相關法律需要將此階段作為新生命開始,可以將“受孕時”作為胎兒的始期;第二,胎兒的終期。相關法律需要將“出生”作為胎兒期的終期,“自然人”是始于出生的人;第三,胎兒的獨立性與依附性。從生理學的角度看,胎兒對母體確實具有依附性,無法脫離母體而獨活作為胎兒的始期。從生命倫理的角度看,胎兒無疑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母體僅具有載體的意義。所以,胎兒的保護,不僅僅是母體的身體權的保護,還是胎兒自身利益的保護;第四,體外受精的胎兒屬性。經人工受孕方法而已經形成的胚胎,在植入母體之前,其法律地位也是胎兒;第五,冷凍胚胎的非胎兒屬性。當某一枚冷凍胚胎被以移植為目的而解凍,其成功解凍后符合移植條件時,即成為胎兒;而在冷凍保存期間的胚胎,則不具有胎兒屬性,其應被視為受法律特殊保護的一種“物”。
2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法律性質
2.1胎兒娩出時為死體
不論是概括主義還是列舉主義,凡是肯定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立法例,都無一例外地為胎兒民事權利能力之取得設定了法定條件,此即“活體出生”對于胎兒娩出時為死體是需要除條件還是停止條件,我國法采取的是附法定的解除條件說觀點,認為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受孕,在整個胎兒期就已經享有民事權利能力,只是在出生時為死產者,則溯及至受孕時喪失民事權利能力。我國立法選擇了概括主義立法模式,當然在解釋上也應當選擇附法定解除條件說,以便周全地保護胎兒利益,最大限度地實現胎兒權利保護。
2.2胎兒的義務能力問題:胎兒是否須承擔民事義務
民事權利能力是指民事主體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能力,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與“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雖然同屬民事權利能力的范疇,但這二種民事權利能力還是存在著差異的。其中,“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僅指胎兒依法享有民事權利的能力,即便是某人為胎兒的利益而付出了費用,如在母腹中為胎兒實施手術,手術費的負擔主體也不是胎兒。另外,我國現行法也在“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之外,創設了一種“只享有權利不承擔義務的特殊民事主體”的例外,此特殊民事主體即為胎兒。此種創設,旨在給予胎兒以特殊保護,立法政策正當,其作為“例外”,也不會對既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主體制度造成沖擊,是科學可行的。
3胎兒民事權利的實現機制
3.1胎兒應視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
我國的《民法總則》賦予了胎兒以民事權利能力,但卻未明確胎兒的主體地位歸屬。但法律中將已經出生的自然人分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相關研究表明,相關工作人員可以將胎兒視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可以利用現有制度來進行胎兒的利益保護。相關人員還需要建立胎兒監護制度。由于胎兒監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胎兒母腹中孕育時,胎兒的母親死亡往往意味著胎兒的死亡,胎兒的母親不會因死亡事由而喪失監護人資格。即使是胎兒的母親死亡時將胎兒成功娩出,胎兒的主體屬于也會發生變化,會由先前的胎兒變為新生兒,胎兒的監護問題也就成了未成年人監護問題。另外,胎兒的監護人可以作為胎兒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替胎兒行使接受遺贈、接受繼承、為提起訴訟等一系列的民事法律行為。
3.2胎兒的當事人能力
作為民事主體的胎兒,具有訴訟法上的當事人能力,其原告的身份可以由監護人代為提起訴訟,可以作為胎兒利益保護的一種訴訟常態。但是,對于胎兒是否具有被告的當事人能力還存在著一定爭議。其實,胎兒被告的當事人能力與胎兒的利益保護之間是不違背的,當胎兒為被告時,表面上看是使胎兒處于不利地位,但是也是保護他人權益之必須程序,對胎兒的實體利益未必有損。所以,相關人員在保護胎兒的合法權利時,不應該作絕對化和擴大化理解。如張某為了不承擔李某的債務問題,并將全部財產無償贈與給王某腹中的胎兒。王某具有替代胎兒接受贈與權利,可以選擇接受或者拒絕。由于王某腹中的胎兒的保護是在犧牲李某的債權為代價的基礎上進行的,以剝奪李四的債權人撤銷權為手段,李某可以將張某作為被告,并以王某腹中的胎兒為第三人,行使撤銷權,撤銷贈與。
3.3胎兒的人身權利
因胎兒尚未出生這一自然事實所決定的不能由胎兒享有的人身權之外,在理論上,凡出生后所能享有的人身權,人身權利的對象是指那些自然人。胎兒的人身權利指身體權、健康權以及婚姻家庭中的一系列人身權利。自受孕時起,胎兒便與父母建立了相應的父母子女關系,具有了家庭成員的家庭關系地位。我國《婚姻法》第21條第2款指出,胎兒父母在履行撫養義務時,未成年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可以要求其父母給予胎兒相應的撫養費。另外,胎兒享有被收養的權利,如胎兒的親生父母有特殊的困難,沒有辦法撫養胎兒子女時,其父母需要在胎兒出生之前賦予胎兒以被收養的權利;對自己的父親,胎兒還享有撫養費請求權;在父母離婚時,應當堅持“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則”保護胎兒的利益。總之,胎兒與已出生的未成年子女一樣,具有婚姻家庭關系中的法律地位,可以享有一系列的法律權利。
3.4胎兒的財產權利
胎兒有權享有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繼承權等一系列財產性權利。其中,胎兒所享有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是當繼承權出現了殘疾或者是死亡的情況,胎兒可以作為賠償權利人;胎兒所享有受贈與權是指某人在向胎兒為贈與時,應由胎兒的監護人作出接受贈與的意思表示;胎兒所享有受遺贈權是被繼承人在遺囑中指定胎兒為受遺贈人的,為胎兒利益的保護起見,胎兒的監護人不得放棄受遺贈;胎兒所享有繼承權是指在胎兒出生之前,被繼承人死亡,胎兒有權單獨繼承或者與其他繼承人共同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另外,胎兒依法取得的財產歸胎兒所有,胎兒是所有權人,胎兒的監護人代為管理財產。
3.5胎兒為死產時的法效回復
如果胎兒娩出時為死體,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的。所謂法效回復,即已經發生的法律效果回溯性地復原,就如同其從來未曾發生過一樣。胎兒為死產時的法效回復問題,不僅是因為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取得為附法定解除條件的取得,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孕婦在代胎兒取得了相關權利后,選擇人工流產。在解決胎兒為死產時的法效回復問題,可以將胎兒的權利分為涉及到財產給付的民事權利和不涉及到財產給付的民事權利兩種,當胎兒實現財產性權利而取得財產時,就始終存在因法效回復而需要向原財產權人返還財產之可能的問題。另外,不管是胎兒在娩出時為死體或者是在出生之前就已經流產的,“胎兒死亡”都不會發生胎兒遺產的繼承問題,所發生的都是法效回復問題。
結束語
綜上所述,胎兒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也可以視為弱勢群體,但是現階段的立法還不能全面有效的保護胎兒免受傷害。所以,相關人士需要重視對胎兒民事權利的保護,并通過相應的機制盡快將胎兒的權利保護問題納入到法制體系當中,進而切實保障胎兒民事權利,推動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
參考文獻:
[1]袁華超.基于《民法總則》對胎兒民事權利規定的思考和建議[J].法制與經濟,2017,(08):15-16.
[2]王洪平.論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及權利實現機制[J].法學論壇,2017,32(04):35-42.
[3]鄧周易.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的理解與適用[J].法制與社會,2017,(14):292-294.
[4]蘇春曲.論我國胎兒民事權利的法律保護——由《民法總則(草案)》引發的思考[J].法制與社會,2016,(26):293-294.
[5]萬媛媛.胎兒民事權利能力研究[D].南昌大學,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