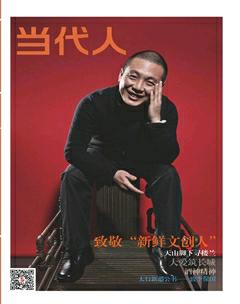張庫大道的雛形
謝云霏
隆慶議和,互市重開
邊關不穩,嚴重影響了明朝的政權統治。順應百姓需求,重開互市,穩定邊關,已經迫在眉睫。而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草原上恰巧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成為改變歷史的契機。
這一年,年過六旬的草原霸主俺答汗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克兔哈屯”,漢族人稱她“三娘子”。此事導致俺答汗和他的親孫子出現了矛盾。因為三娘子本是他的親孫子“把漢那吉”的戀人。奪愛之恨激起了把漢那吉的怒火,他帶著下屬向大明朝投降。俺答汗迫于親情的壓力,不得不發兵到大同城下“要人”。
大明朝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一方面給把漢那吉一行優厚的待遇,借他這顆棋子制約俺答汗;另一方面堅守不戰,派人與俺答汗和談。明廷官員鮑崇德說話直擊要害:“如果把您的孫子殺了,大同的將軍們是會立功受獎的。可是,他們非但沒有殺您的孫子,還把把漢那吉向大明朝廷表示忠誠的意愿奏明朝廷,朝廷因此給他封了官。大明朝廷寬宏大量,你們怎么還要與大明為敵呢?”一席話說得俺答汗唏噓不已。他真誠地對鮑崇德說:“我年紀漸漸大了,早就想得到南朝(指大明)的冊封,重開互市,彼此通好。”
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根據俺答汗的意愿,明穆宗下詔,封俺答汗為順義王,授以王印。俺答汗每年向朝廷貢馬一次,每次500匹,貢使人數150人,由明朝廷給予馬價,另加賞賜。同時,在大同新平堡、宣府張家口堡、山西太原水泉營堡三個地方開設互市市場,這就是著名的“隆慶議和”。
隆慶議和以后,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于中原”的興旺景象。長城下,人群、馬群、牛群、羊群“師師濟濟”,市場內百貨云集、人聲鼎沸。《國朝獻征論》有記載,宣府鎮一帶,五千里范圍內沒有烽火硝煙,人們可以安居樂業,自由行走。守衛的部隊已經漸漸撤去,每年節約下來的糧餉至少二十萬石。
興建來遠堡
從貢市到互市,是社會的重大進步。張家口茶馬互市得到朝廷重臣張居正、王崇古等人的大力支持。到萬歷年間,張家口茶馬互市交易的馬匹數量超過了大同和太原兩地馬市的總和。這從當時規定的馬匹交易數額上限可以看出來。當時,市場的開放是有限度的,各個馬市都限制了馬匹的交易數額。規定宣府張家口堡三萬匹;大同府新平、德勝兩堡一萬四千匹;太原府水泉營堡六千匹。張家口堡的交易數額占到六成。而到了1578年的時候,張家口關口每年馬匹的交易量更是達到4萬匹之多。正如學者黃麗生所說:“蓋三鎮之中,宣府交易量增長幅度最大……”張家口成為茶馬互市的主要市場。
張家口的重要位置,從明朝廷發放的撫賞數量上也能看出來。明后期,朝廷往往拿出一部分財物作為撫賞,這既是對互市貿易的一種補充,也是對游牧部族首領們的安撫和獎勵。隆慶五年的一份兵部文件記載,宣府(張家口)發撫賞52000兩,大同發撫賞32000兩,太原發撫賞14000兩。撫賞發放數量,張家口遙遙領先。
梁勇等學者編著的《京津冀挽起一帶一路》一書中說:“張家口當時的茶馬互市類似于現在的廟會,相對來說比較隨意。萬歷年間,宣府鎮新任巡撫汪道亨,發現茶馬互市的地方存在安全隱患,如,大山的南邊只有一小段長城,中間是一道河流,東邊大路朝天,沒有設防。汪道亨認為‘山川之險,險與敵共;垣鏨之險,險為我專。于是,他打算在這修筑城堡,防患未然……”
汪道亨的折子很快獲準通過,同年,張家口的防務工程破土動工。第二年,工程全部竣工,汪道亨為這處新修的城堡取名“來遠”,當地老百姓則俗稱其“市圈”。明代凡是茶馬互市的地方都要修筑圍墻,劃定市場,這樣的市場被稱為“市圈”。
梁勇說,《明史》記錄了明朝對市圈的管理制度:游牧部落進入市圈的人數不能超過一百,這個數量由甕城卡著。來遠堡位于張家口長城之內,北城墻與長城隔著五十多米,兩道墻體之間的地方就叫做甕城。城門口有人清點人頭,一看人數差不多了,就把外閘門牢牢關上,再開啟內閘門。所謂的“閘”就是來遠堡北門和長城小鏡門上的吊門。當時,開在長城西墻上的小鏡門,本名“西鏡門”,因其寬度只能容一輛小車或一匹馬通過,所以人稱“小鏡門”。明朝這邊把門修得這么小,也是出于邊防安全的考慮。
明代有人畫了一幅《馬市圖》,到清朝康熙年間,戶部漢尚書王騭在欣賞完這幅《馬市圖》后,感慨萬千,揮筆寫了一篇《馬市圖序》。根據《馬市圖序》記載:明代來遠堡互市非常繁榮,每當開市的日子,掌管集市的官吏坐在高高的講市臺上,臺下有軍士伺候,墻頭有士兵保衛。市場上攤鋪延綿,甚至還有表演踢球、摔跤的雜技藝人。文獻記載,當時來遠堡管理課稅的館舍就有24間,可由此判斷其貿易總量不少。
張庫大道現雛形
另外一個可以佐證貿易量的事實是,據歷史文獻記載,萬歷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前后,張家口以西的七鎮,梭布銷售量每年約在百萬匹左右。當時,蒙古土默特、鄂爾多斯、喀喇沁三部,總人口僅僅30萬,如果這百萬匹左右的梭布分給蒙古人,每人就有三匹之多。一個人如何用得了這么多布?事實上,這些梭布又由蒙古族商人輾轉運往了更遠的漠北喀爾喀、車臣、布里亞特等部落,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國北部和俄羅斯南部地區。當時蒙古族商人輾轉行走的道路,應該與后來張庫大道延伸時的路線是一個方向。
對此,《京津冀挽起一帶一路》書中則有更明確的判斷:“參加來遠堡互市的商人有漢、蒙古、滿、維吾爾等民族和俄、德、英等國的商人。市場上,茶葉、綢緞、布匹、米面、紙張、鐵器、牛、羊、馬、駝、藥材等貿易商品應有盡有。來遠堡互市貿易也成了張庫大道歷史的發端,成為農耕民族走出去的起點。張家口堡開始由一個明代長城防御的武城戍堡,逐漸向區域商貿中心和物流樞紐轉型。”
(史料提供人 劉振瑛)
編輯:安春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