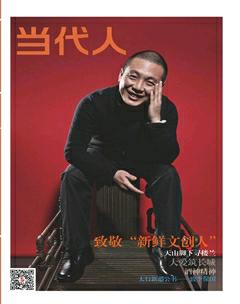新篁,一段趕赴25℃的路
王俊


那些山礬,那些杜鵑,前些日子還呼啦啦地四處漸欲迷人眼,不過半月之余,它們便被季節(jié)招了安。不僅花瓣消失得無影無蹤,連枝干都蔫不拉唧地垂頭不語。倒是遍布林間的桐樹,就在山勢的迂回中,不動聲色地綻放。無邊的白色花朵,只有風(fēng)輕輕地移動它們,仿佛要在連綿起伏的山巒間移出一條秘密的道路。
我們的車子逶迤在山的皺褶里。
一路上,五里鋪、楓林、石橋等村落的名字像一行行詩句跳躍在我們的唇間。車子繞著一道一道的山梁上去下來,再上去復(fù)下來,把路邊的山和樹推遠(yuǎn),又接踵移向眼前。漫山的竹子洶涌綠意,天空的藍(lán)隱現(xiàn)在群山之巔,仿若風(fēng)畫下的拋物線,顯得清遠(yuǎn)和深邃。溪水在巉巖間奔流,新篁就在我們的行進(jìn)中鮮活而生動起來。
凝望一竿竿竹子蓬勃著不同層次的綠,覺得新篁的命名者很有詩意。篁,很容易讓人想起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的“隔篁竹聞水聲”,一靜一動,頓覺幽遠(yuǎn)的古意卷土而來。命名者獨(dú)坐幽篁里,極目盡是鋪天蓋地的春天新綠。風(fēng)吹竹林傳來一陣陣長嘯,遙想自己的子孫后代能詩意地棲居此地,命名者忍不住露出笑容,揮毫留下“新篁”二字。
新篁的竹子恣意地生長在山坡上,它們不會為了取悅誰而去展示形態(tài)之美。它們的枝干緊緊地挨在一起,樹梢攢動在蒼穹之下,像是無數(shù)個人物,胖的,瘦的,高的,矮的,匯聚而成。人和樹很相似。很多時候,人是以自己的精神氣養(yǎng)大了樹,而樹往往會形成一個氣場去孕育人。
新篁的崇山村掩映在一片竹林中。村子不大,只有十幾戶人家。公路旁錯落有致地排列著房屋,開門即看到蒼翠的青山。端的是林木遮天蔽日,群峰連綿,氣象萬千。一條小溪清清淺淺地穿過村莊,又繞進(jìn)田畈和青山,悄悄地滋潤著農(nóng)作物和樹木。水面上橫臥兩座橋。兩橋如同一對父子,依山傍水,立著。老橋漸入式微,始建于清乾隆18年,光緒年間被洪水沖垮,后得以茶亭寺高僧募捐籌錢重修。橋面上的麻石罅隙間露出野草和鵝黃的毛莨,綿延著洪荒的氣息。站在老橋上,低頭見一彎溪水,綠旖的流線泛著緞子般的柔光,水草緩緩地拂動,云影無聲地落進(jìn)水里,又漾出村莊的日常。時值暮春,陽光在山巒間照耀著水面,水面照耀著橋,橋照耀著植物,植物照耀著村莊,村莊照耀著我們,一切景物都泛起了光亮。古老的陽光神奇地將世間的萬物置換成不同的光體,這些光體相互照耀著,輝映著,溫暖著。
老橋的一端矗立著一根石柱,另一端的石柱斜斜地倒在岸邊。石柱呈六個面,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方位。矗立的石柱上半部分明顯有一道裂痕,盡管石灰涂抹著,卻遮掩不住傷口的疼痛。從河岸邊蹣跚走來一位老嫗,著偏襟藍(lán)衫,盤扣之處,已有了歲月的亮光。老嫗指著石柱說,當(dāng)年她的兒子年少輕狂與人打賭,轟然推倒了石柱。后來,她的丈夫死于非命,大兒子跌入河中溺水而亡。推倒石柱的兒子外出打工時,也不幸遭遇車禍去世。
我們聞之,愣怔住了。老嫗像是安慰我們,淡淡地說道,生死有命。各人的修行成就各人的造化。
都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臨橋而居的人,走著相同的一段橋,演繹的人生卻迥然不同。
老嫗的家在橋東。一棵棗樹的根須從地表下延伸出來,伸到了土墻外。樹總是比人活得更堅強(qiáng),也更長久。人死了,樹活著,村莊就活著,而一輩又一輩的人就在村莊中延續(xù)著血脈,繁衍出新的希望。
從老嫗家出來,兜兜轉(zhuǎn)轉(zhuǎn),朋友滕美英夫婦將我們帶到了一片殘垣斷壁之處,告知我們這是弋陽疊山書院的前身。據(jù)縣志記載,這座書院系謝枋得聚徒講學(xué)之地。謝枋得,南宋愛國文學(xué)家,字君直,因推崇蘇軾的“溪上青山三百疊”,故號疊山。《宋史列傳》中描寫謝枋得:“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幾,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
書院早已毀于亂世,散亂的青石和麻石,絲毫還原不了當(dāng)年的模樣。天井的地上鋪著鵝卵石,依稀可見外圓內(nèi)方的銅錢圖案。書院的前方是高聳入云的山峰,林間草木繁茂,水氣氤氳。田壟上,新栽下的秧苗吞吐著生機(jī),大面積的野菊花亮著聲勢浩大的黃。一切喧囂都被大山收集了。遍野的春水嘩嘩地流著,像是昭示著某些歷史深處的吶喊。
宋朝滅亡,蒙古改國號元。元朝意欲拉攏漢族士大夫,圖謀千秋霸業(yè)。遂三番五次派人誘降謝枋得,但都遭到謝枋得嚴(yán)詞拒絕。元朝惱羞成怒,綁架他押往大都。豈料,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謝枋得,憤然絕食,慷慨殉國。
書院幾經(jīng)修繕,后搬至弋陽縣城。從建院到清末廢科舉興學(xué)校的兩百多年里,為國家培養(yǎng)了不少人才。方志敏、邵式平等一批革命先烈就是從這座書院走出來,發(fā)動了震動江西的弋陽抵制日貨運(yùn)動。書院,在國家危亡的動蕩年代完成了一場文化的救贖。如今,書院的跫音遠(yuǎn)去,但精神氣猶在。與書院遙遙相望的是紅色革命根據(jù)地——葛源鎮(zhèn)。兩地的建筑物隔著時空回歸靜默,不逐名利,不慕虛榮,它們從容淡定地吟唱著熱愛、奉獻(xiàn)、堅強(qiáng)的頌歌。
暮色漸濃,裊裊的炊煙從各家各戶的屋頂上升起來。驀然想起朱天文的一段話。她說,突然覺得人生山長水遠(yuǎn),卻就只在這一段趕赴25℃的路上。
在山水間,書院、村莊、紅色革命遺址,日常的真實(shí),卻在我們的內(nèi)心之處,生動而具體。
或許,那才是時光深處的模樣。而彼時,溫度恰好是25℃,不冷不熱,不蔓不枝。
編輯:耿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