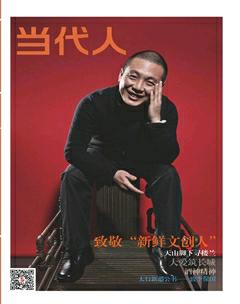皖南小景
龐培
砍柴人
砍柴人從山里出來。那是采茶的季節,山林松風簌簌。一縷小徑橫斜。但她們身影走動的那叢樹林卻看不見路。起先,我們聽到風把她們的衣裳吹到枝椏上,聽見人說話的聲音,隨即聽見走路聲,身子和樹叢相撞,腳下踩碎了落葉枯枝,接著她們慢慢走出來,和我們迎面相遇。
山里涼風習習。一整座山坡都隨風蕩漾喧響。那是寒食節剛過的幾天。沿途映山紅開得稀稀落落,但十分妖嬈顯眼,有時對面的一整座山峰只綻開了一小叢。那紅色卻從融化在蔚藍色天幕的山崖深處懸掛而下。花開得驚險,驕傲。
山中青石橫陳。
看見我們,砍柴人的眼睛顯得訝異、專注。
菜花
這里的油菜花簡直像一片鄉間的染坊,坊間性情憨厚的主人把經由自己的手扎染過的成品到處散播、晾曬。一塊塊山間梯田,沿河畔蜿蜒而去的坡地小路上,有時,在正對著一整棵村頭古榕樹的方圓十數里的平原田疇上,金黃抖擻的油菜花把村民們的眼睛占得滿滿的。菜花的絳黃色、火黃色的光澤甚至滿溢到了高聳入云的村舍白粉墻上。連山谷流下來的溪流,河里的水也充滿了這花的斑斑碎粉。影子在水里纏繞著一條三月里蘇醒的游蛇。興許,染坊的主人有大大咧咧、浪費的習慣罷。我們從來沒有看見他真實的身影,連他的長相面容也不清楚。這里村子上的人誰也說不出他的名姓,但可以肯定是名中年精力過盛的男人。一名田埂上遇見的小孩兒(他正一大早趕去五里路外的學堂)說:誰不知道呢,那是一名為人耿直的鰥夫來著。
今天早上,除了油菜花、桃花、梨花,整個山野村落,我只另外看見兩樣東西:一叢叢的茶園和待耕的水稻田。
油菜、茶葉、水稻——這三樣大地上的寶貝,構成延綿起伏的山里人在青山綠水間的風景。這古老的農事詩篇,門的楹聯。
污田里的牛
牛在污泥的水田里掙扎。趕著牛犁田的莊稼人用一塊拖在牛軛身后平躺的木板駕馭這悲傷的畜生。“吃!吃!”趕牛的聲音,最終被牛蹄子從泥漿中掙扎著拔出來的“噗哧、噗哧”聲蓋過了。牛使勁地低頭、拗下自己粗蠻的背脊、脖子。它對自己的氣力——看得出來——已失去信心。它以一種近乎無望的姿勢向立腳點匍伏,恨不得能像直立動物人一樣雙手著地、趴在農田里。可是它的兩只手掌變成了肌腱發達的蹄子——它必須做牛,必須實踐自己的進化論。一頭農田荒地里的耕牛,它的鼻息出著熱汗,噴著水氣。它的不停搖撼的毛聳聳的尾巴和臀部可笑得被不斷擊濺上來的污泥所恥笑、玷污。甚至眼瞼也被田里的泥水弄得濕漉漉的。
主人狠一狠心,再實行另外一次千篇一律,平均每隔十秒鐘重復一次的動作,那就是在轉彎途中舉手給它幾鞭子!
啊,那鞭子抽打在牛身上——像極了人因為絕望的生活而在地上頓腳——連連跺腳!
興善坊
興善坊門前的火爐。靠弄堂圍墻排放的早點攤位,兩張可折疊桌子鋪了層塑料紙,上面放醬油、醋、筷筒、辣子。攤主是一名中年婦女,外加她前來幫忙湊手腿腳不便的老母親。后者在深狹的弄堂和一大清早趕著辦事的顧客之間跌跌撞撞來回走動,不時遞上一碗熱騰騰的湯粉或餛飩。生意冷清了,老奶奶負責照看煤爐上的火頭。洋鍋子蓋已經掀開,熱氣順著高而陡直的明清風火墻直往早晨瑩澈的空氣熏去。
地上堆了一攤煤灰。一名山里挑擔的小販轉了個彎,從弄堂口擠過身來,他趕完了早市,前后兩只籃筐差不多空了。肩后那一只堆了他嫌天氣熱脫下來的衣裳,另一只碼著捆扎好的新鮮菜苔,正是水淋淋的時鮮貨。菜苔上還有一盆賣掉一多半的腌咸菜。看上去山里人的口味是往這種腌咸菜里放更多的辣子。
“怎么樣?”他把身前的貨筐晃一晃。“一塊五。”
“兩塊兩碗。”女攤主說。
“一塊五。”小販執意,然后加了句當地俚語:“盛滿堆尖。”
“不要。”潑辣的攤主掉頭走掉了,她的家一定就在這牌樓倒塌了的興善坊弄堂深處。
那小販嘆了口氣,把擔子歇下來,安好在地上。把身子往后靠一靠,緊接著,全身的勁頭癱軟下來,他半靠半倚地歇在了弄堂圍墻上。從口袋里掏摸出一根煙,以山里人特有的謹慎和小心翼翼望望兩邊,把煙點燃。看得出來,這是他在那一天早晨的第一次下定決心歇歇腳。他甚至沒有為自己要上一碗熱騰騰的湯粉。
那個動作顫巍巍的老奶奶——攤主的媽媽過來了。她沒有還價。這下,別人才明白她原來是耳聾,并沒聽清楚女兒或媳婦剛才跟小販之間那段對話。她馬上拿來了盛腌菜的搪瓷盆。這邊,著實讓剛愜意了兩口煙的小販忙活了幾下。他用一只海碗掬籃里的腌菜,掬滿一碗,再往碗頭上添扒幾下,“堆尖?”老奶奶問。
“堆尖。”后者的回答鄭重其事。
一小筆買賣做成了。坊間又有幾名顧客走過來要早點。
我走過去一看,這樣老實巴交的“堆尖”法,待那名小販籃筐里的腌菜全部賣完稱凈,也不過還剩三兩碗。
正對著縣城大街的弄堂外面,忙碌的一天開始了。
廊橋
那廊橋在四面寂靜的山谷,睜大了眼睛,仿佛一名活得太久的老農民,忘了自己為何出生、為何死亡。一名樵夫,黑黑的無人相識的樵夫,看見他時他只是背對著你,身背闊大高雄。但他已經老了。干體力活是他從前的榮耀。他甚至見過紅軍,見過山里的土匪倉惶從腳下的青石板路上奔突流竄。時世有時像一攤污水,現在已經干干凈凈。現在那里已經只剩下三月明凈的陽光。一汪汪油菜地,出嫁日的紅油漆嫁妝,紅油漆桶。不,仿佛一名遠古的漁夫身披蓑衣,竹編的、木結構的、石板條相嵌接的。連他那樣經年的耳朵也長時間聽不到砍柴的聲音!那煙熏火燎的寂靜時光,仿佛一只記憶的手掌。一冊山里人家的《年代記》。
木頭的灰黯黧黑中有山里人紅紅的臉膛。每天村子里的牛會走過這里,牛蹄子一旦踏上橋面厚實的木板,牛走路的姿式就變成那種古代帝王式的優雅,連它下垂的肚腹也得意了幾分,顯露出愜意和自信呢。
我遇見他,仿佛遇見了一把群山鑄就的劍。endprint
延綿的青山,處處透露出失傳了的劍法(秘訣)的氣息。我尋覓山中的隱士,無意中在一叢翠竹林間碰見他少年英武的眼睛。
太陽
我在牛的呼吸里傾聽這山谷,聽到山谷的炊煙,村上人家千年悠久的動靜,我讓牛走遠了的犄角帶我尋訪,去往深山里的農田、旅舍、瀑澗、道觀。我把牛和山當做一道圣跡。
田野像古時鋪展開來的朗朗讀書聲。
……想起一首古詩,我的耳朵豁然開朗——
牛鼻“吭哧”一聲!我自己的肺葉也就煥然一新。
牛昂起來的犄角,沖著中午的烈日。
犄角沖進了太陽。
油菜被淹沒在太陽里,油菜已經不是植物,而是一種空氣的溫度,一層肌膚。
太陽變成了土地,變成了高聳入云的山崖、植被、潺潺流水。變成了任何山里人賴以為生的莊稼。今年的收成就是太陽。啊,陽光,你是此地的羊腸小道上清涼的青石條板。
一把鐮刀從樹上掛下來,呆呆地凝視這場太陽靜止的舞蹈。
天空深處一定有一只破碎的碗盞。
小溪
小溪闊闊的,清淺著,時而被裸露出亂石的河床弄出些聲響來,有時你仔細聽,水聲音像極了孩子氣的,或上年紀人想心事時的嘆息。水中橫陳的亂石把水流“咯咯咯”弄出些聲音,這聲音也真有點像村里的雞叫,但更像是山里人家男女間的情事,有些純樸的風騷、撩撥意味在里面。山里人的愛情,也像這溪水一樣清淺——一份古老的溫存……
在村頭轉彎處,忽然裸露出幾層青石的岸壁,很大、很齊整——威嚴的模樣。那里曾經有一處古代的祠堂。祠堂被毀以后,把聆受過訓誡的空氣留了下來。
村莊的名字,或者叫“秧尖”“秋溪”“汪口”;或者叫“大畈”“嚴田”……午后,半村的人都在兩岸的灘頭棲息,婦女們把鍋碗瓢盞浸到冰涼的水里,老漢牽著牛赤腳涉過河床。
牛的腳碰著了歲月的明麗。
茶亭
這個山中石砌的涼亭已經了無生氣了。走近它,甚至空氣里也有一層不知名的衰亡、年邁。但是年邁又從何說起呢?唉……年邁仿佛在此,向下面長滿荒草的石階邁動腿腳,這看不見的走動掠過古老陰森的石壁,靜悄悄地,不說話。涼亭久已遇不到歡喜的人了,那些山里的燒炭工、老農、獵戶。他們曾依偎著古樸久遠的歲月跟它說話,雨天里,把一捆捆濕漉漉的茅柴堆在廊柱下面。而它一度給他們蔭蔽的身子仿佛不久于人世的老人陷入了昏迷的神志里……不再知道山中的歲月是否猶有智慧和美……
當我走近它,仿佛一名無知而貪玩的頑童,魯莽中打斷了一名老人的瞌睡。
我在那張皺紋密布、迷惘的老臉跟前站住,停下來——感到周圍的整個群山,回蕩起一絲無聲的慍怒——
群山之上,正是晴空萬里。
我朝那大山深處張望——一條蜿蜒攀升的青石小徑——不斷有人類的足跡,在此消失……
不斷有人的辛苦、勤勞,蕩漾整個山林的芬芳,微微搖撼藍色閃電般倏忽不見的延綿山脈——
編輯:劉亞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