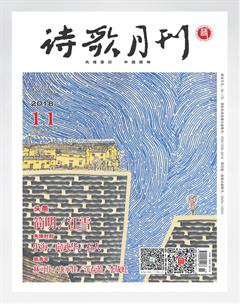詩歌當季2018年秋季中國詩歌巡覽(下)
秋天來了。秋的豐盈與燦爛讓我們欣慰,也讓我們喜悅。我欣喜于我,們的詩歌非常突出、非常濃郁的人文意識。我們的詩人,無論是“朦朧詩”時代的前輩,還是我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同齡人們,抑或是90后的年輕詩人;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他們都以詩的方式表達著自我,表達著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情感與體驗。即使只是在2018年7月至9月這短短一個季節的詩歌中,也能感受到我們的詩人各自獨特和無比豐富的“個體性”。“個體多樣性”一一我所想倡導的人文主義詩學的核心指標,在我們的詩歌已經有很充分的體現。不需要宣言,也不需要什么高頭講章,就讓我們如梁小斌先生所言,“在淡泊和默默無聞的縫合中”,實、勤勉地去努力,去建構!
王夫剛:《滿臉星辰的人》
肖水:《肖水詩選》
趙野:《蒼山下》
阿未:《此刻外面陽光還
榮榮:《如初》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當時代中的鄉土詩篇日漸沒落”
王夫剛:《滿臉星辰的人》,《詩歌月刊》2018年第8期
王夫剛的作品很早就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異鄉人之死》和《暴動之詩》。當時我正主編著一套規模較大的《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201O》,試圖將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文學中各種文體的代表性作品、理論批評和重要史料系統集成,我兼負責其中的“詩歌卷”,因此閱讀了那一個十年的大量詩歌,初次讀到夫剛的這兩首詩,大為震撼,覺得這兩首詩無論是于歷史和時代,還是于鄉村,于我們的詩史傳統,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很能夠代表我們這個時代詩人的良知與見證意識,便很珍惜地收錄其中。至今看來,更加覺得這兩首詩的可貴和自己當初選擇的正確。
與以往的詩作一樣,《滿臉星辰的人》仍然是寫鄉村,是夫剛在“鄉土詩篇日漸沒落”(《每一片落葉上》)的時代中非常可貴的堅持。夫剛寫農事,寫自然,寫許多在我讀來倍感親切的鄉土景觀。在他的作品中,無論是“太陽升上林梢,照徹桃園”(《桃園附近》),還是“槐花熱烈地盛開”“熱烈地凌亂”(《槐花凌亂》),抑或是“黃昏之后,低于月亮的山岡/迎來了遍地月光”(《望見山岡>),或者是“秋風浩蕩”的時節,天空舒展,“有云飄過”(《致青春》);無論是他寫麥田中有“兩個站著交談的人”(《村莊以東的麥田》),還是寫“開鐮的日子,女人大聲地/說笑,男人們已經開始盤算/麥收以后的去處。熱風/一陣一陣地吹來,金色的麥浪/在他們心中起伏著,奔跑著/令大地炫目而又不安”(《村莊與人》)……他筆下的鄉土自然和鄉村生活場景,都會讓我回想起接壤于魯地的我的家鄉,想起自己少年時代的鄉村生活。 《早春與少女> -詩,也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戴望舒的《村姑》,但是其意境要更清新,要更明亮,卻又都給我們留下了美麗的秘密。
“村莊與人”,自然是王夫剛鄉土詩篇的寫作重點,《滿臉星辰的人》中,重點又在于親情,在于對夫剛而言最為屬己的倫理親情。他寫外婆(《獻給外婆的詩》)、祖母(《獻給祖母的詩》)、父親(《田野上的父親》《每一片落葉上》)、母親(《寫母親》《再寫母親》《重返谷雨村莊》),都很自然地飽含深情,亦有很多令人難忘和屬己的細節。但正因為屬己,屬于詩人獨特的個體生命,所以,時代、歷史、地域、血緣等多重性的時空因素集于其一身,也很豐富地交融于詩中,非常有效地表達了夫剛所曾念茲在茲的“個我”,建立了一個他自己的世界,他自己的“內心秩序”(王夫剛:《斯世同懷·自序>)。不過,也正因此,王夫剛的“內心秩序”和更深廣的世界卻又是相通的。大地永恒、親情永在,時代和歷史卻變動不居。王夫剛的鄉土詩篇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避歷史,在歷史的風煙和深刻的轉型中來寫鄉村,來寫人。他的景象與人物,很多都潛藏著歷史的因素一一一如他的《暴動之詩》和《異鄉人之死》。他很清醒地覺察到我們這個時代“鄉土詩篇日漸沒落”的現實,他也深知村莊與人們“在鄉土的時代告白中請求發言”(《村莊與人》),甚至“仿佛最好的詩篇就在這里”,就在鄉村(《村莊以東的麥田》),因此他的領命于詩,堅持著以自己寫作來書寫鄉村、表達鄉村,反抗“鄉土詩篇日漸沒落”的現實,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令人尊敬,也令人期待。
“我的人生開始做減法”
趙野:《蒼山下》,《鐘山》2018年第5期
趙野慵懶,一如鄙人。但趙野的文字,以一當十,勝過許多空闊的宏文。趙野為數不多的詩篇和他散見于其同樣不多的對話、訪談與隨筆中的見解,時常令我嘆服。他于慵懶之中似不經意的話語,每每能夠擊中我們的時代、生命、歷史與世相的本質,機鋒與力道,尋常罕見。所以,“我的人生開始做減法”(《黃昏》),這幾年來一直盤桓于我內心的念頭一經他道出,不禁頓生出遙遠的會心,親切莫名。
減法的人生,意味著要砍去那些不必要的人與事一一“該留的留,該滾的滾”,決不理會污穢的人事。語雖憤激,道理卻很正確。吾生有涯,雖然誠如魯迅所言,“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但是,我們并不應該讓人生漫漶無涯地消耗于那些無益之事,忘卻精義。趙野的減法,趙野的后退,便源于其對精義的了悟。
以“第三代詩人”來命名“艨朧詩”之后的一代詩人,趙野是起初重要的發明者,其時他還發起創辦了《第三代人》詩刊,雖只刊行一期,已很必然地載入正史。不過趙野并不很在意,很快他便退出現場,隱身或游走于更加廣闊的江湖:策展、從商,偶或有詩,直到前些年退居大理,于蒼山洱海之間尋得其世外桃源。《蒼山下》,正是趙野桃源中的詩篇。
但桃源中的趙野,內心果然有真正的安寧?“黃昏蒼山讓人心醉/我的人生開始做減法/這地老天荒的算術使結局/越來越清晰,年歲浩蕩流逝/我們正在經歷的每一天/其實就是最好的日子”(《黃昏》)、“蒼山蒼涼如故……/……我出入山水之間,俯仰成文/生命終要卸下重負/詞語破碎處一切皆空”(《蒼山》)、“想象一種傳統,春日/天朗氣清,我們幾個/吟風,折柳,踏青草放歌/或者繞著溪水暢飲/我們會在冬天夜晚,依偎/紅泥小火爐,看雪落下/此刻詩發生,只為知音而作/不染時代的喧囂與機心”(《想象》)……趙野似乎是安寧的,卻也好多創痛,好多不甘,他最好的生活,也得靠“想象”,靠對“傳統”的“想象”來構建(《想象》)。通讀趙野不多的詩篇,幾乎從1980年青年時期開始,他就采取了后退的姿態,他說“我或許應該走得更遠/直到宋朝”“空氣中的/優雅和頹廢,以及嬌慵的湖泊與明月”(《冬日》),讓他迷戀。“桃花流水悠悠”,他說“吾從周”;“長空深闈幽幽”,他說“吾從宋”(《剩山》)。趙野的內心,充滿著永遠無法擺脫時間的焦慮。而亙古如斯,我們的宿命,我們的悲劇就是,根本沒有抽象的時間、純粹的時間,過去、現在、未來,傳統、現代,他人、自我、生命……一切全裹挾于時間之中,是時間性的存在。所以在蒼山之下,即使是在“獨自”的時刻,趙野也難忘卻時代,難以不掛礙于“大地上/奔騰著粗鄙的現代性”(《獨自》)。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趙野從1980年代開始,就與當時奔騰不己的現代性發生緊張關系,并將這種緊張落實和體現于其人生姿態與詩學選擇,做減法、往后退,形成了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的精神立場。相對于二十一世紀以來取此立場的諸位朋友,允為先行者。
在衰敗的季節里,爛漫如初!
榮榮:《如初》,《詩刊》2018年第8期
無意之間,榮榮曾以自己的寫作回應了克里斯蒂娃關于女性時間的主張。在她的一組題為《更年期》的組詩中,榮榮以其略帶自嘲與反諷的方式書寫了一位“更年期”女性的內心與日常。“別試圖從我的詩句里探詢秘密/我只是兩手空空的絮叨婦人”,在這組詩的開篇之作《聲明》中,榮榮首先就做出如上的“聲明”,試圖“撇清”她的寫作與其“自我”的關聯,打消我們索引的念頭。但是在實際上,我們雖然無法證實榮榮詩歌中諸多細節與榮榮本人的自傳性關系,這些細節仍然構建了一個形象鮮明的女性主體,并在當代中國女性詩歌的歷史脈絡和當下格局中,顯示出非常重要的獨特性。這一獨特性,不僅在于其以“更年期”這樣獨屬于女性、獨屬于身為女性的榮榮自身的個體生命體驗來表達自己、書寫女性,更重要的,還在于以“更年期”這一女性時間來區別于女性主義者們所耿耿于懷或意欲挑戰與逃離的男性時間,建構了一種女性自己的“女性時間”。我以為這正是榮榮的意義。
榮榮的詩歌有很自覺的時間意識。她的關于更年期的詩歌自然如此。她也寫有《時間之傷》這樣的關于“更年期詩歌”的詩學思考。新作《如初》,更年期的特征不甚明顯,時間意識卻一仍其舊。“如初”之題,已經含有非常明顯的時間意識。組詩中的其他幾首,基本主題都關乎時間。只是這“時間”,屢屢被榮榮以隱喻的方式,以“衰敗的季節”來予以表現。在《遙遠》中,是“修剪后的樟樹露出新鮮的傷口/陳葉落下來……”;在《梧桐》和《溫嶺小鎮》中,則是梧桐“闊大的落葉成潮”“季節又一次轉向衰敗”。榮榮真實和深切地書寫了“衰敗季節”中的女性情懷,她內心的痛楚、念想與不甘,有開闊與松弛,亦有對自我生命的認真反芻,特別是生命中的某些“傷害”,或曾錐心,但均關乎愛,讓詩中的主體念念不忘,刻骨銘心,詩人的書寫也意味深長,欲說還休。索引很困難。索引也不必。榮榮的詩歌有很突出的戲劇性。在《遙遠》《散亂的月亮》《尤其》《梧桐》《聲音》《逃遁》《小區暮景》《陽春》《濃霜》和《溫嶺小鎮》等諸多詩篇中,都有一個男性,一個“你”“他”,一個榮榮喜歡喚作的“那人”。不一定需要從自傳性的角度或以索引的方法,榮榮詩中的男性形象,特別是他與女性主體之間豐富的戲劇性,其實已經足堪玩味、足夠我們思考;不過在另一個方面,榮榮詩的戲劇性,還發生在其自我的內部。像在前述諸詩中“我該如何重新去愛”“我越來越不喜歡遙遠的事物”(《遙遠》)、“他的黑暗讓她心疼//曾經,他是她一個人的圣物/現在,他是她一個人的經典”(《尤其》)之類的自問和自我揭示,不僅屬于詩歌主體自我內部的戲劇,使得主體更加豐厚,更使她與“那人”之間的戲劇性增添了許多復雜的意味。《承德圍場的向日葵》《陽春》和《如初》諸詩,相比而言更具獨白性,但其獨白,也面向著一個“他”,一個“你”。詩中的獨白,雖仍發生于人生中的“衰敗季節”,但更陽光、更燦爛。人生或許經歷過“坎坷”(《如初》)或許被“寫壞”“許多錯處”(《陽春》),或許“也曾在傷害里穿行”(《如初》),但很可貴的是,“陽光也在那里濃郁著”、她“仍習慣地遠望”(《陽春》),她仍有著“爛漫如初的心跳!”一一在“更年期”之外,榮榮又以其詩歌提供了另外一種女性時間,書寫了被稱為是“衰敗季節”中的諸般戲劇,其對女性主義的詩學建構,頗有意義。
“保持必要而絢爛奪目的孤獨”
肖水:《肖水詩選》,《江南詩》2018年第4期
2018年第4期的《江南詩》在《首推詩人》欄目中重點推出“肖水詩選”,并刊登青年詩人和詩評家王子瓜關于肖水詩歌很有分量的評論文章《孤獨與風景》,非常值得關注。在出生于1980年代的青年詩人中,肖水是一位非常活躍的領軍人物。他不僅從事詩歌創作,還從事詩歌翻譯、詩歌編輯出版、詩歌活動的組織策劃等許多工作,營造了頗具特色的詩歌文化。這一文化的青春氣質與學院精神,也彰顯了肖水的詩歌文化形象。基本上,肖水屬于“學院派”,是目前越來越引人注目的“學院詩群”中的代表性詩人。
肖水似乎很喜歡可能性。他的豐富多樣的詩歌文化實踐是其探索可能性的重要方式。即使在寫作中,他也愛尋索多種可能。這些可能性的展開,不僅體現在他的詩集《失物認領》《艾草》和《渤海故事集》中, “肖水詩選”也能代表他的探索。比如詩體探索方面, 《橋上》《艾草》《失火》《風暴招待》和《天工開物》就屬于“新絕句”; 《恐龍特急克塞號》《南溪鄉》或《松枝》《來歷不明》等則屬于“小說詩”; 《獨樂詩》《芳香中學》諸詩,歸總于“渤海故事集”,屬于“故事詩”。不僅在80后一代或學院詩群中,就是在我們的詩歌界,像肖水這樣有很自覺的詩體意識并且努力做多種探索的,也不多見,因此非常值得重視。他已有的詩體探索,也很值得充分地去總結與思考。
不過在另一方面,肖水雖然熱衷于可能,似乎有點八方出擊的感覺,但其內核與定力,卻也很突出。他的“新絕句”“故事詩”“小說詩”等詩體探索,均非淺嘗輒止,而是頗有定力和洋洋大觀地寫得很充分。他的“新絕句”如《橋上》 -詩一一“霧氣早早地合并了群山。鵝王養靜,/諸厄消除,水面的平安道場,經聲也漸消散。//小葉苦丁不描而翠。烏雀耳根圓通,/所入既寂,只有蜂鳴四起,仿若萬物爛醉如泥”一一詩中的禪意盎然,空寂渺遠境界中的“蜂鳴四起”泥醉萬物,唯一“小葉苦丁不描而翠”,讓我們疼惜,也讓我們驚喜莫名。肖水的“新絕句”承續了我們的古詩傳統,返本開新,以一枚小葉苦丁凸顯出一個現代的主體。
肖水的詩歌主體往往都很“小”和“苦”,但都像這枚小葉苦丁一樣有著清新、翠綠的生意。這是肖水詩的內核。他在《艾草》中曾經寫過近乎格言般的詩句一一“有三種苦可以歸為榮耀:慷慨,悲憫,以及孤獨”。肖水的詩歌主體既小且苦,更常孤獨。不管是在“新絕句”,還是在肖水其他類型的詩歌中,經常都會有一個孤獨的主體。在《自畫像》中,肖水曾說:“寫詩就是將自我物化,將所有細小的/鬃毛固定在馬背一條狹長的金屬板上,”他一方面要“保持必要而絢爛奪目的孤獨”(《微光》),另一方面,則要從這樣的主體擴展至萬物,既表現其“內心顫動”,也創造其“自身的幻象”(《葉家花園》),由此也形成了詩人繁復萬端卻又擁有其內核、變化有常的詩歌世界。
“這天空,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悲情”
阿未:《此刻外面陽光還好》,《作家》2018年第9期
“阿未,本名魏連春,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中期,吉林市人……”2018年第9期的《作家》雜志刊發阿未組詩《此刻外面陽光還好》,附有一則關于詩人的介紹。他是我的同齡人。我們這些出生于1960年代中期的人,應該都已經飽經滄桑,不惑之后,己知天命。但我們的人生、我們精神的深處到底如何,阿未的詩中,興許能有深切的表達。
我是一讀到阿未的詩,就被它們深深地吸引。請看開篇第一首《一個人在人聲鼎沸的街角幽坐》(下稱《幽坐》)一一
在這條廢棄的舊船上,我看到了一些/關于大海的往事/我看到所有的驚濤駭浪都驟停于/風吹日曬的斑駁中,像一個/走累了的人,在人聲鼎沸的街角/幽坐,你不知道他究竟來自哪一條街/也不知道他經歷了哪些事或見過/什么人,所以你當然不知道一條/傷痕累累的舊船,經歷過怎樣一場/潰敗,面對潮水的低吼和時光的消磨/一條船朽掉了體內的鋼鐵,它必將/沉默著一寸一寸地坍塌/在離水越來越遠的岸上,把自己擺成了/一道舊風景,像一個走累了的人/在人聲鼎沸的街角幽坐……
阿未的這首詩,寫的是一條“傷痕累累”的舊船,也寫了一位幽坐于街角的“走累了的人”,它們其實都是詩歌主體的自我寫照。詩人以其精準的刻畫與描摹呈現了舊船與人的形象,主體自我清晰明確,意涵深刻。我想,我們同代人中的很多朋友,一定都能從這首詩中獲得共鳴。但我特別留意到了詩中的“鋼鐵”。阿未寫這條舊船在“潮水的低吼和時光的消磨”下“朽掉了體內的鋼鐵,它必將/沉默著一寸一寸地坍塌”,這條舊船顯然已“潰敗”至極。然而,就在緊接著的《又看到水凍僵的樣子了>中,至柔的水因為寒冷而“變成了堅硬”,而那些也曾于水中輕拂的水草,也“長出了風搖不折的肋骨/它們把根深扎在冰里,就有了蔑視疾風的底氣”,“當時間開始/揮舞冰冷的利刃,我們已經僵硬了的/內心和軀體,就再也不怕/血流成河……”。因此那舊船,和那街角幽坐的人,并不能夠代表詩歌主體的全部,至柔如水,如“行將腐爛”的水草,環境的冷酷也能使其身心如鐵,甚至不怕“向流成河”。
所以說,阿未詩歌的基本主題一方面像《幽坐》這樣書寫了詩歌主體的飽經滄桑,他寫“月光之下我的孤影長長/像遍體鱗傷的記憶中留守的/一道疤痕” (《你們和從前的日子都走了》),寫我們在“步步緊逼的寒冷”中,“以接近匍匐的樣子,在越來越大的/風雪中艱難前行”(《那么多的冷被滿世界兜售》)。在《一場暴雨過后有陽光弱弱地照下來>中,更是“想象出天空曾經淚流滿面的樣子”,他問“這天空/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悲情呢”。因此天空也與其舊船一樣,成了詩歌主體的生動寫照,只是它的苦難,表現得更加浩大……世道險惡,人生艱難,生命復又有涯,這樣的主題很自然地道出了我們的心聲;但是,在另一方面,像水成冰或至柔的水草冷硬成肋骨一樣,在他的《質疑》《我開始對落日有了敵意》《確信黑暗包圍了深夜》和《午后》等詩作中,詩歌主體與“雪”“黑夜”及“窗外的冷”的“對抗”“抗拒”“對視”“對峙”,同樣也非常突出。阿未詩中的“敵意”(《我開始對落日有了敵意》)令人振奮,也喻示著“傷痕累累”的主體的堅韌與剛硬,并未被擊敗。他甚至還有柔情,還有深厚與廣闊的愛。《一場愛情覆蓋了荒蕪的曠野》和《假設》中所寫“要隨這群/滿眼的蝶舞,赴一場清風拂面的艷遇”,愛與柔情書寫得何其動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