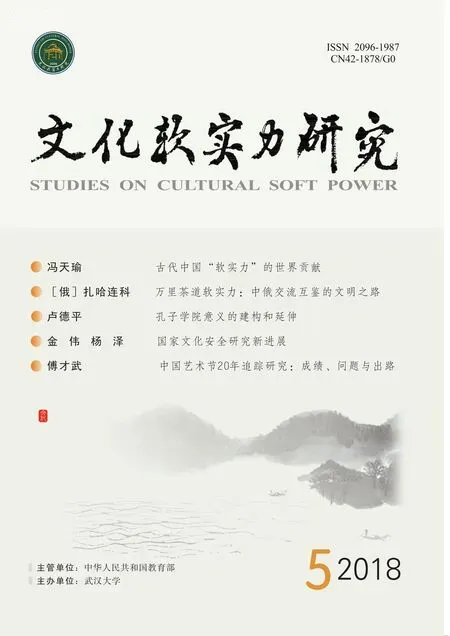古代中國“軟實力”的世界貢獻*
馮天瑜
中國有著延綿不絕、高峰迭起的文化系統,它以卓異的風格、多方面的成就使世人嘆為觀止——
2007年評定新的“世界七大奇跡”,橫亙于中國北方燕山山脈至河西走廊的萬里長城,以第一名當選;
隨著工業化在世界范圍展開,運河已不勝枚舉,而1 300多年前開掘的中國南北大運河,其里程迄今仍居通航運河首席;
各國在古代、中世紀、近代都曾集中能工巧匠,修建許多精美壯觀的宮殿,而北京紫禁城是其中的佼佼者,其規模的宏大,使凡爾賽宮、克里姆林宮相形見絀。
本文側重介紹傳承不輟的史學、睿智的古典哲學的世界性貢獻。
一、史學域外播揚
中國古代史學傳揚世界,東亞文化圈內,日本受影響頗深。日本的第一部史書—— 《日本書記》 (成書于8世紀),就是模仿中國正史的敕撰史書,其體例仿照中國《史記》 的本紀,按天皇立卷,編年記事。書中還多處摘抄中國古史的原文。自《日本書記》始,學習中國正史,以之為范本,成為日本古代史學的傳統。日本學者清原貞雄曾對《日本書記》《日本后記》《續日本后記》《文德實錄》《三代實錄》 等“六國史” 的編撰加以評論:
六國史專仿中國史記、漢書以下諸史中的本紀而編。中國歷代正史所謂二十四史,都是某朝把滅亡了的前朝的歷史加以編纂……日本朝廷一系相傳,并不似中國有彼亡此興的事實。卻也模仿中國,只記到前代為止,而不記當代的事。[注][日]清原貞雄:《日本史學史》,昭和三年東京中文館本。
日本自古設立史官,也仿效漢唐。史學家日柳秀湖指出:“史官的位置,是中國文教傳來最顯著的結果。” 一如日本平安朝初年,專設“撰日本紀所” (后改稱“撰國史所”“修國史局” )。陸續編成《日本后記》 等五種國史。
受中國文化啟發,日本學者的修史宗旨在于作政治借鑒和人倫規范; 史觀取儒家的道德史觀,宣揚大義名分,勸善懲惡。體裁取中國史書范例,如德川時代兩大史書——幕府編《本朝通鑒》 取編年體,水戶藩編《大日本史》 取紀傳體。史筆或春秋筆法,字字寓意褒貶,如《元亨釋書》; 或“據事直書義自見”,編者不予置評,如《本朝通鑒》; 或設論贊,縱論善惡得失,如《大日本史》; 史評則常援引中國同類史實而評判日本歷史的意義和價值。
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聘明儒朱舜水(1600—1682)為賓師,朱舜水向弟子安東守約、安積覺、伊藤仁齋、山鹿素行傳授“尊王攘夷” 說,形成水戶學派,對江戶時代以至明治時代的修史及政治均有影響。德川光圀及后繼水戶藩主主持編纂的《大日本史》,多有朱舜水弟子及再傳弟子參加,該書仿效《史記》,采取紀傳體,故有《日本史記》 之稱。
朝鮮的《高麗史》、越南的《大越史記》 也從體例到史觀、史體都深受中國史學的影響。東亞各國還仿效中國的修史制度,開史館,設史官,編撰史書,12世紀時的王氏高麗亦仿照宋朝的史官制度,設置編修官修實錄。越南則自19世紀后,仿照中國的明、清史館,設立國史館。史官制度以及撰史宗旨、方式上的一致性。成為東亞文化圈的重要元素。
歐洲啟蒙思想家也高度贊賞中國史學的非宗教的理性主義精神及連綿的歷史記錄。當然,他們筆下的中國史學,經過了或多或少的改造,以適應反對宗教神學與封建蒙昧主義的需要,與原來面貌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對于伏爾泰等思想家來說,“用中國這個例證把《圣經》 的歷史權威打得七零八落,這就足夠了”[注][法]維吉爾·畢諾著,耿昇譯:《中國對法國哲學思想形成的影響》,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由此可見中國史學的理性主義傾向所蘊藏的巨大的生命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卓異地位。
二、萊布尼茨發明二進制之后從《易經》 圖式找到呼應
凝聚中國民族精神的古典哲學,一方面涵泳外來文化的精華以滋補、發展本民族的理論思維; 另一方面,在與外民族文化系統的交流中,傳遞出其獨有的“智慧之光”,對人類理論思維的進步作出自己的貢獻。
16世紀以降,入華耶穌會士向歐洲介紹中華元典《易經》《老子》 及宋明理學等,這是在13世紀馬可·波羅介紹的中國幾乎被歐洲人遺忘三個世紀以后,西方知識界突然重新認識到還有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大國屹立在世界東方,他們的耳目為之一新,恰如伏爾泰所言:“歐洲王公和商人們發現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的世界。” 萊布尼茨、伏爾泰、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文化巨匠都從東方哲思中受到教益,獲得靈感和啟示。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德國古典思辨哲學的先驅者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文化對西方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家。這位被人稱為“千古絕倫的大智者”,對中國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他從20 歲起便研究中國哲學,直至垂暮之年,還為向歐洲闡揚中國哲學的真諦而嘔心瀝血。
萊布尼茨在為《中國近事》 所寫的導論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醒!” 從而開啟以后啟蒙思想家借重中國文明鞭笞舊歐洲傳統的先河。對于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接觸,萊布尼茨十分興奮,他說:“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陸兩極端的二國,歐洲及遠東海岸的中國,現在是集合在一起了。” 他預言這兩個最有教養的民族文化攜起手來,將影響和促進其他民族(如俄羅斯)的進步。萊布尼茨又對歐洲與中國作文化比較:
歐洲文化之特長乃數學的、思辨的科學……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注][德]萊布尼茨編,梅謙立、楊保筠譯:《中國近事》,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因此,他極力主張進一步擴大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對于那些非議中國哲學的言論,他大聲加以反駁:“我們這些后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是因為這種學說似乎首先和我們普通的經院哲學不相符合,這真是狂妄之極。”[注][德]萊布尼茨著,龐景仁譯:《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 1981年第3 期。
萊布尼茨有關單子的理論,在相當程度上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是宋儒的精華。德國學者利奇溫指出:“他(萊布尼茨)的靈子(即單子)的學說,在許多方面和代表中國生活的三大派——老子、孔子及中國佛學所表示的道的概念,有一致的地方。所謂‘先定的和諧’,在中國則有所謂天道。萊布尼茨亦如中國圣人一樣,相信實體的世界是一個整體,是精神實體的不斷繼續充實提高。兩者對于先定的和諧的信仰和對于天道的信仰,產生了無限的樂觀精神。”[注][德]利奇溫著,朱杰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79頁。萊布尼茨的單子論,之所以從內容上或邏輯上,同冶儒、釋、道于一爐的、講究道德的宋儒理學如此相似,原因就在于萊布尼茨的哲學體系中,有意識地吸收和融合了來自中國的思想。從此,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因素匯入德國古典的思辨哲學之中。
萊布尼茨對二進制算術的研究,從中國古代《易經》 的六十四卦說中得到印證,這使他倍受鼓舞。
萊布尼茨于1672—1676年前后發明二進制,1701年,萊布尼茨將二進制數表給法國在中國傳教士白晉,同時將二進制論文交巴黎科學院,同年11 月白晉把宋人邵雍(1011—1077)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和伏羲六十四方位兩個圖給萊布尼茨,萊布尼茨閱后興奮異常,發現中國古老的易圖可以解釋0~63的二進制數表,他說:“幾千年來不能很好被理解的奧秘由我理解了,應該讓我加入中國籍吧。” 可見,萊布尼茨于17世紀70年代發明二進制,約30年后,于18世紀初讀到邵雍概述的《周易》 六十四卦的論述,引為同道,受到鼓舞,而并非是萊布尼茨受《周易》 啟發后才發明二進制的。[注]見胡陽、李長鋒:《萊布尼茨二進制與伏羲八卦圖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萊布尼茨在給法國朋友德雷蒙的一封書信中,講明了他的二進制與伏羲八卦圖的關系。其間他高度稱贊伏羲八卦圖。
我和尊敬的白晉神父發現了這個帝國的奠基人伏羲的符號的顯然是最正確的意義,這些符號是由一些整線(指陽爻)和斷線(指陰爻)組合而成的……一共有64 個圖形,包含在名為《易經》 的書中。《 易經》,也就是變易之書。在伏羲的許多世紀以后,文王和他的兒子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五個世紀以后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64 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制算術,這種算術是這位偉大的創造者所掌握而在幾千年之后由我發現的。[注][德]萊布尼茨著,龐景仁譯:《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 1982年第1 期。
1703年,萊布尼茨在《皇家科學院科學論文集》 中發表了題為《二進制計算的闡述》 的論文,并將二進制擴展到加減乘除四個方面。
沒有二進位法的引入,就不可能出現現代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而“萊布尼茨成為符號邏輯或數理邏輯的前輩,對其觀念的刺激,公認來自中國特殊的表意符號的性質”[注][英]李約瑟著,翻譯小組譯:《中國科學技術史》 第二卷,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497頁。。
萊布尼茨不僅介紹、傳播中國文化,還積極籌建中西文化交流學會,他成功地移植了中國蠶桑,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籍,并寫信給傳教士敦促他們翻譯中國古代法律、天文學與醫學著作。他的努力,為其他18世紀啟蒙思想家向東方學習,準備了豐富的思想材料。
三、中國理性與歐洲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于18世紀漸次勃興于西歐各國,并在法國得到最典型表現。啟蒙大師們的思想特征,是一切求助于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具有“把一切現象都歸因于自然而不歸因于奇跡的傾向”[注][英]漢默頓編,何寧譯:《西方名著提要》,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頁。。黑格爾確信——
“理性” 支配世界,而且“理性” 向來支配著世界。[注][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55頁。
啟蒙思潮的出現,固然有其深厚的經濟和社會根源,但是,按照思想文化運動發展的一般規律,一種新的學說,都有由先驅者傳來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以宗教神學為主體的中世紀傳統是與啟蒙思潮對立的意識形態體系,古希臘羅馬傳統才是啟蒙思想的源頭,而來自東方的具有實用理性精神的中國文明,也提供了啟示,成為伏爾泰及與其同時代啟蒙思想家借以鞭撻中世紀歐洲的“巨杖”[注]王德昭:《服德爾著作中所見之中國》,《新亞學報》 1970年第九卷第二期。。
(一)啟蒙學者對中國理性的推崇
熱烈追求理性與智慧的啟蒙思想家注意到中國哲學宗教色彩淡薄,而以認識到的各種形式為最高的學術。啟蒙思想家對此大加推崇。
法國伏爾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現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 之后,建立一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伏爾泰心目中,中國儒教乃是這種“理性神教” 的楷模。他在這個時期創作的哲理小說《查第格》 中說,中國的理或者所謂的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古老和文明“完美” 的原因。他稱中國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注]《伏爾泰小說選》。。他推崇孔子,稱贊他“全然不以先知自認,絕不認為自己受神的啟示,他根本不傳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注]《伏爾泰全集》 第七集。。他的書房掛著孔子畫像,下面題著四句頌詩:
子所言者唯理性,實乃賢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則明,國人世人皆篤信。[注]《伏爾泰全集》 第七集。
伏爾泰還稱贊中國哲學“既無迷信,亦無荒謬的傳說,更沒有詛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條”[注]《伏爾泰全集》 第八集。。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 中也指出:“孔教否認靈魂不死”。狄德羅《百科全書》 中關于“中國”一段,介紹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國哲學,認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別稱贊中國儒教,說它“只須以‘理性’ 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
啟蒙思想家還從中國的歷史中看到了以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的哲學思想的力量。中國的萬里長城未能阻止異族入侵,而入主中原的異族無一不被漢族所同化。歐洲啟蒙思想家認為,這種“世界上僅見的現象”,究其原因,乃在于中國所特有的倫理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伏爾泰對此深有所感,編寫詩劇《中國孤兒》,劇中崇尚武功、企圖以暴力取勝的“成吉思汗” (這是一個移植的代稱。伏爾泰將劇中的王者取名“成吉思汗”,乃是鑒于歐洲人最熟悉的東方“暴君” 是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義。伏爾泰在這個詩劇的前言中寫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體現了理性與才智對盲目和野蠻的力量具有自然的優越性。”[注]《伏爾泰全集》 第一集。
(二)“哲學代宗教” 思潮與中國哲思
在德國,以“哲學的宗教” 來代替正宗的宗教的哲學思潮。也受到中國哲思的影響。黑格爾雖輕視中國哲學,但他認為中國在宗教方面“是依賴自然界的各種對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質的上天”[注][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75頁。卻一語中的,而中國的這種宗教觀念對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出現的自然神論有某種啟迪。
在英國,啟蒙學者也常常引用“中國人的議論” 來批駁《圣經》。例如18世紀早期的自然神論者馬修·廷德爾在其思精之作《自創世以來就有的基督教》 中,把孔子與耶穌、圣保羅相提并論,將其言行加以比較,從中得出“中國孔子的話,比較合理”的結論。英國哲學家休謨(1711—1776)曾說:“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學徒”,因此,中國哲學可以作為英國自然神論者的思想資料。
中國哲學宗教色彩淡薄,而倫理準則滲透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這一特質也引起歐洲思想家的廣泛注意。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1723—1789)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倫理若無政治的支持,便毫無力量,政治若無美德的支持和協助,便岌岌可危,迷失方向,倫理的目的在于告訴人們,最大的利益在于實行美德,政府的目的則促使人們這樣去做”[注][法]霍爾巴赫:《社會體系》,黃楠森、沈宗靈主編:《西方人權學說》 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德國哲人萊布尼茨也說道:“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么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 他說:“就我們的目前情況而論,道德的敗壞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正如我們給他們派了教士去傳授啟示的神學那樣。” 直到法國大革命,中國哲學中的德治主義還對雅各賓黨人發生影響,羅伯斯比爾(1758—1794)起草的1793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的第6 條引用中國格言:
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然,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 其道德界限則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法國憲法集》,1970年,巴黎,第80頁。
中國哲學對歐洲思想家的影響是經過他們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才發生作用的,他們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國文化,帶有明顯的理想化色彩。但是,中國哲學對于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思想體系的完善確乎發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法國學者戴密微高度評價這一東方哲學流向西方的現象。他認為:“從16世紀開始,歐洲就開始了文藝批評運動,而發現中國一舉又大大推動了這一運動的蓬勃發展。”[注][法]戴密微:《中國和歐洲最早在哲學方面的交流》,《中國史研究動態》 1982年第3 期。
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并不局限于18世紀。從19世紀中葉開始,歐洲加速了同中國的文學、藝術、哲學的融合。就德國而言。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初年間,出現一種可稱之為“東亞熱” 的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歐洲文化危機,使不少知識分子再次把目光轉向東方,希望在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文學中去尋找克服歐洲文化危機的辦法。德國哲學家、戲劇家布萊希特(1898—1956),便注目中國古代哲學,贊賞墨子學說對于解決個人與社會取得和諧問題的探索,其“非攻”“兼愛” 等思想常被布萊希特援引。老莊修身治國、“柔弱勝剛強” 的理論也為布萊希特所贊賞。他的《成語錄》 采用中國古代哲學著述常見的對話體裁,處處流露出將墨翟引為忘年交的感情。中國哲學給布萊希特與德國表現主義戲劇家的哲學論爭提供了有力的論據,開拓了他的眼界,使他從一個歐洲學者變成一個世界性哲人。
中國傳統文化在19世紀的俄國也頗有影響。俄羅斯近代文學奠基人普希金(1799—1837)深受啟蒙時代法國出現的“中國熱”感染,作品吸納中國元素,詩歌《致娜塔麗婭》 出現“謙恭的中國人”,《魯斯蘭與柳德米拉》 出現“中國的夜鶯”,《驕傲的少女》 出現“去長城的腳下” 等句,顯示了對中國文化的向往。[注]見柳若梅:《普希金筆下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2年7 月20 日。俄國文豪托爾斯泰(1828—1910)對中國傳統哲學極感興趣,他研究過孔子、墨子、孟子等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學說,而對老子著作的學習和研究則持續到暮年。他在日記中說,“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是令人驚異的。老子的學說——執行自然法則——同樣是令人驚異的。這是智慧,這是力量,這是生機”,“晚上全神貫注修改墨子。可能是一本好書”[注]轉引柳卸林主編,董平等譯:《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547頁。。他認為,孔子和孟子對他的影響是“大的”,而老子的影響則是“巨大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惡” ——在很大程度上便得到老聃“無為” 思想的啟迪。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國傳統哲學對人們的吸引力持續不斷。當東方的人們為西方科學技術的大量涌入而應接不暇,嘆為觀止之時,西方一些思想家,痛感西方工業社會弊病叢生,終日被一種無限的荒漠感所包圍,不知何處是邊際,何處是歸宿,看不透,沖不破,走不出。他們又一次把目光投向東方,到中國古代圣賢中去尋找人生的意義和真諦,尋覓來自內心,來自精神世界的幸福。這也是當今值得注意的一種文化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