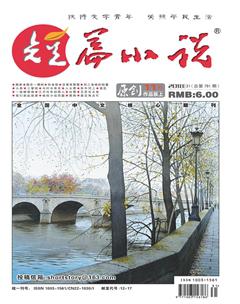和三角褲的較量
余顯斌
1
突然就想起莫老師,依然笑笑的,彌勒佛一般。
莫老師脾氣好,大家都愛臟派他,開他的玩笑,無論啥話,他都照單全收,從不冷臉,從不發惱,也因此得到老佛爺的稱號。那時,他的文章已寫得全國開花了,據業內人士評價,在小小說界近十年殺出的三匹黑馬,幾乎寫瘋了,一個是山東的,成了省作協副主席,一方寫作諸侯,人五人六的,挺著個啤酒肚子;另一個是湖南的,七十多的老頭子,白須飄飛,仙風道骨,是省作協的顧問。只有莫老師仍在教書,鱉瞅蛋一樣守著小鎮,從未挪步。有一次我去省里參加語文教學研討會,有個戴著眼鏡的高考專家談到高考文章時,說莫老師文章是樣板,可以多研究研究。當聽說我和他同事時,那人帶著不信的神態道:“真的啊?”然后就打聽莫老師是個啥樣的人。
我說,一般化,不是丑男,也絕不是帥哥。
那人說,莫老師低調,如是一般人,早喧嚷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回到單位,我談到我對他的介紹,他放下杯子哎了一聲,埋怨我為什么不說他是帥哥、小鮮肉一類的人,目光一閃,電倒一片。說著,他還特意做了個放電的神態,小小的眼睛連眨幾下。
莫老師不低調,有時甚至是很狂的,起碼就曾狂過一次,是省文化廳準備照顧一批寫作人,叫啥百人計劃。他知道消息,是一個作家告訴他的。作家說,趕快聯系,有很多優惠條件,大家都削尖了腦袋朝里面鉆,估計百人都已經滿了。莫老師連連哦著,就手忙腳亂地打開文化廳的網站,果然就看到一百人名單公布著,下面有個電話號碼,注明,如果認為某人不合格,可以舉報。莫老師坐在電腦前,呼哧呼哧半天,對當時也在旁邊的我說:“打個電話?”
我點點頭,在心里暗罵,真正日先人,這叫啥事嘛!
他打了電話,那邊是個男人接著。莫老師清了一下嗓子道:“請問名單下面放一個電話號碼是啥意思?”對方回答,有誰不合適,可以舉報的。莫老師聽了激動起來,狂性大發道:“我告訴你,沒有我的名字在里面,這里每一個人都不合格。”我傻傻地看著莫老師,他的臉很紅,眼光在鏡片里如刀一樣橫切出來,閃閃發光,讓人感到害怕。對方顯然也被這句狂言激怒,在那邊問:“你又是誰啊?”那個“又”字咬得很重,如咬著鐵丸一樣,明顯地帶著譏諷味道。一響樹葉落下都怕砸破頭的莫老師,這次竟然上演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梁山好漢風采道:“你聽著,我叫莫書涵。”對方愣了一會兒,告訴他:“這次選人,三個月前就向各市作協下發了文件,讓參選作家將材料書籍送上,可一直不見你的啊。”然后,對方勸他,說以后有機會時一定考慮到他,請他稍安勿躁。
那邊電話掛上,他坐在那兒,呼哧呼哧的。
他老婆埋怨那個告知他消息的作家,既然要告訴就早告訴啊,現在一百人滿了才告訴,不是故意讓人生氣嘛。莫老師聽了苦笑道:“人家還告訴了哎,有的平日親熱得換褲子穿的朋友,不是都鉆入烏龜王八窩里不吱聲嘛。”那一天他一個字沒寫,就那樣坐著。
第二天,我們再翻看那個網站時,張貼的名單已經不見了,舉報的電話也不見了。
幾天后,在那個朋友微信中,他發現百人計劃會召開,他的朋友在里面,對著鏡頭,一個五十多歲的老男人,做出一個很女人化的招手動作。他大怒罵道:“操蛋,好些都向我請教過寫作呢,這會兒都人五人六的!”
2
我們學校在一個小鎮上,這兒水色環繞,一片白亮,地方在江北,可又有江南韻味,用破詩人的話說,是江北和江南做愛,生出小鎮這么個混血兒。
這兒有一種風氣,大家都愛寫文章。
很多上面領導來檢查,挺著肚子說:“嗯,滿滿的都是正能量。”學校領導聽了,都臉紅紅的,仿佛覆著一層陽光。可也有一個例外,這個例外就是我們年級組的王副主任,那臉色如吊茄子一樣,灰塌塌的。
我們學校有個制度,每個年級由一個教學副主任管著,主抓一切,包括年級人事安排,包括年級各種款項花用。說白了吧,王副主任就是我們年級組的土皇帝,我們就是他手下的臣民。他每次背著手從我們面前走過的時候,即使我是男的,仍有一種被皇帝巡視翻牌子的惶悚,汗珠冒出,難以自已。
我是才調來的,莫老師特意叮囑我,注意著這王八蛋。
我忙問為啥。
他說,才能和氣量成正比,能入得針鼻子。
我聽了,更感到惶悚不安。
我們每次寫作,或者一起說道文章時,王副主任就會背著手走過來,乜斜著眼睛望著我,如餓了三天的狼突然抓獲一頭小羊的樣子,許久道:“小王吧,跟著大師想學做大師啊。”我聽了,知道他話里有話,知道我這會兒如一只雞被他抓住,他正舉著刀,準備隨時一刀下去,讓旁邊的猴們看看。我于是就腦門發汗,渾身發熱。
有一次,他又來抓我這只雞了,看我正在寫東西,就說:“小王吧,向大師學做大師啊。”
莫老師笑笑,對他道:“老王吧,咋的,不可以啊?”說完,莫老師意猶未盡地對我說,“以后他喊你小王八,你就喊他老王八。”大家聽了都忍不住笑了,一個女教師一口水剛喝到嘴里,噗的一聲噴泉一樣噴出,灑得漫天花雨。王副主任就嘿嘿笑著,回頭對莫老師道:“那可是你罵人家未來作家啊,可不是我啊。”說著,他轉身慢慢走了。
也因為這,王副主任會上批評:“我們一些新同志啊,啊,功名心太重了嘛,要將心思放工作上。”說著,他將眼睛掃過來,掃得我頓時矮了一截。
一次,他再說的時候,莫老師站起來:“王主任,不寫文章干啥?”
王副主任眼睛光一翻:“看課本啊。”
莫老師再問:“課本看好了呢?”
王副主任回答:“備教案。”
莫老師仍不緊不慢問:“然后呢?”
王副主任臉紅了,瞪著莫老師。莫老師仍不緊不慢道:“他不會像你那樣整天上網和美女聊天,不寫作干嘛?”
王副主任生氣了道:“我……啥時和美女聊天了?”
莫老師笑嘻嘻地問:“你忘了?那次去你辦公室,你一句一個親的。”
王副主任臉色有點白了:“我是和我老婆。”
莫老師做出驚訝萬分地樣子道:“你老婆美容了啊?”看大家一臉不解,莫老師說,“頭像里是個大美女啊。”
王副主任手一揮,告訴大家:“散會散會。”
于是我們就散會了,路上,莫老師慢騰騰地對我道:“啥東西,老鴰捉柿子專揀軟的來。”
莫老師這樣說王副主任,是因為他曾做過軟柿子,被王副主任啄過。
莫老師和王副主任本是扯不上關系的。王副主任開始是年級組長,莫老師教著語文。那時,鎮中學進行校建。王副主任就毛遂自薦,學校的標語校歌,還有其它東西,自己包圓了,不用請別人,那樣太花錢太浪費了。可是,后來不是他,是莫老師。一月工夫,莫老師完成了任務,質量還可以,來校參觀的人看了都說:“呵,不愧是名校啊,有文墨人啊。”
莫老師聽了,胖胖的肚子鼓鼓的,更大了。
王副主任的臉吊得更長了,幾乎拉到了褲襠,得用一塊布兜著。
到了晉級的時候,莫老師希望借助這些優勢,過關斬將,晉級成功,成為一名光榮的一級教師。王副主任也瞪著眼睛,望著一級教師職稱。可惜,學校有制度,一切按照制度辦事,兩人最后都是狗咬豬尿泡,空歡喜一場。
莫老師那兩天垂頭喪氣的,如被一棒子打中了脊梁的狗,拖著尾巴走路。王副主任卻整天唱著“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到處亂竄。有人不解,就問:“你晉級不成,咋還恁高興啊?”王副主任女人一樣,悄悄乜斜了莫老師一眼道:“有人整天舔著學校的肥尻子,還不是沒有晉成嗎?”
王副主任因為這才感到解氣,感到高興。
莫老師聽了,轉身走了。
我知道了很不舒服,就找到莫老師,問他當時為啥不反擊兩句,這樣懦弱,給我們寫文章的人丟臉,沒有文人骨氣。他解釋,那人說那話是一種標準的酸葡萄心理,自己故意這樣,讓他有酸氣也無處發泄,活活憋死。說到這兒,他問我:“你說,如果你在街上走,突然有人跑來將你砸一石頭,然后叫著笑著跑了,那是啥人?”
我不知他突然這樣問啥意思,回答:“神經病人啊!”
他笑著說:“如果你拿著石頭追上十幾里,還擊一下那個神經病人。完了,世界從此又多了一個神經病人。”
他說完,顯然為自己的幽默而得意,嘎嘎大笑,如一只企鵝一樣。
3
在和王副主任的矛盾中,王副主任高唱凱歌,攻城略地。莫老師一路敗退,丟盔棄甲。
至于他們之間矛盾初起的緣由,是因為創辦校刊的事。
創辦校刊,是和破詩人有分不開的關系的。破詩人曾因詩歌,引來很多美女青睞。他吹噓說,他走出去,每次都是踩著一路美女的眼珠子回來的。說完,他還抖抖衣服,好像是特意抖落粘在身上的美女眼珠子似的。他的老婆就是他的粉絲,讀了他的詩,就春情大發,千里迢迢趕來投懷送抱的。大概因為這樣吧,破詩人對于文學的熱情,和對懷中美女的熱情一樣空前高漲,難以遏制。他在寫詩,在充分享受美女微笑的同時,準備辦一個校刊。
破詩人有這樣想法,就去慫恿莫老師:“老師,學校最近幾年發展呼呼的啊。”莫老師點著頭,嘴里咬著豆芽,咯吱咯吱響。破詩人接著說:“質量呼呼飆,校建呼呼飆,你說還缺啥啊?”莫老師喝杯酒說:“校園文化啊。”破詩人手一揮,啪的一聲拍在桌上,把莫老師嚇得一哆嗦,抬頭望著他。破詩人很歉意地笑笑:“那……校園文化中啥東西最重要?”莫老師開玩笑說:“你一拍桌子,我以為你要打人哩,嚇了我一跳。文化建設……校刊嘛?”
破詩人舉起巴掌,準備再拍桌子,又停下道:“老師,你出面辦一份校刊吧?”
莫老師搖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弄這些的。
破詩人繼續慫恿,破詩人的言辭,能華麗地讓一個美女死心塌地地投懷送抱,別說莫老師這樣的老男人了。破詩人描繪校刊辦起后的燦爛前景,還有對學生的生葉開花的作用。莫老師一聽,熱血上涌,就在破詩人美好言辭里不知不覺迷醉,找不到北了,誰知辦刊后碰壁連連,以至于悔恨莫及,常常指著破詩人道:“你個詩人啊,真正的破詩人。”也因為這,詩人就成了破詩人。
校刊辦起來本是好事,很多娃娃的文章從校刊里走出,身子一扭,進入到了國家刊物里,可是問題也隨之出現了。一次,校刊刊登了一篇學生的文章,是有關周瑜諸葛亮和劉備的,小孩子文筆不差,但喜歡用文言文寫,這樣一來就不通暢不自然了,如小腳女子穿著高跟鞋,磕磕絆絆的。王副主任如《動物世界》里的鬣狗嗅著獵物了一樣,哈喇子流著趕來,指出文章的錯誤。莫老師面對批評,擺出一副誠懇接受的樣子。
王副主任鑒于莫老師態度,感到很得意,提出自己來此的目的:為了免于刊物再次出現歷史性錯誤,自己衷心希望,編輯部有必要聘請一個德高望重的歷史老師做歷史顧問。
莫老師連連點頭說:“需要需要。”
王副主任肚子一挺,指著自己道,如果莫老師認為可以,自己打算毛遂自薦。
莫老師再次笑著說:“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王副主任一杯茶后,挺著肚子心滿意足地走了。離開時,莫老師還專門送了他幾本書,都是自己出版的歷史集子,恭請這位德高望重的歷史名家指點一二。
王副主任拿了書轉身剛走,莫老師就冷哼一聲道:“人可以自信,但不可以毫無羞恥地自信。”我不知他說的誰,望著他,他指指門外道,“寫作方面,我用腳趾頭,他用手指頭,他不是我的對手;歷史文章,我用腳趾頭,他用手指頭,他也不是我手下的三合之將。”
莫老師沒有聘請王副主任做歷史顧問,他也沒那個權利,因為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編。
王副主任也沒有指點他的歷史著作,不久,臉如吊茄子一樣拉著來還書說:“太高深,我看不懂。”
4
大家私下里稱王副主任為三角褲衩,我弄不清啥意思,就問莫老師。莫老師笑著說,小孩子家家的,這些話不能告訴你。他說完還補充一句,這個家伙,憑著三角褲起家,把別人名聲都連累臭了,簡直是一顆老鼠屎害了一鍋粥。
我再問原因,他仍笑瞇瞇的,說要保護少年兒童,不能臟了下一代的心靈。他越這樣,我就越著急,越希望知道其中的內幕。
最后,磨得沒辦法了,還是破詩人告訴了我。破詩人莊重地伸出一根手指說:“你得發誓,別說出去。”為了獲得一手資料,我舉起手嚴肅發誓,我如果說出去,以后一輩子打光棍,憋死活該。在破詩人想來,一輩子打光棍是一個非常毒的誓,因此,他咳嗽一聲,讓我倒一杯茶,他慢慢喝著,慢慢講述著故事的內幕。
他說:“有一段時間啊,很奇特的,也很溫馨的。”破詩人講故事時,愛營造一點氛圍,吊大家胃口。感覺到差不多了,他接著說,王副主任老婆每天風雨無阻,來給王副主任送飯,那種殷勤勁兒,那種黏糊勁兒,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大家都羨慕得眼睛放光。破詩人甚至暗暗咬著手指發誓,將來娶一個老婆,一定要如這女人一樣溫柔似水。可是,問題來了。破詩人講到緊要處,站起來,手輕輕一拍,如說書的一般道:“諸位,常言道,金風未動蟬先覺,當事者是最為警醒的。”他說,老婆突然如此溫柔體貼如此蜜意如水,大概也讓王副主任第六感蘇醒,高度警惕起來。于是,王副主任有一天就提前回去,“你們猜猜,他看到了啥子?”
顯然,大家都早已知道謎底,都懶得去猜。只有我仍傻傻的,大惑不解地問:“啥子?”
破詩人說,王副主任老婆和老婆單位的頭兒正在醉生夢死著。
我驚訝地問:“喝酒啊?”
破詩人氣得睜著眼睛,一掌拍在我的肩膀上道:“瓜蛋,在床上是喝酒啊?”
我知道在干啥了,睜大眼睛:“咋可能?”
散文老師在旁邊,帶著極為肯定的語氣反問我:“咋不可能?”
我說,王副主任老婆我見過,那是一眼之后,欲望全失的對象啊。
破詩人打量著我,斷言我完了,成不了作家了,作家應當有想象力的,有沖蕩一切束縛的思維的。說著,他很色情地道:“人丑鋼火好,絞鋼斷鐵。再說了,窗簾一拉如黑夜,啥都一樣的。”他說,也因為那事,那個騷情頭兒短處被捏,不得不替王副主任四處說盡好話,求爹爹告奶奶的。也因為這樣,王副主任憑著那副德行,在原來學校就成了領導,到鎮中學,也順理成章成了領導。
我們都笑,都指著破詩人,說他一臉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的男盜女娼,想得太惡心了。破詩人毫不以為意,指著桌上盤子道:“沒葷菜,權當一盤葷菜,大家品嘗啊。”
散文老師笑笑,夾了一筷子肉片塞在破詩人嘴里問:“味道咋樣?”破詩人咀嚼著,點著頭說不錯,就是太爛了,沒有嚼頭。說到這兒突然想到自己挨了罵,就呸的一聲吐出肉片,做出哇哇嘔吐的樣子道:“我一個詩人是嘛人?寧嘗鮮桃一個,不吃爛杏一筐。”
大家都哈哈大笑,破詩人也哈哈大笑,突然又不笑了,做出很神秘的樣子道,這回慘了,莫老師可能不能上高二了,得留在高一。我們學校有個潛規則,一般帶課不行的,成績馬尾巴穿豆腐提不上串的,一般到了下半年開課時候,就會被留在原年級,其余的老師隨著年級走,原來一年級的就上二年級,二年級的呢就去三年級,叫跟班走。我們都睜大眼睛望著破詩人,莫老師留著不許跟班,咋可能?傳出去不是笑話嗎,絕對能做為一條笑掉牙的新聞?我們就說破詩人又在散布謠言,一天不散布謠言好像會死一樣。破詩人一臉無辜地發誓,自己這次說的絕對絕對真實,如果虛假的話,自己甘愿再吃一片肥肉。
我們說:“美的呢,還吃肥肉呢。”我們讓他重發毒誓。
他說,他如果虛張的話,受罰一年不說話。
散文教師說,這對破詩人的懲罰是震古爍今的。我們一致通過,接著就詢問是啥原因。
破詩人搖頭晃腦地說莫老師得罪了王副主任啊。他說王副主任是我們年級的皇帝啊,一個平頭百姓得罪了皇帝,沒有被殺頭就已經算吾皇開恩了,死罪免去活罪難免,自古是帝王的最高治術啊。
我們看他說的如此莊重,就詢問莫老師究竟怎么王副主任了。
破詩人說:“屁事。”
我們問:“啥屁事啊?你倒是說啊。”
破詩人說,莫老師和王副主任那天聊天,聊著聊著,不知道咋的就說到了辦刊,莫老師說自己最近很忙,教書之外,又得編刊,滴溜溜轉著如猴兒一般。莫老師這樣說,大概是在顯示自己日理萬機呢,卻讓王副主任抓住了話茬子說:“你在學校究竟是編刊的啊還是教書的?”莫老師說,書得教,刊物也得編啊。王副主任認為莫老師不該這樣說,這樣說是頂撞了自己,傷害了自己至高的權威。王副主任的臉就紅了,如猴兒屁股一樣說:“你要編刊,下學期就別上高二了,就去給學校編刊吧。”
莫老師笑笑道:“好啊,你去給學校說說吧。”
王副主任哼了一聲,翻著眼睛背著手走了。
破詩人說完,我們都等著下文。破詩人不講了,拿起筷子夾起盤子里的花生米吃著,咯吱咯吱的。我們急了問:“說啊。”他一攤手說就這些啊還說啥啊。我們說就這點破事啊。破詩人用筷子點著盤子咣咣地響,解釋說,這事對別人而言是小事,對于王副主任來說是大事。看我們傻乎乎地不解,破詩人分析:“王副主任為了做領導,老婆都送出去了,損失大不?”我們都點頭,認為損失確實不小。破詩人接著很內行地分析,“他這樣為了啥?不就是為了享受一下權力帶來的滿足感嗎,不就是想用權力來撫平內心的傷痕嘛?”說完,他斷定,莫老師完了,這次一定會吃虧的。
我們都笑著搖頭,這是一件鳥毛大的事,詩人就喜歡夸張。莫老師那天沒來參加聚會,去聯系出版刊物,第二天聽到破詩人的預言道:“啥破道理?不會的。”
可是,我們都認為是不會的事情,就被破詩人給料到了。
到了假期加班學習期間布置任務時,莫老師瞪大眼睛驚訝地發現,高二教師名單里沒有莫書涵三字。他以為自己看錯了,再睜大眼睛看一遍,還是沒有。他想想,拿起手機撥了王副主任的電話,沒人接。他再撥打一次,仍然沒有。他于是發去一個信息:王副主任,請問怎么沒給我安排課啊?然后,他緊跟著打了個電話,那邊接了,一個聲音如上吊剛剛被解下繩頭又活過來的口吻道:“你——誰啊?”
莫老師說:“我啊,莫書涵啊,王副主任,咋沒我的課啊?”
王副主任哼了一聲,在那邊道:“那次我和你說惱了,我讓你別教學去辦刊,你不是說好嗎?”說完,那邊掛了電話。
5
長長的假期,我們在組織學生學習,莫老師就穿著一條短褲一件襯衫,在街道四處轉悠著。有時看見我們去上課,他就很羨慕,就問我:“小王,累不累?”
我說累啊,一節課下來渾身都汗透了。
他想想說:“我替你上一節咋樣?”
我眼睛一亮說好啊,這樣我就能歇一節,喘一口氣。莫老師拿過書翻上幾頁,又長嘆一口氣道:“士可殺不可辱,我姓莫的還能讓那王八蛋笑話。”他說著朝校園里望望,轉身走了,去河邊轉悠去了,仍然邁著緩慢的步子,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
另一個下午,我和破詩人去他家里玩。他在看著一本書,說自己都困得長霉了,然后談起上課的事情,談起讓他留下的事情,他苦笑一聲道:“這個王八蛋下手還真準,打中了我的七寸,我幾乎能用腳趾頭打敗的人,現在竟然輕易將我打敗。這事要是傳出去,外面一些朋友曉得了,還不笑話。”
我們勸他,別那么想,看開一點兒。
破詩人說:“你不是被他打敗的,是被三角褲打敗的。”
莫老師一愣,不知是什么意思,我也是的。破詩人慢條斯理地分析,王副主任如果沒有房中捉奸的事,就不會有后來的風生水起,如果沒有風生水起,莫老師就不會如此。所以,莫老師應該想開點,權當被三角褲打敗了。說到這兒,破詩人開玩笑,要打敗王副主任很簡單,靠文字是絕對不行的。莫老師忙請教靠啥,破詩人賊眉鼠眼道:“讓嫂子也去找那個不看貨色只尋下水道的人,玉體橫陳,你也趕去捉奸,他不就也替你到處跑腿求人了嘛?”
我們都嘎嘎地笑,莫老師也笑,呸的一聲,指著破詩人說:“你家伙壞的,把我看成啥人了?把你嫂子看成啥人了?”
我們都說開玩笑嘛,消消氣的。
莫老師嘆口氣,告訴我們,假期很長,他參加了一個暑假支教團,專門選中西藏一帶,準備出去走走。我們問為啥,他說他只會教書,去教教孩子們玩玩,也算幾十天不閑著。他說,一次在一張圖片里,他看到一個西藏的孩子,一雙大眼睛圓溜溜地望著外面,一下就擊中了他,他就想,如果有時間的話,就去西藏走走,去盡一份自己的力。
我們都說,出去看看也好。
他于是就走了,在群里給我們發了個信息:兄弟們,你們忙,我去西藏了,到時給你們拍照片。不久,就真的有照片傳來,他和支教學校孩子的照片,孩子們笑著,臉上陽光燦爛的,帶著兩抹高原紅,他也笑著,人卻有些黑了。
我們都紛紛點贊,表示羨慕。
他告訴我們,回來了,他就準備動手寫遠行西藏的書稿。他說,等著吧哥們兒,到時你們會羨慕死的。
我們都說拭目以待,一定要拜讀他的文章。
可是,后來他的照片沒有了,他的留言也沒有了,他如蒸發了一般。十多天后,西藏那邊傳來信息,他走失了。他是去家訪的,那天的天氣開始還好好的,如干凈的微笑。可后來就雷電交加大雨傾盆,天地一片黑暗,鍋底一樣。此后,他就再也沒有出現過,學校打電話詢問家訪的孩子,根本就沒見他人。學校急了,就報了警。警察和當地居民結隊尋找,走遍他可能去的地方,啥也沒有。
學校校長說,莫老師離開時穿著紅襯衫啊,很好尋找的,咋就找不見人啊?
有老年人說,雪域高原上有一種女妖,很漂亮,整天在雪山頂上對著陽光唱歌,看見英俊才子,就會柔柔地一笑,愛上那人,并留下他一起在雪山唱歌踏雪。一般定力稍差的男人,一旦看到女妖,也會被她的微笑和美麗所魅惑,樂不思蜀的。可莫老師并不英俊,甚至還有些丑啊。再說了,他的定力好像還可以的,從無緋聞的。
我知道那是一個傳說,但我又希望那是真的。
后來,我離開了小鎮中學,背著行李在外面四處漂泊著。那一晚上,在一個城市旅館的床上,我做了一個夢,夢里也是走在一處城市的角落里,轉過街角,被一個人撞了一個趔趄,抬頭一看不是別人,竟然是莫老師,這么多年了,他仍然穿著去西藏的紅襯衫。他望望我,好像不認識我似的,徑直走了,很快消失在來往的人群里。我醒來,第二天接到在省作協工作的破詩人的電話,他說他昨夜做了一個夢,夢到了莫老師,還是穿著原來的紅襯衫哎。
責任編輯/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