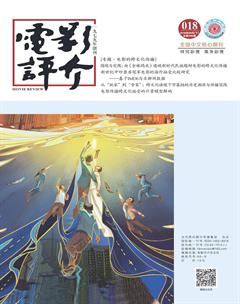臺灣電視劇文化訴求的歷史嬗變與當代轉向
張帆 黃婉彬
一、 中華文化:臺灣電視劇的根性訴求與文化緣起
臺灣電視劇的“根性文化”訴求是從臺灣電視劇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有顯現的,只是隨著臺灣社會的風云變幻,出現了不同階段性的“沉浮”。臺灣電視劇“根性文化”訴求最好的體現是在解嚴之前,國民政府利用強大的統治力創造出“想象的共同體”“以構建出‘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大中華民族主義”[1],體現出其強烈的中華文化這一“根性訴求”;臺灣解嚴后,商業主義和消費文化的發展,根性文化訴求逐漸減弱,成為文化消費的“籌碼”;而進入到新千年,“根性文化”更是逐步削減。
隨著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臺灣中產階級逐步形成,國際社會風云突變,國民黨外的民主運動逐步興起,這些變化給臺灣社會帶來不小的變化和沖擊。電影界也拍出了《香火》《原鄉人》等尋根影片,以及反映臺灣社會變化的相關電影,“文化界探尋臺灣于祖國地緣血緣關系的文化尋根活動”[2],這些文化動態也深深地影響到臺灣電視劇的制作,如何通過影視作品縫合這種社會的“裂痕”是創作者思考需要面對并解決的問題。此時,臺灣電視劇大多以家庭為敘事的中心內容,這些內容的表達有其自身的藝術特色和文化價值,意蘊大多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觀的表達,加之聯播時期的政府管控,臺灣電視劇呈現出強烈的中華文化“根性訴求”,主要表現為對中華倫理與傳統美德的彰顯,以及對中華歷史的認同。
無論是仁義禮智信的氣節,還是溫良恭儉讓的禮節,儒家文化可謂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性之一。兩岸在地緣相近、血緣相親、文緣相承,大陸儒家文化中的“宗族制度、鄉族制度、科舉制度、文化思想帶到臺灣,世代相傳,成為臺灣的本土文化”[3],儒家文化也成為臺灣社會凝聚中華力量的精神支柱與道德規范。這也是盡管不同時期臺灣遭遇到不同殖民者的統治,依然能夠在精神層面上不被“殖民”的歷史原因,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節義的力量不可低估。蔣介石來到臺灣后也大力頌揚儒家文化,尤其是推崇“倫理”。早期臺灣電視劇的主創人員大多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因而,儒家文化中的倫理道德成為其待人接物的處世準則,更是成為其藝術創作的思維定勢。臺灣早期的電視劇幾乎都是對中華文化中儒家倫理文化的傳播與贊譽,如《歡樂家園》《春閨孝女心》《寒門孝子心》等,這些電視劇無一不體現儒家文化中倫理孝道。這些臺灣電視劇在傳播“戲劇”的同時,也是對中華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彰顯。如果說臺灣電視劇對中華文化根性訴求中“倫理”的呈現稍顯抽象,那么“美德”的弘揚則更加具體。無論是親情美還是友情美,無論是立志圖強還是拼搏向上,這都是中華文化中傳統美德的外在形式。臺灣第一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以主人公萬里尋母故事為整體框架,通過曲折的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牽動著電視機前的觀眾,它是一部以“歌頌中華民族的親情美、人情美作為自己的重任,從而譜寫出千千萬萬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的作品[4];中視制作的《母親》以其歌頌偉大的母愛為主旨,具有強烈的感人的效果和說教人心的功效,因此,該劇還獲得了“教育部”的獎勵。
進入到臺灣電視的“聯播時期”,臺灣電視劇也呈現出“另類極端”的文化指向,盡管這種指向是中華文化的根性訴求。“聯播”的初期,國民黨以“反共抗俄”為名,在社會上實行“白色恐怖”,與電視業相關的有“大陸烏龜”事件、“大哥,不好了事件”“東方紅”事件等。國民政府一直停留在“反共復國”的理想之中,于是要求其管制下臺灣各電視臺要加緊政治鉗制,肩負政治宣傳、教化使命,“對文化藝術進行嚴格控制,積極推進和倡導為‘反共復國服務的‘戰斗文藝”[5]。1976年出臺的《廣播電視法》對臺灣廣播電視節目的內容加以限制;1983年4月, “新聞局”更是頒發了關于電視節目“先審后播”條例。這一時期的臺灣電視劇幾乎呈現出完整統一的“文化訴求”,那就是“反攻復國”政治理念。其間,包括《藍與黑》《寒流》《風雨生信心》《河山春曉》等。其中,《寒流》更是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親自策劃監制,該劇全盤否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偉大歷史功績,此時的“電視劇在兩岸政治抗衡的角色,成為一種凈化人心的工具”,也成為當時臺灣電視連續劇一種特殊的現象。
二、 消費文化:臺灣電視劇的大眾訴求與類型生產
誠如前文所言,臺灣電視劇在起步的發展階段主要呈現出中華文化的根性訴求,但不可以忽視的是,在文化工業化、文化產業化、文化商業化等詞匯粉墨登場后,臺灣電視劇的發展也受到多種利益的鉗制,呈現出消費文化的大眾訴求。這使得原本試圖“真實再現”的電視劇在生產創作的過程中逐步失去了藝術性或藝術價值。相反,更多的創作者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考量更多的是受眾的喜好,而這種滿足“市場”其實就是踐行大眾文化訴求的理念。因此,臺灣電視劇的研究者才會指出:“電視劇商品化的結果,造成敘事者創作風格的保守主義,敘事者所再現的內容不再求新求變,只以觀眾已經接受的通俗模式進行小幅度修改與變化。甚或針對某些風行類型或情節一窩瘋的搶制,每過數年即換一批制作群與演員,重新制播一次。”[6]這些觀點在臺灣電視劇生產中一一得到了應驗,而商業化帶給臺灣電視劇的正是大眾訴求與類型生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臺灣電視劇出現類型化的趨勢,這便是臺灣電視劇大眾文化訴求的原點,也成為臺灣電視劇的“黃金始點”。盡管臺灣電視劇的制作者在生產過程中滿足了大眾文化訴求和民眾審美的口味,或考慮到商業化利益和產出,但仍然出現了一些好的電視作品,如《一剪梅》《昨夜星辰》《星星知我心》《八月桂花香》《京華煙云》等。隨后,類型化生產逐漸加劇,呈現出“言情劇”“古裝劇”“武俠劇”三足鼎立之勢。在臺灣電視劇的歷史上,“言情劇”就是賺取受眾“情感”最多的電視劇類型之一,它將社會記憶進行影像的再現。從最初的《重回懷抱》就凸顯出臺灣電視劇濃濃的“人情味”,到《星星知我心》里面的母子之愛、親人之情,再到《幾度夕陽紅》的跨時代情感,可以說,“情”一直是臺灣電視劇敘事的主題,對于親情、友情、愛情的表達也是人世間的基本訴求。臺灣“言情劇”真正走向巔峰應該算是瓊瑤式“言情劇”的出現,人們通常稱為“瓊瑤劇”。這些電視劇講述青年男女的愛情故事,主題的設定抓住了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延續了人類最基本的訴求,但也正因如此,人物的模式化、故事的公式化受到人們的詬病。繼承“言情劇”衣缽的臺灣“偶像劇”也出現明顯的程式化、公式化的保守風格,而“這種制作保守風格,迫使敘述者提供的訊息必定先要經過社會、政治、經濟、道德、信仰以及美學條件等因素的壓縮與過濾。如果一部電視劇能夠同時獲得敘述者與觀眾的認可,其再現之象征符號當即能符合大眾經驗或記憶之標準模式,電視劇的再現過程因此極為值得重視”[7]。
臺灣“古裝劇”,就是大陸通常意義上的歷史題材電視劇,也有稱之為“新編歷史劇”,如中國傳媒大學的李獻文教授。臺灣電視的相關研究者對該種的類型稱謂均選擇“古裝劇”,如何貽謀的《臺灣電視風云錄》和王唯的《透視臺灣電視史》。臺灣該類型電視劇不同于大陸歷史劇,因為劇本往往在選擇人物時在意其歷史真實性,但在內容、細節的表達上并不在乎其真實性,因此,這些以這種“歷史故事”為架構的影視作品又充滿了消費主義的文化特征。也正是如此,這些臺灣電視往往都貼上了“戲說”的標簽,如《戲說乾隆》《戲說慈禧》。不僅如此,“傳奇”和“演義”也成為臺灣“古裝劇”的一種敘事風格,如《楊貴妃傳奇》《秦始皇的情人》《嘉慶君游臺灣》。“作為娛樂片,用輕松活潑的視點,去重新審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編撰一部令人開懷大笑、又較濃烈娛樂色彩的藝術樣品,應該是無可非議的。特別是對于現代社會的民眾生活,有相當好的補充、調節作用”[8],這是對臺灣“古裝劇”的敘事風格所作的合適注腳。
“武俠劇”的制作與生產也承接了大眾化、商業化的模式,但礙于表達內容的限制,在文本中還是呈現出濃烈的“中國味道”。劇中的“大俠”往往具有“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的特征,他們除暴安良、鋤強扶弱、成仁義之法,展重義之道,如《俠女尋母》《武當弟子》《洪熙官與方世玉》《七俠五義》等。這些劇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出神入化的武功,高妙脫俗的意境,忠奸明判的人物性格,動靜對比的節奏旋律”[9]。除此之外,這些劇目已經呈現出一定的“家國”情懷。“武俠劇”將中華文化中武道、術道、仁道、義道等精神貫穿于俠骨柔情的故事中,在捕獲許多觀眾喜好的同時,也呈現出濃烈的中華文化根性訴求。這些劇都具有鮮明的主題意識,重民族氣節,講國家義氣,恪守中華文化的傳統倫理道德,《義薄云天》中的趙燕翎、《雪山飛狐》中的胡斐、《射雕英雄傳》中的郭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他們有江湖道義,也有俠骨柔情。對于觀眾而言,吸引的不僅僅是“故事”的演繹,還有“文化”的傳遞。
三、 本土文化:臺灣電視劇文化訴求的當代轉向
每一部電視劇都帶著某種天然的“味道”,而這種“味道”正是來源于“土地”的氣息,具有“土地”的神韻、節奏、靈氣,這一切都是對于“本土文化”的外在顯現,而這又源于創作者的“本土意識”。秦忠在《談談電視劇的本土意識》一文中這樣說:“電視劇的本土意識是創作者有意識的對選定的素材或題材中蘊藏的地理、自然特色以及長期生存其中的人們的情感和記憶、文化傳承和思維、心理和性格這種綜合體的關照和把握。”[10]臺灣電視劇在多種因素的引導下呈現出濃厚的臺灣本土文化訴求,這些文化訴求主要體現在兩個面向上:臺灣精神的在地創作與臺灣故事的情感重。
臺灣精神是什么?臺灣東吳大學哲學系葉海煙教授在其著作《臺灣人的精神》中從歷史、文化、哲學等多個層面探討了臺灣人的精神;臺灣逢甲大學的李永明認為:獨立自主的精神與人格才能構成所謂的“臺灣精神”。兩位教授從各自視角闡述了對臺灣精神的理解,殊途同歸。因此,本文認為,臺灣電視劇中的“臺灣精神”就是創作者對人物在行為處事方面表現出來的勇敢、善良、誠實、友愛等高尚的品質與崇高的情操。“鄉土劇”是臺灣電視劇中極具臺灣本土文化特色的一種電視劇類型,也是最能夠體現臺灣文化本土訴求中“臺灣精神”的臺灣電視劇。它通過故事的發生與發展、劇中人的生活態度與行為方式來展現“臺灣精神”,并對“臺灣精神”進行了頌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具有“人生三部曲”之稱的《欲望人生》《美麗人生》《夜市人生》和具有“臺灣三部曲”之稱的《臺灣阿誠》《臺灣霹靂火》《臺灣龍卷風》。因中央電視臺的播放,《意難忘》《再見阿郎》《又見阿郎》的系列作品也成為大陸電視觀眾最為熟悉的臺灣鄉土劇。不僅僅是鄉土劇,當下臺灣的“趨勢劇”也具有這樣的氣韻。臺視“開創節目新形態,以‘趨勢劇為概念制作偶像劇”①。趨勢劇是臺灣社會的現象及討論現代人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如社會問題、兩性關系等,來厚實臺灣大事件的原創能力,劇中的故事、場景、人物、道具等往往反映時下的流行趨勢。
臺灣電視劇也一直在創新求變,在原有的文化中尋求新變化。每一部電視劇的制作都希望觀眾體驗不同的人生,不同年代的不同心酸,不同領域階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發生在臺灣本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在不斷講述的同時,也不斷的進行民眾情感的重組。正如蔡琰教授所說:“電視劇的敘事應可視為是一個與社會訊息與文化意念皆有所關聯的傳播問題,其故事層面可用來解釋文本之情節邏輯與人物結構;透過分析故事往往就能協助人們了解電視劇所傳透的人生意義。”[11]因此,臺灣電視劇中的情感表達與本土故事折射出臺灣本土不同民眾的不同情感。鄉土劇圍繞臺灣本土進行故事創作,堅持臺灣鄉土情節,將臺灣故事發生的時空背景置于臺灣歷史之中,如《后山日先照》將故事空間背景設定在臺灣花蓮,時間背景橫跨臺灣近現代的歷史,從日據時代到二戰結束,再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所有的時空背景都聚焦于臺灣本土,展現生長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的過往歲月。臺灣本土歷史文學大戲《臺灣百合》,忠實地呈現了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這片土地上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對立與融合,獲得廣大群眾的認同與支持,對于白色恐怖時期遇難者的遭遇、對人性善惡對立的批判引發廣泛討論。除了上述還原臺灣本土風貌的“鄉土劇”以外,還出現了極具臺灣本土特色的客家文化和眷村文化題材的電視劇。客家人,作為臺灣島上的重要一部分,他們擁有自己的日常語言、生活方式、民間習俗和崇拜信仰。因此,客家文化也成為臺灣本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魯冰花》《阿婆的夏令營》《牽紙鶴的手》《春天愛唱歌》《免費搭乘》等。眷村,在臺灣社會具有濃烈的“符號”價值。眷村,是祖國大陸人居于美麗島情感的寄托,是在美麗島上原有生活方式的棲息之所,更是歷史洪流中的產物,不但見證來臺灣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在早期“前方生死與共于戰場,后方同甘共苦于眷村”的年代,更發揮來安定作用。作為一個時代的烙印,作為集體的記憶,眷村文化也出現在臺灣電視劇的創作之中,用自己獨有的手法講述眷村的故事。“眷村文化”雖然在人物行為和日常生活上呈現出根性文化訴求,但正是因為遠離大陸的那片土地,才使得原本也是“故鄉”的臺灣變成了自己的“異鄉”,還原了特定歷史時期這個特殊的群體“欲把‘他鄉當‘故鄉”的文化記憶,具有代表性的是《再見,忠貞二村》和《光陰的故事》。總之,這些電視劇在臺灣本土文化的指向上表達的非常全面,無論是臺詞對白還是情景出現,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習慣方式,都傳達出來濃厚的“臺灣色彩”,講述“臺灣人的故事”。
結語
當下臺灣電視劇的中華文化根性訴求的文本相對較少,表現的強度也相對較弱,甚至出現略“顛倒”與“轉移”,即將“中華文化”納入到“臺灣文化”的一部分,或將作為臺灣根性文化的“中華文化”實行了“外在”的轉移,使其變成“外來文化”。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中華文化才是臺灣文化的“根”,兩者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因此,中華文化才是臺灣電視劇的根性訴求。綜觀當下臺灣電視劇,無論是鄉土劇、古裝劇、偶像劇還是植劇場,無論是鄉土文化、眷村文化還是客家文化,正是臺灣電視劇的類型、主題的出現,使得臺灣電視劇呈現出如此多元的文化“景觀”,只是此時多元“景觀”已經不再是以中華文化的“根性訴求”為基礎,而是在所謂的臺灣文化的“本土訴求”下進行的選擇與展現,文化表層面的多元卻實實地折射出臺灣社會“文化一元”的面向。
參考文獻:
[1]謝國斌.族群關系與多元文化政治[M].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3:216.
[2][3][9]陳飛寶,張敦財.臺灣電視發展史[M].福建:海風出版社,1994:166,172,187.
[4][5][8]李獻文:臺灣電視文藝縱覽[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21,32,102.
[6][7][11]蔡琰.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M].臺北:三民書局,2000:69,46.
[10]秦忠.談談電視劇的本土意識[J].當代電視,200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