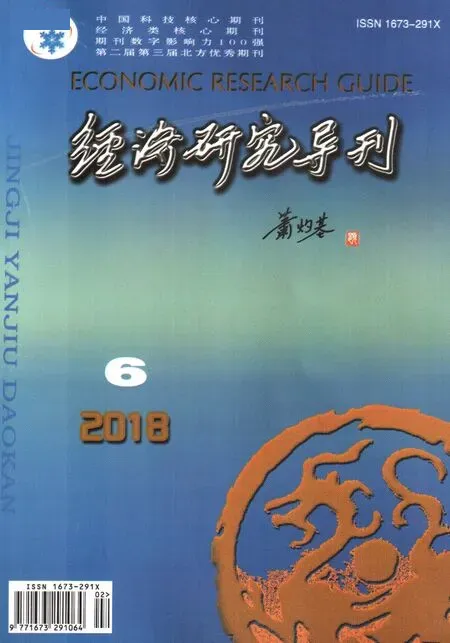“一帶一路”倡議對我國農產品外貿的影響
——基于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
柴 樺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北京 100102)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很多國家在商業貿易領域的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國際貿易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國的發展面臨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外開放面臨調整轉型,亟須通過國際合作活力激活發展動力。而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數據顯示,貿易不便利造成的交易成本大約占國際貿易總貨值的1%~15%,或將成為制約中國外貿水平發展的一大瓶頸。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訪問時提出了一同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創新型合作模式。在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合作構想后,習主席在印尼的國會上發表演說時表達了中國愿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的意愿,希望可以通過共同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共贏模式建立起海洋合作伙伴關系。“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在一起被稱為“一帶一路”,是我國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下積極應對國內經濟轉型發展需要、統籌國際合作共贏而做出的重大的決策,強調相關各國通過互相協作使得貿易便利化,交流深刻化,合作加強化,促進貿易和投資增大,從而達到互利互惠的目的。
農產品貿易是“一帶一路”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市場貿易的結構來看,我國在農產品貿易方面長期以來面臨著進出口市場高度集中等問題。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初期,我國的農產品主要出口到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而農產品進口則主要來源于美國、澳大利亞和歐盟,市場集中度居高不下。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與推進,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市場將進一步多元化。從農產品的貿易總量方面來看,我國的農產品外貿總量在20世紀以順差情形為主,自2001年我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農產品的國際貿易總量大幅提升,逆差情形開始成為新的常態。下頁圖展示了我國2006—2015年農產品進出口額的變化趨勢。數據顯示,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受到重創,貿易總量和逆差都大幅縮小。在2010—2012年期間,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呈現出較為良好的發展態勢,進出口均有一定增長。但是2013年以來,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則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
國家商務部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進口總額高達228.39億美元,大約占中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的18.8%;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總額達到210.32億美元,占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高達29.48%。眾所周知,我國農產品出口占據優勢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勞動力、土地和投入品成本長久以來處于較低水平,導致農產品的出口占據了價格方面的競爭優勢。而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的資源稟賦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我國在生產農產品方面的投入已經不再占據成本優勢。擁有更加廉價勞動力、土地資源的新興國家正不斷削弱我國農產品外貿的競爭優勢,使得我國傳統優勢農產品出口增長乏力。在我國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尷尬境地的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將大力推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合作國家之間的農產品貿易,或將為中國農產品未來的國際間貿易找到新的增長點。

2006—2015年期間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的變化趨勢圖
一、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已經對我國農產品外貿流量問題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程國強(1999)基于我國1980—1998年農產品外貿的情況,分析了我國農產品外貿發展的格局、歷程和政策含義。何秀榮和Thomas I.Wahl(2002)利用SITC數據,對我國近二十年以來農產品外貿的變化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孫林(2008)在貿易引力模型中增加了貿易集團和共同邊境這兩個虛擬變量,利用49個樣本國的橫截面數據,對貿易潛力問題進行了探究。隨著我國與東盟、非洲、歐洲等地之間的貿易合作加深,我國農產品的多邊貿易研究也逐漸得到了重視。趙雨霖、林光華(2008)探究了影響我國和東盟10國區域間農產品貿易流量的因素。張海森等(2008)研究了我國與東歐的農產品貿易情況。謝杰等(2011)則對我國與非洲國家間的農產品貿易發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孫林和譚晶榮等(2010)從分類產品數據和匯總數據兩個層面實證分析了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對世界農產品出口的影響。王瑞(2012)則基于1992—200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對農產品外貿具有顯著的推進作用,全球金融危機則對貿易流量產生了負面的影響。而在“一帶一路”建設實施的背景下,我國的農產品外貿研究則較為匱乏。“一帶一路”的推進已三年有余,已有的文獻大多通過定性方法分析“一帶一路”的實施對我國農產品外貿的影響,缺乏實證研究。程國強(2015)認為,“一帶一路”的布局將為中國農業的全球戰略保駕護航。吳莉婧(2016)從“一帶一路”的研究視角進行切入探討,認為“一帶一路”建設為我國農產品外貿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結構的改善、產業結構的升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從研究方法上來看,Tinbergen(1962)最早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的領域,在此之后貿易引力模型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拓展,已經成為分析外貿問題的主流方法。Armstrong(2007)認為,傳統的貿易引力模型估計的是各個因素影響的平均效果,而且只有少量能夠得到量化的客觀影響因素可以被引入方程,而大量諸如貿易信息不對稱、政策規定等的影響貿易的主觀影響因素無法被引入方程,導致較大的殘差項,從而引起估計結果與真實情況之間較大的偏差。魯曉東(2010)指出,傳統引力模型中“冰山成本”的適用條件過于苛刻。為了避免上述問題,隨機前沿方法被引入到引力模型中,隨后隨機前沿方法在測算貿易潛力方面被廣泛應用。
在數據處理方面,大多數研究采用SITC(標準國際貿易分類)或HS(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數據并應用貿易引力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影響我國農產品外貿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規模、人口規模、貿易國之間的距離以及是否加入貿易合作組織等。然而現有文獻存在對截面數據的使用較多,基于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存在年份久遠的不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利用20個主要的“一帶一路”建設沿線國家2011—2015年的面板數據,引入“一帶一路”實施與否這一虛擬變量,重新構建我國農產品貿易的隨機前沿引力模型,通過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帶一路”的推進對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影響,并給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模型構建
(一)引力模型的基本思想
引力模型最早是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他們通過研究發現,國家間雙邊貿易的流量與國家間的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國家間的距離成反比,類似于經典的萬有引力模型。之后,國外學者對于引力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一是基于不同的視角對引力模型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探尋,對引力模型的理論基礎加以鞏固和完善;二是引入了一系列新的解釋變量對引力模型進行擴展,如人口變量、開放度、邊境等因素。引力模型的對數形式將傳統的貿易引力公式進行線性化,既減少了數據中的異常點現象,又較好地地避免了異方差以及數據殘差的非正態分布等問題。一般而言,貿易引力模型對數化的基本方程為:

在(1)式中,Xij表示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雙邊貿易流量,Yi是國家i的經濟總量,Yj是國家j國的經濟總量,Dij是兩個國家首都之間的地理距離,uij為隨機擾動項,α0、α1、α2、α3為待估的系數。
(二)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的設定
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由Farrell提出,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是基于該方法對傳統貿易引力模型的進一步完善。Broeck和Meeusen(1977)將隨機前沿方法和面板數據結合用來分析生產技術效率問題。Battese和Coelli(1992)改進了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的函數形式,提出了時變隨機前沿模型。由于影響國際貿易問題時,不可觀察且難以量化的主觀因素較多,因此使用簡單的最小二乘估計方法對傳統引力模型進行估算容易使得估計結果的偏誤較大。而貿易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經濟規模、貿易雙方之間的地理距離等多種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的多元函數。Armstrong(2007)研究的結果則證實了用分析生產效率的方法來分析國際貿易流量問題的可行性。與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的形式類似,隨機前沿引力模型可以表示為:

Xijt表示的是國家i與國家j之間的雙邊貿易流量。xij是1×k階向量,表示影響貿易量的自然因素,如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地理距離等因素。β為待估參數向量。隨機前沿分析將傳統殘差項分為隨機誤差項和貿易非效率項,所有不可觀察變量均計入貿易非效率項μ。
(二)我國農產品具體貿易模型的構建
借鑒經典的貿易引力模型來考察經濟規模、空間距離等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總體影響,并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構建如下隨機前沿引力模型:

(2)式中,Xijt代表t年我國和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貿易流量,由我國與相關國家之間農產品的進、出口量加總得到。YitYjt表示t年我國與貿易伙伴國由GDP表征的經濟規模的乘積。貿易距離Dij表示我國首都北京與其他國家首都之間的空間距離。兩國人口總數越大,貿易需求越高,雙方貿易往來越多,因此預估α1符號為正。兩國距離越遠,交通運輸成本越高,不利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因此預估α2符號為負。
考慮人口規模對農產品外貿流量的影響構建引力模型方程(3)。

其中,Pit、Pjt分別表示t年我國和20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口數量。預估農產品貿易流量與貿易國的人口規模成正比,因此預期α3的符號為正。
林德定理認為,兩國收入水平越接近,兩國的需求就越相似,則兩國之間的潛在貿易量就越大。因此從“林德定理”出發,考察需求相似對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將模型(3)進一步擴展為:

其中,Gijt表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均GDP差異。根據林德定理,可預估α4的符號應當為負。
由于研究選取的20個貿易伙伴國均于2011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故不在模型中設置該變量。而考慮到區域性組織APEC對我國農產品外貿產生的影響較大,故有必要對虛擬變量——是否加入APEC貿易合作組織進行設定,在t年,若“一帶一路”沿線貿易伙伴國是APEC組織成員國,則將該變量設置為1,否則設置該變量設置為0。得到引力方程的擴展形式如下:

APEC組織是亞太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組織,組織成員之間通過基于自主協商的非強制性的承諾加強商業合作。APEC致力于推動區域間的貿易自由化,為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提供便利條件以促進合作共贏。從APEC的現實影響來看,APEC為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做出了毋庸置疑的突出貢獻。因此,可以預估APEC對我國的農產品外貿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預估α5的符號為正。
“一帶一路”是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沿革,是在新時代背景下提出的新興戰略。它試圖建立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雙邊乃至多邊的合作機制,致力于構建政治方面和平共處、經濟方面融合發展、文化方面尊重包容的平臺。相比較APEC這一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成果的區域性合作組織,“一帶一路”則是發展尚未成熟的合作組織,它在部署實施的短短幾年內是否能對我國的農產品外貿產生顯著的推進作用還是未可知的,亟須通過實證分析進行探討分析,并基于研究的結論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基于以上分析,基于探討“一帶一路”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往來的影響,加入t年是否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一虛擬變量,得到新的貿易引力方程:

2011年、2012年、2013年 R的取值為 0,2014年、2015年,“一帶一路”正式實施,將R的取值設置為1。基于模型回歸結果中待估參數α6的統計顯著性和符號,可以判斷“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是否已經對我國的農產品外貿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
(三)數據說明
為了實證檢驗“一帶一路”對我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的效應,本文選取我國“一帶一路”沿線的20個主要農產品貿易伙伴國作為樣本進行研究,具體國家選定了日本、美國、韓國、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德國、俄羅斯、荷蘭、英國、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亞、巴西、智利、法國、烏茲別克斯坦及印度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代表。而確定農產品貿易的統計口徑是研究農產品外貿的重要基礎,因此,本文選取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商務部網站公布的關于農產品國際貿易流量的數據。源數據來自中國海關總署,以海關合作理事會制定的《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HS)為基礎編制,采用八位數編碼結構。第1章至第97章的前六位數編碼及商品名稱與《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完全一致。第七、八兩位數編碼是根據我國關稅、統計及貿易管理的需要設置的。各國的人均GDP數據則來自世界銀行world bankdevelopment indicator數據庫,其中人均GDP和GDP總額都是用2005年不變價格進行測算的,排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距離數據則來自Distance Calculator,將其中貿易國首都間的直飛距離作為貿易國間的地理距離。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適用性檢驗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需要先確定隨機前沿引力函數的適當函數形式,才能利用我國農產品外貿的數據對模型中的待估參數進行判斷。本文首先進行貿易非效率檢驗,其次是貿易效率時變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隨機前沿引力模型存在貿易非效率,說明適合運用隨機前沿方法對貿易引力模型進行估計。根據進一步時變性檢驗的結果,函數不存在時變性,因此函數形式確定為時不變隨機前沿引力模型。
(二)模型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同時探求各解釋變量解釋能力大小,先用經濟規模GDP和地理距離D作為初始的解釋變量,利用貿易引力模型的基礎方程(2)進行回歸,然后逐步加入其他解釋變量,最后形成的方程(2)至方程(6)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回歸結果表明,方程(2)至方程(6)的調整后的R2擬合度較高,說明各方程解釋變量的解釋力較強。相應的P值也說明回歸結果高度顯著,拒絕了解釋變量系數為零的假設。從統計的角度來看,模型引入的解釋變量都是能對我國農產品外貿產生顯著影響的因素。
(二)經濟意義檢驗
對擬合結果做進一步的經濟分析。經濟規模GDP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預期一致,表示經濟規模是影響我國與主要農產品貿易伙伴貿易流量的主要因素。隨著未來雙邊國家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農產品的需求也將進一步擴大,農產品貿易量存在較大的增長潛力。兩國間的地理距離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與預期一致,說明距離是阻隔雙邊貿易的因素,空間距離越遠,運輸成本越高,雙邊貿易量越少。一般而言,一國人口的增加提高了該國對海外農產品的貿易往來需求,從而提高了農產品的貿易量。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貿易伙伴國的農產品貿易方程中,人口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與預期一致,較好地證明了上述觀點。方程(2)至方程(6)的回歸系數均在1.5上下,說明人口每增加1%,農產品貿易量增長1.5%。
人均GDP差異的絕對值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與預期一致,說明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符合需求相似論,即兩國人均收入相當時,兩國的需求結構越相似,則兩國的貿易潛力越大。當兩國的人均GDP差異越大,農產品需求差異也越大,兩國的農產品貿易量就越少。虛擬變量APEC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并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系數在方程(6)中為0.86,影響程度反而較“一帶一路”因素高。一方面,區域制度安排往往比全球化的貿易制度安排更能獲得國家間的認可和依賴,從而對國際貿易產生的促進效果更加明顯。另一方面,APEC的實施時間比“一帶一路”更為長久,對我國農產品外貿產生的影響更大。虛擬變量R——“一帶一路”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其系數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一帶一路”雖然在發展的初期,卻對我國與主要沿線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農產品貿易量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促進作用。但從回歸系數的比較分析來看,在t檢驗中,“一帶一路”這一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的P值低于APEC這一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的P值,前者在統計的顯著性方面不如后者。此外,“一帶一路”這一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也小于低APEC這一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說明“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農產品外貿的推動作用還遠不及APEC組織。一方面,“一帶一路”的實施較APEC晚,戰略正屬于布局階段,許多有利于外貿的基建工作和商務洽談工作尚未開展完全,效果還未完全顯現。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帶一路”相較APEC而言還有非常廣闊的發展前景。在未來發展中,“一帶一路”應當汲取APEC成功的經驗,為促進我國農產品的外貿發展和世界貿易的合作共贏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引力模型(2)至模型(6)回歸結果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濟規模依然是促進貿易雙方農產品貿易的主導因素,而距離起到一個非常顯著的負面效應。區域貿易制度APEC的實施對農產品外貿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旨在為中國農業全球戰略提供支撐、服務于農產品對外貿易的“一帶一路”對農產品貿易的促進效應已經開始顯現。初步判斷,“一帶一路”的進一步實施對農產品對外貿易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資源互補。“一帶一路”這一新型國際合作形式充分發揮了我國與沿線國家豐富的農業資源優勢,有利于實現中國與周邊國家農業資源的互補。“一帶一路”不僅有利于解決相關國家糧食安全保障和農民增收問題,還能夠擴大其農產品出口,增加全球供給。同時,也起到了支持有關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科技水平,改善農田水利設施,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作用。
第二,產能合作。“一帶一路”把國內農業食品產業的價值鏈通過投資、合作等方式延伸到境外,形成覆蓋“一帶一路”區域的農業供應鏈,這不僅有利于沿線國家農業食品產業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也對促進國內農業食品產業轉型升級,建立全球價值鏈有利。
第三,市場互惠。在“一帶一路”倡導的區域合作框架下形成的公平、合理、安全、穩定的區域農產品市場體系,能使沿線各國家平等、安全地分享各國經濟發展、農產品市場增長帶來的利益。
第四,發展共贏。實證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對我國與這些相關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流量具有明顯的推進作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農產品種植和食品加工工業方面互補性較強,具有廣闊的互利合作前景。“一帶一路”建設將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農業共同受益、共同發展。
因此,我國各地區和各相關部門要抓住“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機遇期,全面布局境外農業投資,堅決實施“走出去”的戰略,大力促進我國同這些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市場的貿易往來,不斷增加雙方貿易總額,推動對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戰略合作與支持,促進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積極參與和推動改革和完善全球農業治理,構建公平、合理的全球農業新秩序,注重統籌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為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夯實基礎。落實到具體措施上,應當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一帶一路”貿易便利化水平。距離因素是影響中國與沿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因素,基礎設施水平提高將有利于削弱距離限制,促進地區貿易。此外,要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依托,推動建設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借鑒現有區域多邊合作經驗,依托沿線現有各類自貿區,以點帶面,逐步建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通過與沿線各經濟體的貿易便利化合作,連接中國與沿線經濟體,實現貨物、服務、文化的自由流通,從而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
[1]彭廷軍,程國強.中國農產品貿易回顧與展望[J].國際貿易問題,1999,(5):14-19.
[2]何秀榮,Thomas I.Wahl.中國農產品貿易:最近二十年的變化[J].中國農村經濟,2002,(6):9-14+19.
[3]孫林,倪卡卡.東盟貿易便利化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影響及國際比較——基于面板數據模型的實證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13,(4):139-147.
[4]張海森,謝杰.中國—東歐農產品貿易: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8,(10):45-53.
[5]趙雨霖,林光華.中國與東盟10國雙邊農產品貿易流量與貿易潛力的分析——基于貿易引力模型的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8,(12):69-77.
[6]張海森,謝杰.中國—非洲農產品貿易的決定因素與潛力——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1,(3):45-51.
[7]孫林,譚晶榮,宋海英.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對國際農產品出口的影響: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0,(1):74-96.
[8]王瑞,王麗萍.我國農產品貿易流量現狀與影響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2,(4):39-48.
[9] 王穎梅.程國強:“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農業發展[J].農經,2015,(7):74-77.
[10]吳莉婧,謝淑華.“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J].安徽農業科學,2016,(2):266-268.
[11]史朝興,顧海英,秦向東.引力模型在國際貿易中應用的理論基礎研究綜述[J].南開經濟研究,2005,(2):39-44.
[12]程國強.“一帶一路”為全球農業發展帶來新機遇[EB/OL].中國新聞網,201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