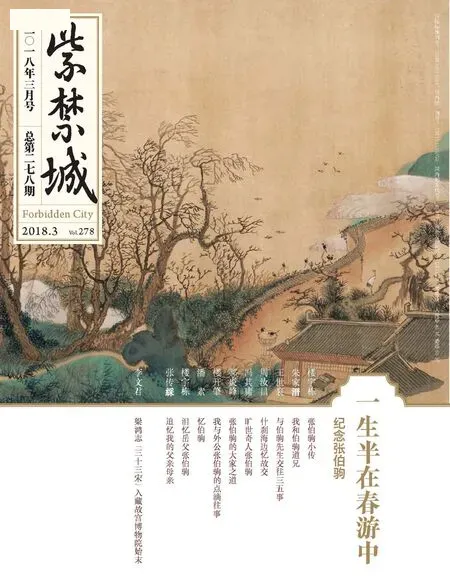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為保存中華文化而藏張伯駒的大家之道
郝炎峰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
張伯駒先生是我國近代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他「曾從戎,務實業,主杏壇,工考古;擅詩詞,長戲曲,能書畫,識棋道」(與張伯駒過從甚密的古文學家張琦翔語),在書畫鑒藏、詩詞、戲曲等不同藝術領域均有深厚造詣,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享有盛名。尤其是在書畫鑒藏方面,張伯駒先生眼光如炬,先后購藏《平復帖》、《游春圖》、《張好好詩》、《雪江歸棹圖》等諸多珍貴文物,避免了國寶流失海外,更被啟功先生譽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建國后,他把耗費了自己畢生心血的書畫珍品捐獻國家,體現了一位文化人的愛國情懷和高尚的品格。

張伯駒先生小像
大家之藏—張伯駒的收藏概況
根據《叢碧書畫錄》統計,張伯駒先生一九六〇年以前共收藏有書畫一百一十七件。其中唐代以前六件,宋代十三件,元代十一件,明代四十件,清代四十七件。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三十件,約占其所有藏品的四分之一。需要說明的是,張伯駒先生的書畫收藏數量當不止于此。首先,《叢碧書畫錄》中張伯駒先生自己提到:「宋元團扇、明清便面,皆屬冊類,對聯則多不錄。余所收便面、對聯是錄亦不另列入。」其次,張伯駒先生捐贈給吉林省博物館(現名吉林省博物院)的部分書畫未包含在《叢碧書畫錄》中(參見閆立群《網取珊瑚 護傳文化— 吉林省博物院藏張伯駒夫婦捐贈書畫》,《中國書畫》二〇〇八年第六期),原因可能在于《叢碧書畫錄》「于庚子歲(一九六〇年)寫畢」,而張伯駒先生是一九六一年到吉林工作的,這些未含在目錄中的書畫可能是張伯駒先生在一九六〇年之后收藏的。
宋元及之前的書畫因「年代湮遠,非經多見廣不易鑒別」。(張伯駒《春游瑣談》「北京清末以后之書畫收藏家」,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故而一定程度上講,收藏宋元書畫的質量和數量成為衡量一個收藏家眼力、實力和地位的重要參考因素。張伯駒先生所藏的三十件晉唐宋元書畫中,即包含了《平復帖》、《游春圖》、《張好好詩》卷、《道服贊》卷、《諸上座帖》、《雪江歸棹圖》等為人們熟知的煌煌巨跡。
章伯鈞先生曾說自己「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張伯駒)的一件」,雖是自謙之語,但從中可看出張伯駒先生收藏之精、之好。如張伯駒先生收藏的《魏倉慈五王經》卷,為敦煌藏經洞流出。曹魏時代距今已一千七百余年,但此件「筆法古拙,墨色如漆……所見敦煌石室藏經,當以此卷為最古」(張伯駒《叢碧書畫錄》)。

啟功先生為《叢碧堂張氏鑒藏捐獻法書名畫冊》所題詩
陸機《平復帖》是現存年代最早并真實可信的西晉名家法帖,有「法帖之祖」的美譽。它是漢字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重要佐證,也是歷史上第一件流傳有緒的法帖墨跡,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晉 陸機 平復帖卷紙本草書縱二三·八厘米 橫二〇·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閱讀鏈接
啟功說《平復帖》—
◎ 唐宋以來,講草、真、行書書法的,都上溯到晉人。而晉代名家的真跡,至唐代所存已逐漸稀少,流傳的已雜有摹本。宋代書法鑒賞大家米芾曾說:“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而他所見的真跡,只是李瑋家所收十四帖中的張華、王浚、王戎、陸機和臣詹奏章晉武帝批答等幾帖(見《書史》卷上。《寶章待訪錄》所記較略,此從《史書》)。其中陸機一帖,即是這件《平復帖》。宣和時,十四帖已經拆散不全。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子集引《宣和書譜》說:“陸機《平復帖》,作于晉帝初年,前王右軍《蘭亭宴集敘》大約百有余歲。今世張、鐘書法,都非兩賢真跡,則此帖當屬最古也(今本《宣和書譜》無此條,如非版本不同,即是張丑誤記)。”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二十跋《米元章臨晉武帝大水帖》說:“西晉字,在今豈可復得!”明董其昌跋說:“右軍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其實明代所存,不但鐘帖已無真跡,即二王帖,亦全剩了唐摹本了。按先秦和漢代的簡牘墨跡,宋以前雖也偶有出土的,但數量不多,不久又全毀壞,可以說,在近代漢晉和戰國的簡牘大量出土以前,數百年的時間,人們所能見到最古的,并非摹本墨跡,只有這九行字,而在今日統觀所有西晉以上的墨跡,其中確知出于名家之手的,也只有這九行。若以今存古代名家法書論,這帖還是年代最早的一件,以今存西晉名家法書論,這帖又是最真實可靠的一件。
—節選自啟功《〈平復帖〉說并釋文》,原載《啟功叢稿》,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游春圖》卷,歷來被認為是隋代畫家展子虔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中國早期山水畫的面貌,開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雖然有學者對這幅作品的作者和時代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它在中國山水畫史上的地位仍舊不可替代。
閱讀鏈接
王世襄談展子虔《游春圖》的流傳—
◎ ……有兩點值得提出談一談。其一是阮元著的《石渠隨筆》及他參加編纂的《石渠寶笈續編》都說《游春圖》就是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所著錄的展子虔《長安車馬人物圖》。這一說是不可信的。因為畫中有馬無車,且景物全是江南,絕無長安景象。同時張丑《清河書畫舫》中明明兩件一并著錄,并稱《長安車馬人物圖》在《游春圖》上。另一點是此卷雖經趙佶題簽,但《宣和畫譜》所著系展子虔的二十件作品中卻無《游春圖》之名。這是什么緣故呢?一個可能是此卷進入宋內府已在《宣和畫譜》成書之后,所以不及收入。但引人注意的是二十件之中有一幅名《挾彈游騎圖》。安岐在《墨緣匯觀》敘述此畫時,特地講到“游騎有四,內一挾彈者”。他雖未提到此圖可能就是《宣和畫譜》所著錄的《挾彈游騎圖》,但他在兩句之中嵌用了“挾彈游騎”四字,分明是意有所指的。按理說,《宣和畫譜》所著錄的畫名應該與趙佶的題簽相合。但畫原有名,而趙佶在題簽時另為更易,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就畫論題,“挾彈游騎”與此卷的景物是吻合的,但《游春圖》三字似乎更能概括整個畫卷的情景和氣氛。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而趙佶為它改換了名稱呢?當然,現在很難找到更多的證據來證實上面的臆測,而這里只當作一個線索提出來供大家參考而已。
——節選自王世襄《談展子虔〈游春圖〉》,原載《故宮博物院藏寶錄》,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上海文藝出版社聯合出版,一九八五年第一版

隋 展子虔 游春圖卷絹本設色縱四三厘米 橫八〇·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上陽臺帖》卷,是「詩仙」李白傳世的唯一書跡,落筆天縱,意義非凡。
《張好好詩》卷,是唐代著名詩人、書法家杜牧的僅存墨跡,也是稀見的唐代名人書法作品之一。
《道服贊》卷。此卷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為同年友人「平海書記許兄」所制道服撰寫的一篇贊文,「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也是這位歷史名人為數不多的傳世佳作。
閱讀鏈接
啟功談李白《上陽臺帖》—
◎ 怎知道它(《上陽臺帖》)是李白的真跡呢?首先是據宋徽宗的鑒定。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時間,以宣和末年(一一二五年)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僅僅三百六十多年,這和我們今天鑒定晚明人的筆跡一樣,是并不困難的。這卷上的瘦金書標題、跋尾既和宋徽宗其他真跡相符,則他所鑒定的內容,自然是可信賴的。至于南宋以來的收藏者、題跋者,也多是鑒賞大家,他們的鑒定,也多是精確的。其次是從筆跡的時代風格上看,這帖和張旭的《肚痛帖》、顏真卿的《劉中使帖》(又名《瀛州帖》)都極相近。當然每一家還有自己的個人風格,但是同一段時間的風格,常有其共同之點,可以互相印證。再次,這帖上有“太白”款字,而字跡筆劃又的確不是鉤摹的。
◎ 另外有兩個問題,即是卷內雖然有宋徽宗的題字,但不見于《宣和書譜》(璽印又不可見);且瘦金跋中只說到《乘興帖》,沒有說《上陽臺帖》;都不免容易引起人的懷疑,這可以從其他宣和舊藏法書來說明。現在所見的宣和舊藏法書,多是帖前有宋徽宗題簽,簽下押雙龍圓璽;帖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鈐“政和”、“宣和”小璽,后隔水與拖尾接縫處鈐以“政和”小璽,尾紙上鈐以“內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印,這是一般的格式。但如王羲之《奉橘帖》即題在前綾隔水,鈐印亦不拘此式。鐘繇《薦季直表》雖有“宣和”小璽,但不見于《宣和書譜》,王獻之《送梨帖》附柳公權跋,米芾《書史》記載,認為是王獻之的字,而《宣和書譜》卻收在王羲之名下,今見墨跡卷中并無政、宣璽印。可知例外仍是很多的。宣和藏品,在靖康之亂以后,流散出來,多被割去璽印,以泯滅官府舊物的證據,這在前代人記載中提到的非常之多。也有貴戚藏品,曾經皇帝鑒賞,但未收入宮廷的。還有其他種種的可能,現在不必一一揣測。而且今本《宣和書譜》是否有由于傳寫的脫訛?其與原本有多少差異?也都無從得知。總之,帖字是唐代中期風格,上有“太白”款,字跡不是鉤摹,瘦金鑒題可信。在這四項條件之下,所以我們敢于斷定它是李白的真跡。
◎ 至于瘦金跋中牽涉到《乘興帖》的問題,這并不能說是文不對題,因為前邊標題已經明言《上陽臺》了,后跋不過是借《乘興帖》的話來描寫詩人的形象,兼論他的書風罷了。《乘興帖》的詞句,恐怕是宋徽宗所特別欣賞的,所以《宣和書譜》卷九李白的小傳里,在敘述詩人的種種事跡之后,還特別提出他“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字畫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這段話正與現在這《上陽臺帖》后的跋語相合,可見是把《乘興帖》中的話當作詩人的生活史料看的。并且可見纂錄《宣和書譜》時是曾根據這段“御書”的。再看跋語首先說“嘗作書譜”云云,分明是引證另外一帖的口氣,不能因跋中提到《乘興帖》即疑它是從《乘興帖》后移來的。
◎ ……或問這卷既曾藏《石渠寶笈》中,何以《三希堂帖》、《墨妙軒帖》俱不曾摹刻呢?這只要看看帖字的磨損剝落的情形,便能了然。在近代影印技術沒有發明以前,僅憑鉤摹刻石,遇到紙敝墨渝的字跡,便無法表現了。現在影印精工,幾乎不隔一塵,我們捧讀起來,真足共慶眼福!
—節選自啟功《李白〈上陽臺帖〉墨跡》,原載《啟功叢稿》,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唐 李白 上陽臺帖卷紙本草書縱二八·五厘米 橫三八·一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宋 范仲淹 道服贊卷紙本楷書帖心縱三四·八厘米 橫四七·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閱讀鏈接
朱家溍與蔡襄《自書詩》卷的故事—
◎ ……蔡襄此帖就是當年“品古齋”鄭掌柜送到我(朱家溍)家的,先父看過后以五千銀元成交。《選學齋書畫寓目續記》的作者崇巽庵先生與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實際就是在我家。當時先父叮囑他不要外傳,所以他在書中稱此帖“近復流落燕市,未卜伊誰唱得寶之歌”。先父在此帖跋語中有“壬申春偶因橐鑰不謹竟致失去,窮索累日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之說,是指一九三二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吳榮竊去后又復得之事。吳榮竊得此帖,便拿到一個與我家沒有交往的古玩鋪“賞奇齋”求售。掌柜的一看便知道是從我家竊得的東西,遂表示只肯以六百元買下,否則就報告公安局,吳榮只好答應。“賞奇齋”掌柜把上述情況告訴了“德寶齋”掌柜劉廉泉和“文祿堂”掌柜王搢青,并請他們通知我家。劉王二位與先父商議,認為最佳辦法是不要追究吳榮,而盡快出錢從“賞奇齋”把此帖贖回來。先父一一照辦。此事如無“賞奇齋”與劉王兩位幫忙后果就不堪設想了。所以除償還“賞奇齋”六百元墊款外,我家又贈掌柜的一千元作為酬勞。此帖拿回后先父就決定影印出版。當時他是故宮博物院負責鑒定書畫碑帖的專門委員,于是就委托故宮印刷所影印,命我把此帖送到東連房(印刷所的工作室),由經理兼技師楊心德用十二寸的玻璃底版按原大拍照,張德恒(現在臺北故宮)沖洗。這是此帖第一次影印發行。那時距今已整六十年了。
◎ 先父逝世后,抗戰期間我離家到重慶工作。家中因辦理祖母喪事亟需用錢,傅沅叔世丈代將此帖作價三萬五千元,由“惠古齋”柳春農經手讓與張伯駒。此帖在我家收藏了二十余載;在張家十數載,隨陸機《平復帖》等名跡一起捐獻給國家。自此以后,蔡襄此帖便入藏故宮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寶笈三編》著錄此帖以后的收傳情況。
—節選自朱家溍《從舊藏蔡襄〈自書詩〉卷談起》, 原載《書法叢刊》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閱讀鏈接
張伯駒對蔡襄《自書詩》改成手卷的看法—
◎ 那天在酒席筵前,從“平復帖”、“游春圖”談到“蔡襄自書詩冊”,這都是一同捐入故宮博物院的。伯駒說:“聽說《蔡襄自書詩冊》到故宮博物院以后,又重新揭裱,改成手卷了,是有這回事么?”我說:“是揭裱改成手卷了。”伯駒說:“是你出的餿主意?”我說:“當然不是!事先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堅決反對了。”伯駒說:“蔡襄自書詩冊,完完整整毫無殘破的情況,為什么要揭裱呢?簡直是大膽妄為。當然在宋代曾經是卷,不過裱成冊已經又幾百年了,有什么必要又重裱。”我也了解伯駒的心情,他完全能料到我決不是出主意揭裱的人,不過因為我家曾經是《蔡襄自書詩冊》的收藏者,所以要在我面前共同發泄一下,這是可以理解的。
—節選自朱家溍《幾凈閑臨寶晉帖 窗明靜展游春圖》,原載《收藏家》一九九八年第一期
《自書詩》卷,作者為「宋四家」之一的蔡襄,他的書法在宋代已享有很高的聲譽,被推為本朝第一。此件筆致飄逸,點畫精美,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圓潤的書風特色與純熟的功力,「為蔡書之最精者」。

宋 蔡襄 自書詩卷紙本行書縱二八·二厘米 橫二二一·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諸上座帖》是「宋四家」之一黃庭堅草書的代表作,「自明以來已譽為黃書第一」(《叢碧書畫錄》),字法奇宕,如馬脫韁,無所拘束,顯示出書者懸腕攝鋒運筆的高超書藝。
《雪江歸棹圖》卷是宋徽宗趙佶所作的一幅山水畫,張伯駒先生贊其「布置精密,筆意超絕」,代表了徽宗時期畫院的藝術水平。
《百花圖》卷多認為是南宋女畫家楊婕妤所畫,《石渠寶笈初編》中評為「列朝人畫卷上等」,是目前已知現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畫家的作品,張伯駒先生甚至認為「唐宋以來女子畫此卷為孤本」。

《孟蜀宮妓圖》軸(現稱《王蜀宮妓圖軸》)是「吳門四家」之一的唐寅所畫,工筆重彩,細致入微地描摹了宮妓四人,顯示出唐伯虎在造型、用筆、設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藝。
除此之外,張伯駒先生還收藏了多位藝術史上著名書法家、畫家和重要流派的作品,其精品之多、質量之高,使他成為二十世紀有定評的六大收藏家之一。

宋 趙佶 雪江歸棹圖卷絹本淡設色縱三〇·三厘米 橫一九〇·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大家之途—成為大家的幾個因素
要成為書畫鑒藏大家,一般來說,必須具備幾個主客觀因素:自身的興趣和愛好、淵博的知識及辨偽識真的眼光、必要的經濟基礎、購藏的魄力等。如果有歷史創造的機遇,那就更是鑒藏家之福了。
清代康熙、雍正直至乾隆時期,清王朝走向興盛并發展到頂峰,乾隆皇帝對書畫藝術十分重視,民間的書畫精品持續向內府集中,使得內府收藏的書畫達到了驚人的數量,可謂中國歷史上書畫的一次最大規模的匯集。乾隆皇帝自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十二月起,開始了編纂著錄內府書畫的工作,陸續纂輯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續編和三編,著錄書畫一萬余件。這對于古代書畫的保護和傳承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后,隨著清政府控制力的衰退,內府書畫收藏遭到了劫掠: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將圓明園所藏書畫洗劫一空;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皇家苑囿甚至紫禁城內的書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盜;清帝遜位后,溥儀又將一千兩百余件書畫精品盜運出宮,偽滿覆滅后在東北散佚。這些都造成了中國古代書畫精品的外流和損毀,令人痛心。但另一方面,長期貯藏宮廷內府的書畫精品的外流,恰恰給民間收藏家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接觸古代書畫的契機。這是張伯駒先生開始收藏生涯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張伯駒先生生于書香門第。其曾祖父張致遠飽讀詩書,藏書有萬卷之多。祖父張瑞楨為光緒甲午科舉人。生父張錦芳乃清末廩生,曾任度支部郎中,一九一三年任眾議院議員、道尹等職,能詩善文,有詩集《修竹齋引玉詠》行世。張伯駒六歲時,因伯父張鎮芳兩子女早殤,故將其過繼為子。張鎮芳二十一歲中廩生,次年以鄉試第一中舉,二十九歲中進士,也是飽學之士。張伯駒在嗣父的安排下入塾讀書。在名師的指導下,張伯駒受到了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一九一一年后,張伯駒離開項城私塾,到天津「新學書院」讀書,負責他學業的,是有「南開校父」之稱的嚴范孫。這些都對他成年之后的興趣和志向有著深刻的影響。

宋 吳琚 雜詩帖卷紙本行書、草書故宮博物院藏
成年后,張伯駒先生雖在父親的安排下進入軍界,但他目睹內戰頻仍,政壇更換,官場腐敗,非自己志向所在,便毅然從中脫身。一九二七年,三十歲的張伯駒先生偶然在琉璃廠購得康熙御筆「叢碧山房」匾額一塊,「為予收蓄書畫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為號」(《叢碧書畫錄》),并且把自己的宅院命名為「叢碧山房」,可見對這塊匾和書畫文物的喜愛。從此,兒時埋在心底的種子生根發芽,一發而不可收,書畫鑒藏成為他一輩子的心之所屬。他曾自云:「三十以后,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觀。」當他終將《張好好詩》卷收藏后,「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數日,始藏貯篋中」(《春游瑣談》),并改字號為「好好先生」。而此時,他已經五十三歲,仍保持著對書畫鑒藏的初心和熱愛。
張伯駒先生在收藏過程中,鑒、藏相長,收藏促進了眼力的提高,而眼力的提高又使他明辨更多珍品,藏以促鑒,鑒以明藏,形成了良性循環。張伯駒先生青年時期累積的傳統文化知識和素養,為他在辨別古書畫方面的快速成長提供了基礎。他曾見過唐寅《行書詩》卷,說此卷至精,但有人以其中「揚州」寫為「楊州」而斷為偽作。張伯駒認為:「揚者為楊,抑者為柳,揚楊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誤寫。他進而評論道:「未學小學而論字,誤以斷名跡真偽,豈不甚謬。」(《叢碧書畫錄·元顏輝煮茶圖卷》)由此可見其訓詁造詣之一斑。我們還可以從對《游春圖》的考證一窺他對古書畫的鑒定方法:「是卷自宣和以迄南宋元明清,流傳有緒。證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畫山水,與是卷畫法相同,只以卷絹與墻壁用筆傅色有粗細之分。《墨緣匯觀》亦謂山巒樹石空勾無皴始開唐法。今以卷內人物畫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斷為隋畫無疑。按中國山水畫,自東晉過江中原,士夫見江山之美,抒寫其情緒而作。又見佛像畫背景自以青綠為始,一為梁張僧繇沒骨法傳自印度。是卷則上承晉顧愷之,下啟唐大李將軍,為中國本來之青綠山水畫法也。」(《叢碧書畫錄》)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對「流傳有緒」非常看重,認為文字和文獻的著錄是前人眼光和經驗的總結;另一方面,對于古書畫的判定,他會從筆法、材質、皴法、內容等多方面考證,同時參以壁畫、陶俑等其他藝術門類,而不是單單依靠一個具體的方面。實踐證明,他的這套方法和眼力十分有效,也使他收藏了不少極其珍稀的法書名畫。

元 趙孟頫 千字文帖卷紙本草書縱二四·一厘米 橫二四〇·六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宋 趙構書、馬和之繪 詩經節南山之什圖卷絹本設色縱二六·二厘米 橫八五七·六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宋 朱勝非 杜門帖紙本縱二八·七厘米 橫二八·六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收藏書畫,尤其是古代書畫珍品,必須要有雄厚的資金。張伯駒先生自軍界抽身后,子承父業,任鹽業銀行常務董事,加上父親留的雄厚遺產,為其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他的第一件藏品「叢碧山房」匾額花費一千塊大洋,《平復帖》四萬元(銀元,下同),《游春圖》二百二十兩黃金{關于《游春圖》的購入價格,有不同說法。張伯駒在《春游瑣談》中自述為「以黃金二百二十兩定價」,而當時的賣方代表李卓卿則說:「經六家共同商議,由穆蟠(磻)忱拍板定價,以二百兩黃金的代價賣給張伯駒」(陳重遠《古玩談舊聞》,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中間人馬寶山則說:「經他(李卓卿)與馬濟(霽)川等反復商談,最后以二百兩黃金之價議妥。」(馬寶山《書畫碑帖見聞錄》,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七年)},杜牧《張好好詩》以「五千數百金收之」,蔡襄《自書詩》四萬五千元,李白《上陽臺帖》、唐寅《孟蜀宮妓圖》、王時敏山水、蔣廷錫《瑞蔬圖》共六萬元,米友仁《姚山秋霽圖》一萬元,《摹懷素書》五千元。而這些只是他平生所收藏書畫的一部分而已。
收藏書畫花費巨大,當珍稀名品與現實困難同時擺在面前,就到了考驗鑒藏家眼光和魄力的時候了。張伯駒先生雖然家境殷實,但后期仍不免捉襟見肘。他收藏《游春圖》時,古董商要價黃金二百二十兩,當時張伯駒「屢收宋元巨跡,手頭拮據」,如無奈放棄,則會與此「存世最古之畫跡」失之交臂,遺憾終生,甚至此畫極有可能「流出國外」,這是張伯駒先生不能忍受的。「因售出所居房產付款,將卷收歸」。(《春游瑣談·隋展子虔游春圖》)所售出的房產位于弓弦胡同,是其長居之所,占地十五畝,原為李蓮英的宅子。楊仁愷認為張伯駒「背水一戰,將他在北平的房產變賣,以了結平生的心愿,此事非大智大勇者決不能下此決心」。
大家之品—鑒藏理念與民族大義
張伯駒先生的書畫鑒藏始于愛好。他在《叢碧書畫錄·序》中說,「三十以后嗜書畫成癖」。這對于一個從小受傳統文化教育熏陶成長起來的富家子弟來說,是再正常不過了。在收到喜愛的書畫后,「每于明窗凈幾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間,應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內,陶熔氣質,洗滌心胸,是煙云已與我相合矣」。因喜愛而收藏,因收藏得以與古人神交,體會天地濃縮于咫尺、人物浮現于晷刻的樂趣,文物以形象化的視覺體驗令收藏者對詩詞、書法、繪畫、印章等藝術門類融會貫通,進而胸中滌蕩,心曠神怡。古往今來,這種精神層面的愉悅令多少鑒藏家醉心于此,樂此不疲。這不可不說是古書畫的魅力,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所在。
如果僅限于此,張伯駒先生與歷史上多數鑒藏家別無二致,也不會得到后世那么高的評價。其品格和貢獻,主要在于他將個人收藏提升到了民族大義的高度。近代中國,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反帝反封建、維護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成為有識之士的奮斗目標。對于文化藝術界人士來說,守護中華瑰寶、延續中華文脈就是他們的崇高使命。
張伯駒先生的鄉土觀念很重。他生于河南項城縣秣陵鎮閻樓村,雖少年即已離家,但一生鄉音未改,而且他的詩文書畫落款,一直沿用「中州張伯駒」。他還請陳半丁為其制印,文曰「重瞳鄉人」,蓋取舜和項羽皆重瞳子,而「兩重瞳皆與吾邑有關……此印余不輕用,只于題畫作詩時偶用之」 。(《春游瑣談·重瞳鄉人印》)
從鄉土觀念生發出來的民族大義,結合近代以來的國家觀念,使得張伯駒產生了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愛國熱情。他看重古書畫的「世傳有緒」— 國寶流出國外,失去了中華大地的根基,就喪失了「世傳有緒」的意義。自一九四八年十月起,他在《新民晚報》副刊《造型》上連載《故宮散佚書畫見聞錄》,最后一篇「結論」中寫道:「則書畫之保存研究,似非小道,或謂為玩物喪志,或謂為作煙云過眼觀,是皆懦夫市儈之語,謬哉!」針對當時很多文物外流,他痛心疾首,曾評價說:「約在民國十五至十七年間,日本在東京舉行《中國唐宋元明清書畫展覽會》,宋元書畫價值遂重,而流出者亦漸多。綜清末民初鑒藏家,其時其境,與項子京、高士奇、安儀周、梁清標不同。彼則楚弓楚得,此則更有外邦之剽奪。亦有因而流出者,亦有得以保存者,則此時之書畫鑒藏家,功罪各半矣。」(《春游瑣談·北京清末以后之書畫收藏家》)他認為,古書畫在國內藏家間流動,「楚弓楚得」是正常的,但流出國外就是罪過了。談到五代阮郜《閬苑女仙圖》卷未像「梁楷卷」一樣在溥儀的授意下被陳寶琛經手賣到日本,張伯駒先生感慨地說,此圖「未于劉(可超)手流出國外,誠為幸事」。據章詒和記載,張伯駒曾對章伯鈞說:「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

元 錢選 山居圖卷紙本設色縱二六·五厘米 橫一一一·六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為保珍貴的古書畫不致外流,張伯駒先生在購入之后,極少再次轉手。他花四萬元購入《平復帖》后,「時白堅甫聞之,亦欲得此帖轉售日人,則二十萬價殊為易事。而帖已到余手」。他在售房購入《游春圖》后,「南京政府張群來京,即詢此卷,四五百兩黃金不計也。而卷已歸余有」。言語之間,頗顯堅定與自豪。相比于《游春圖》「永存吾土,世傳有緒」,他雖售房收蓄,還有人「訾笑」,但他不為所動,「不悔」。他認
為,《游春圖》猶如「魯殿僅存之國珍」,他不果斷購藏,其定「已不在國內矣」。從《平復帖》和《游春圖》的購藏過程來看,張伯駒先生在當時購藏珍貴書畫的出發點,是出于文物自身流傳有緒的考量。同時,他認為由故宮博物院收歸是這些書畫最好的歸宿。他曾諫言故宮博物院:「一、所有賞溥杰單內者,不論真贗,統由故宮博物院價購收回;二、選精品,經過審查價購收回。」中年之后,先生「屢收宋元巨跡,手頭拮據」,但為避免文物「流出國外」,即使「鬻物舉債」甚至變賣房產也要收購一些珍貴的文物,其他人出高價也不賣出,說明其收藏不以牟利為目的。日軍侵華,北京淪陷,先生「攜眷入秦。帖藏衣被中,雖經亂離跋涉,未嘗去身」。言語之間,透露出一位視國寶為生命的大收藏家的至高品格,體現出張伯駒先生對于書畫珍品和民族文化的強烈認同感,這些行為都是在他民族主義的觀念下進行的,是他收藏書畫的重要動機。



元 王冕、張觀、趙雍、朱德潤、方從義 元五家合繪圖卷紙本墨筆故宮博物院藏


此手卷畫蘭、菊、竹三段,各有文氏親筆題詠。用筆寫意,簡率之中見生動秀逸之致,墨色清潤淡雅,顯示了詩、書、畫結合的筆墨境界。中國傳統文化以擬人化的手法,通過褒揚蘭、菊、竹的自然屬性而歌頌或表彰文人的道德品質,體現了中國花卉畫的特殊功能。

大家之格—煙云過眼與化私為公
早在壬申年(一九三二年),張伯駒先生撰寫《叢碧書畫錄·序》時,已談到了他鑒藏古書畫的「煙云過眼」觀。「煙云過眼」源自蘇軾為宋英宗駙馬王詵作的《寶繪堂記》,其文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云之過眼……于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但張伯駒先生較此則更進一步,以民族、國家大義為落腳點,少了一些不舍,多了一些豪放曠達,與蘇軾「煙云過眼」注重自我修養的內涵大有區別。


清 吳歷 興福庵感舊圖卷絹本設色縱三六·七厘米 橫八五·七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中國歷史上的書畫收藏家不少,如項元汴、高士奇、安岐、梁清標等,但其藏品能夠「子孫永保」者甚為罕見。張伯駒先生對清末民初的幾位北京書畫收藏家更為熟悉,如完顏景賢「精鑒賞,所見甚廣」,著《三虞堂書畫目》,共錄有百四十六件,「多系珍品名跡」。但「景氏故后,遺物散失殆盡」,或流于日本,或流于國內收藏家之手。著名鑒藏家楊蔭北收藏頗豐,但「晚年窘困,全部陸續讓出」。另一鑒藏家關伯珩在收藏書畫方面亦頗具魄力,但關氏故后,所藏亦陸續讓出。
張伯駒先生對此感慨良多,自言曰:「自鼎革以還,內府散失,輾轉多入外邦,自寶其寶,猶不及麝臍翟尾,良可慨已。予之煙云過眼,所獲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是則予為是錄之所愿也。」這就是先生收藏的最大動力,也是他花費巨資,甚至變賣房產也在所不惜的魄力之源。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為保存中華文化而藏,張伯駒身上體現的崇高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情操值得我們永遠學習。
在收藏了大量書畫珍品,尤其是在經歷了上海被人綁架勒索和攜帶珍品跋涉入陜之后,藏品雖萬幸未受損失,但也讓張伯駒先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促使他更緊迫地思考自己藏品的歸宿問題。

清 樊圻 柳村漁樂圖卷絹本設色全卷縱二八·六厘米 橫一六七·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清 禹之鼎 納蘭性德小像軸紙本設色 縱五九·五厘米 橫三六·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新中國建立后,張伯駒先生在致周恩來總理的信中說:「在國民黨時期,曾對家人潘素立有遺囑,謂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愛戴,政府修明之政府,應不以自私,捐歸公有。」一九五六年,張伯駒、潘素夫婦將所藏的八件頂級法書珍品捐獻國家,時任文化部部長的沈雁冰專門為其頒發了褒獎狀。曾經「煙云過眼」的藏品得到了最好的歸宿,也達到了張伯駒「永存吾土,世傳有緒」的愿望,他也終于可以釋然:「此則終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這八件法書后來由國家文物局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張伯駒贈送毛澤東主席的李白《上陽臺帖》后來也轉贈故宮博物院。如今,故宮博物院藏有張伯駒鑒藏的書畫共二十一件,他還捐贈給吉林省博物院數十件書畫(參見閆立群《一段機緣留下珍寶無數— 吉林省博物院藏張伯駒、潘素夫婦捐獻書畫作品》,《榮寶齋》二〇一一年第九期),這些歷代書畫精品均已成為國家的重要財產,保留著中華文脈,延續著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附:張伯駒捐獻古書畫文物精選一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