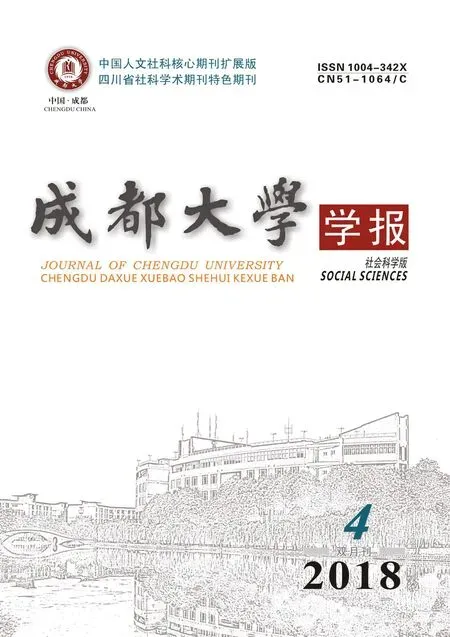解讀《卑劣的靈魂》中的環境種族主義
李潤潤 李 偉
(安徽科技學院 外國語學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在美國當代印第安人作家中,美國本土裔女作家琳達·霍根頗有建樹,她的作品大多圍繞美國本土族裔奇卡索部落的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和風土人情而展開。除了作家的身份,霍根還是一個十足的環保主義者。通過她的作品,作家呼吁更多的人去關注我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與其他印第安作家相比,霍根不論是在詩歌、小說還是在散文創作中都更加集中關注一個凸顯的主題——環境,以美國印第安居民所特有的傳統文化視角對于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環境變遷進行鞭撻,對于印第安居民在此過程中的慘痛經歷進行回顧,在對歷史的再闡釋和對殖民暴力的控訴中強調其社會和政治的訴求。
霍根在1990年推出的小說《卑劣的靈魂》一經出版就受到極大的關注。《洛杉磯時報》發表的書評認為這部作品堪稱“北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就如同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智利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Isabel Allende)用魔法師的目光考慮他們的政治史,琳達·霍根則通過奇事和魔幻審視某些血腥的美國真相”。
目前國內對琳達·霍根的作品研究比較有限,對于《卑劣的靈魂》這部作品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數。路潔和鄒惠玲從文學倫理學的角度將霍根的兩部作品《北極光》和《卑劣的靈魂》結合起來從而“再現了白人統治與壓榨下印第安人水深火熱的處境和白人與印第安人水火不相容的倫理選擇”[1]。唐建南和劉凱菁從后殖民生態的角度“揭露西方霸權主義者的卑劣靈魂”[2]。在此研究基礎之上,本文將從環境種族主義的視角解讀《卑劣的靈魂》,將印第安人面臨的各種環境問題與種族主義聯系起來。由于美國白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對石油進行肆意開采以及對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從而給印第安人帶來了環境和精神上的雙重危機。在這場面對環境非正義行為的運動中,印第安人不僅依靠自己的綿薄之力奮起應戰,還盡力將自己的生態思想傳遞給白人,借此希望美國白人能夠反思一下自身的環境種族主義行為。
一、《卑劣的靈魂》中的環境種族主義行為
霍根從小就目睹了身邊的印第安人因為身份差異而不得不面對的社會變遷與動蕩。她從小成長的印第安人世界俄克拉荷馬與印白混居的丹佛市為她提供了一個既單純又復雜的文化大背景,一方面她可以去體會淳樸的印第安人靈學思想傳統,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適應不斷變更的混雜的社會洪流的影響。這些關于種族問題的矛盾和沖突在《卑劣的靈魂》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該小說以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歷史事實為原型,以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突然被發掘的石油而引發的一系列兇殺案為主要故事背景。琳達·霍根在文學作品中將故事發生的地點移至俄克拉荷馬州(Oklahoma)一個名叫瓦托納(Watona)的印第安小鎮。小鎮上印第安居民的生活因為突然被發現的豐富的石油資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么這些石油資源對印第安人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突然發現的石油資源讓小鎮上的居民接二連三地死亡或失蹤。小鎮居民格雷斯·布蘭科特(Grace Blanket) 根據道斯法案獲得了160英畝干旱的砂石地。這些土地一開始因為貧瘠被稱為“不毛之地”(The Barren Land)。后來在這片被人拋棄的土地上卻因為意外發現了石油而變成一塊“貴族之地”(The Baron Land)。然而不幸的是,因為土地下豐富的石油資源而一夜暴富的格雷斯卻被殘忍地殺害了。“然后在光天化日下,一聲槍響打破了空氣的沉寂……那兩個男人把格雷斯的尸體放在他們中間,好像她只是一個星期日外出的女朋友。”[3]14不僅如此,死亡的陰影還蔓延至她的女兒、妹妹、妹夫等所有可能獲得土地繼承權的親人們。事實上,圍繞這筆巨大的石油財富,已先后有近20人莫名地死亡或失蹤。可以說,對于印第安人而言,巨大的石油財富并沒有為族人帶來幸福的生活,而是一切災難的開始。
其次,除了籠罩在小鎮上的死亡陰影之外,鎮上印第安居民的生態環境也遭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自從美國白人在瓦托納小鎮上開采石油之后,曾經生機勃勃的土地變得滿目瘡痍。印第安人每天不得不面對和忍受小鎮周圍土地上因為石油開采而被挖掘的一個個黑洞。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美麗家園一夜之間變得面目全非,他們棲息的土地變得傷痕累累,曾經茂密的森林變成了一片焦黑的荒山禿嶺,野生動物也在逐漸瀕臨滅絕。在小說中,霍根用生動的筆觸描述了白人對待地球母親的殘忍方式,他們貪婪地想要榨取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滴石油。“一陣爆炸聲把他們震得站起來了,使他們完全清醒了。它搖晃著大地,好像它被分開了。”[3]75
二、“環境種族主義"行為背后的原因
“20世紀以來,維護環境正義活動中,人們越發注意到一個事實:在不同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少數族裔社區以及社會弱勢人群,正在不公正地成為有毒垃圾、空氣污染、水污染、各種軍事武器試驗所導致的環境災難的受害者。”美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會在1987年公布的一份報告上將上述環境種族歧視現象命名為“環境種族主義”。
在《卑劣的靈魂》這部作品中,為什么以格雷斯為代表的少數族裔人群沒有享受到財富帶來的福祉,反而成為財富的受害者?為什么石油資源給他們帶來的只有數不清的磨難和死亡呢?為什么受傷害的一直都是印第安人?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印第安人正在不公正地淪為白人發展經濟所導致的環境災難的最大受害者。作為一部圍繞石油而展開殺戮史實為背景的故事,作品中的白人出于貪婪瘋狂掠奪和占有印第安人土地下的石油資源。地底下被發現的豐富石油資源讓白人在巨大的財富面前利益熏心、草菅人命。讓人感到更憤怒的是,這兇殘的明目張膽的罪行卻無法在聯邦法律的框架中得以申訴和懲處。上述種族歧視現象就是典型的“環境種族正義”。美國政府一直以來所宣揚的公正與民主,在印第安人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面前,根本就是一個幌子。霍根通過文學之筆真實地再現了這段暴力的罪惡歷史。她指責美國白人的環境種族非正義行為造成的不公使當地的環境日益惡化,使印第安人的幸福生活遭到了嚴重的威脅。通過對印第安人所面臨的精神困境和生態災難的描寫,霍根有力地控訴了白人社會的環境種族非正義行為。
霍根不僅僅是在為她的同胞所遭受的殘害討回公道,更是為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而戰。一開始,美國白人為了發展自身的經濟將印第安人強行遷移至被白人嫌棄的貧瘠的土地上生活。然而當這片土地上發現了石油之后,印第安人又一次遭受了迫害。不僅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印第安人再次遭到擠壓、驅逐甚至失去生命,甚至連這片土地也成為被無情掠奪的最大受害者。借用小說中印第安人牧師喬·比利(Joe Billy)的話,這不僅僅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更是一場人與自然之間的戰爭。“他們在向大地挑戰,他們燒毀了我們的森林和玉米地……”[3]14
三、如何面對環境種族主義行為
霍根在小說中講述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圍繞石油資源而展開斗爭的故事。“印第安人的世界正在與白人的世界相互撞擊”[3]13。小鎮上的每一個印第安人在這個相互撞擊的過程中都遭遇了物質和精神上的不公。當財富從貧窮的印第安人的家園轉移到相對富裕的白人手中時,正義遭受到了損害。那么在這場對抗白人貪欲的斗爭中,印第安人該如何實現自身的生存發展和身份構建呢?
首先,小鎮上的印第安居民要切實做到保護好腳下的這片土地。對于印第安人而言,土地絕不僅僅是用于開發從而獲取利益的工具,它更是承載所有生命的載體,是所有生命的源泉。“這是印第安人的土地。這是我們的寶貝,是我們的領土。"[3]310以格雷克勞德(Graycloud family)一家人為代表的小鎮印第安人民眾都清楚地知道誰是殺害格雷斯等人的元兇,也知道在美國現有的法律體制下,利令智昏的白人并不會為他們伸張正義。所以在這場保護族人權利和對抗白人貪欲的斗爭中,只有保護好腳下的這片土地,才能保全族人,才能阻止更多的罪惡。正如基爾·霍布森(Geary Hobson)在《被記住的土地》(The Remembered Earth,1980)的前言中寫道:“遺產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土地,土地就是遺產。通過記住這些——人民、大地、過去——的關系,我們重申了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延續的力量。……‘人民'和‘土地’是無法區分,不可分割的。”[5]
其次,印第安人可以借助傳統文化的精神力量幫助族人度過這場危機。在遠離小鎮的某個僻靜之處生活著一群古老的族人。因為他們隱居在山上,所以被小鎮上的印第安居民尊稱為“山人”(The Hill People)。盡管生活在別處,山上的古老族人卻一直默默地關注瓦托納小鎮上的情況、關心格雷克勞德等印第安居民的安危并指導他們與白人作斗爭。可以說,“山人”擔當著小鎮居民精神領袖的角色,指引著他們回歸傳統,實現自身的生存發展和身份構建。“在山人古老的居住地彌漫著一種不同的安寧,那里如此寧靜,它深深地浸入大地火紅的骨架中。”[3]253他們在這場保衛大地的戰爭中伸張了正義,也最終引導白人重新認識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
印第安老人米卡爾·霍斯通過書寫《霍斯福音》來傳遞印第安人的精神信仰。他說道:“《圣經》滿是錯誤,我想我會校正它,例如,它何處提及所有的生物都平等合一?”[3]273于他而言,書寫更像是一種救贖的行為。霍斯的書寫行為在為族人傳承印第安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給白人以警醒和啟示。可以說,這部作品不僅僅是印第安人的心靈指南,也是指引白人行為的精神向導。它教導人們“尊崇天空父親和大地母親,照看所有的一切……與大地溫和共存……向大地祈禱,修復身心,恢復表達,重塑靈魂,使之與自然和宇宙和諧共處……”[3]361
再次,在這場面對環境非正義行為的運動中,印第安人不僅依靠自己的綿薄之力奮起應戰,還盡力將自己的生態思想傳遞給其他人。在小說中,克里族人牧師喬·比利(Joe Billy)和警探斯泰斯·雷德·霍克(Stace Red Hawk)的思想變化彰顯了印第安文化的精神影響力。
作為精神世界的導師,克里族人牧師喬·比利摒棄了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試圖接受印第安傳統文化中關于“萬物合一”的靈學思想。通過這些方式,他最終保全大地免遭涂炭,保護族人免遭殺戮。年輕時的喬·比利贏得白人女子瑪莎的芳心。從神學院畢業回到家鄉后,他立志拯救和服務于他自己的印第安鄉民。在小鎮上的浸禮會教堂里,喬對他的教眾們宣講著神的旨意。然而白人與印第安人兩個社會群體之間的激烈沖突讓他逐漸意識到:在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中,白人的上帝已經無法再給印第安人信眾帶來心靈上的慰藉。白人在探測石油時打井爆破的聲音將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大地撕裂。最后,連比利牧師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的布道。“那是我向別人許下的諾言,當他們在世的日子結束時,他們將進入天堂的黃金世界。我覺得自己像個偽君子。”[3]261他認識到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與印第安人的大地倫理思想的背道而馳。最終,喬·比利和他的白人妻子一同選擇摒棄基督教的上帝,走向印第安“山人”的世界。
來自華盛頓的警探斯泰斯·雷德·霍克是另外一個深受印第安文化影響的例子。他同情印第安人的處境,一開始他希望用強大的聯邦法律為他們伸張正義。但是,他親眼目睹了聯邦政府對于印第安人的冷漠態度。這一切讓他意識到所謂強大公正的聯邦法律并不能保證印第安人的安寧,更無法保護這片土地免遭白人的侵害。所以他最終放棄了政府的工作,選擇信奉印第安人的傳統。“他感受到了大地的靈魂……他感受到了河流的美麗和力量,他變得頭腦清醒,他確信為政府工作是一個錯誤的決定……有時斯泰斯認為人們已經走入絕境,但有時他又知道未來是一片開闊地,他必須找到新路穿過它。”[3]248
四、結語
美國教授喬治·廷克曾說,“現代社會的生態惡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式、歐化的改變造成的,它逐漸突出個人而貶低共同利益,對于自治、自主、長久存在的原住民群體缺乏政治上、經濟上的尊敬和理論上的認同。”[6]現代人的盲目自大更是加劇了這種生態的惡化。這種盲目自大體現在對于地球的無止境的征服,對于資源的無窮探索和貪婪占有,對于欲望的無法扼制等等。所有這一切終將造成人類與自然世界的對立,產生各種生態危機。面對這樣的現狀,霍根在小說中通過歷史再敘的手法既描述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不公,又彰顯了印第安人對于人類與土地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的信仰所能激發的生命力。作為印第安少數族裔的一員,霍根親自經歷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種種不公平待遇。這種不公平不公正行為在《卑劣的靈魂》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通過反復講述各種環境種族主義行為,她積極地為印第安群體發聲,呼吁并尋求環境和社會正義。“她崇尚彌合與補救,竭力傳達生態保護思想,希望用文學打動心靈,改變精神狀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