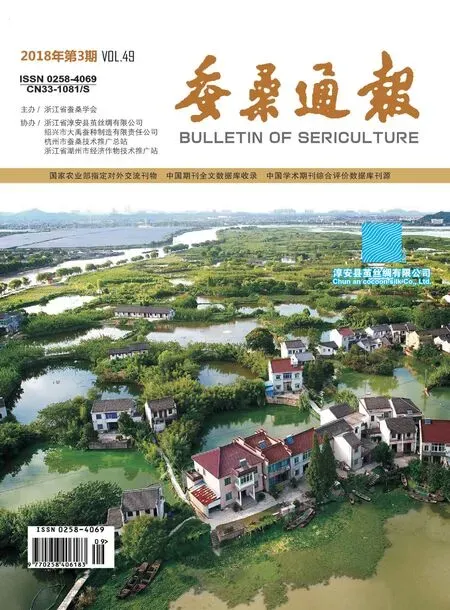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蠶業(上)
蔣猷龍
第一節 三國時代的蠶業
東漢末期,曹操、劉備和孫權,各在所處的統治范圍內擴充勢力,先后建立魏、蜀、吳,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前后長達六十年之久,在此時期,三國分治,生產開始恢復,蠶業生產也有所發展。
魏統治我國的北方,包括蠶業的重點地區,蠶業生產仍不失為農業生產的重要內容。且大力墾殖屯田遠達隴西,把蠶桑生產擴展到西北。《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載“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說明屯民除繳納租谷供應軍糧為主外,也必須向統治者提供綿絹。興平年間(194~195),曹操有一次帶著一千多人馬,行軍路過新鄭,因缺乏軍糧,新鄭的地方官楊沛知道后,立即命令百姓進獻積儲的干桑椹,解決了曹軍缺糧的困難。用民間儲存的干桑椹解決曹軍千余人的缺糧困難,所需桑椹數量是相當大的,由此可見,當時新鄭一帶有大面積的桑樹林。由于蠶絲生產的普遍,規定每戶田租出絹兩匹、綿二斤,可能這標準對農民來說還不是過重的負擔。建安九年(204),曹操克袁紹,正式令“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①《魏書》“趙儼傳”。《冊府元龜》上也有同樣的記載:“魏太祖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戶絹二匹,并綿二斤”。從左思《魏都賦》所載“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綿纊房子,縑縂清河,若此之屬,繁實伙夠”,可看出當時蠶絲業的興盛景象。為了保障蠶絲生產,曹操曾在軍令中申明“軍行,不得砍伐五果、桑柘、棘棗”②《通典》卷149。當時在野王(今河南沁陽縣)有連成數百頃的桑田③《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曹植詩“美女篇”所載“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落葉何翩翩”,“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何繽紛”(曹植“雜詩六首之三”),描繪了當時采桑養蠶的盛況。
“夏則縑、縂繪,其自如雪。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下,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鏤飾之物”④《魏志》“夏候尚傳”,公元238年日本女王遣使貢獻,曹叡賜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紺地句文綿三匹”⑤《魏志》“東夷傳”。說明高級絲織品也有所生產。
魏時,機匠馬鈞對綾機作了重大的改革。“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仍皆易以十二躡”⑥《三國志》杜夔傳注引“馬鈞傳”。綾機經過這樣的改革,非但提高了工具效率,且可以織出更為奇立異變的織品。
地處西北的隴西地方,是曹魏大力墾殖屯田發展生產的地方。1972~1973年從嘉峪關東戈壁灘上挖掘到從曹魏到西晉的墓葬,在砌墓的采磚畫像中,有繪成采桑、養蠶的場面,這是隴西曾試圖發展蠶業的真實記錄⑦《文物》,1975年第1期,第47頁。
在魏、蜀、吳三國中,絲織技術最高超的是蜀國,尤以錦為名產,為他國所不及。劉備以成都為中心建立蜀國,統治地區包括四川和云貴。四川的蠶業在漢末就很發達“桑梓接連”,著名的蜀錦在對吳國和魏國的貿易上有重要的地位,諸葛亮也建議政府必須擴大蜀錦的貿易以輔助財政上的不足,“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當蜀的勢力伸展到西南地區時,把蠶業技術帶到了云南,后人為紀念諸葛亮的功德,曾刻石說:“昔日夷壇舊瞧天,如今原峂盡桑田”。⑧《諸葛亮集》“遺跡篇”
蜀錦亦作為犒賞功臣的物資,“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克蜀,……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錦千匹,其余各有差”⑨《蜀志》轉引自《太單御覽》卷815。錦又作為友誼交流的物資,蜀與吳國交往,“遺使獻重錦千端”⑩環氏《吳記》。公元223年蜀使中郎將鄧芝去吳,帶去錦千端(1匹=2端)及方物,自此以后,聘使往來以為常。公元263年劉禪降魏時,派尚書郎李虛到魏所送到“土民簿”上開列“綿、綺、綵、絹各二十匹”[11]《蜀志》。在蜀國的領域內,多處為蠶絲織產地,巴有“桑、蠶、麻、芋”;巴西郡有“桑、蠶”;蜀有“錦繡、有桑”;漢安縣“宜蠶桑”;永昌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諸葛亮在成都自己的家中也“有桑八百株”(諸葛亮“上后主表”)。
成都在漢時就已成為全國的絲織中心之一,由于長期處于穩定的環境中,三國時更是繁榮昌盛,“阛阓之里,伎巧成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12]左思《蜀都賦》,非但有織機之多,織工之巧,且江水清澈,織錦洗滌后,文明更勝于初成,此后更命江水為錦江。高級絲織品計有錦繡篡組,綺羅綾段等種,更以黃繭絲為名產。
孫權在江東立國,對東南地區的開發有顯著的成效。公元240年吳王孫權命令“當農桑時擾民者,舉正以聞”[13]《吳志》“孫權傳”,公元259年孫休提出“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14]《吳志》“孫休傳”;公元264年孫皓繼位,華霰霾建議政府必須“暫息眾役,專習農桑”[15]《吳志》“陸檄傳”。當陸遜到海昌(今浙江海寧)任屯田都尉時,他“勸督農桑”[16]《吳志》“陸遜傳”。使長江中下游的經濟,較東漢時有所發展,這也與東漢末年中原和江淮間大量流民逃入荊揚有關,他們帶來了北方較先進的生產技術,使江東地區原來的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了改進。
在吳建國期間,屢次號召發展蠶桑。吳國的勢力繼承兩漢的余緒一直延伸到日南郡。左思《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當時吳國的勢力范圍一直到日南(今越南),“八蠶之綿”可能是該地貢獻上來的多化性蠶絲綿,這是不能繅絲織綢的,以細軟著稱。
吳在三國中,可能是絲織技術較差的。國內所需的錦大部分從蜀國買來,“江東歷代尚未有錦”[17]山謙之《丹陽記》,“吳所織如意、虎頭、連壁等錦,來至洛邑,亦皆不惡”[18]張澍《蜀典·魏文部論》,故從《吳都賦》中只提到“鄉貢八蠶之綿”,大概從吳國所屬地區的繭質來說,適于生產一些質地較菲薄的絹、繒之類。
第二節 兩晉南北朝的蠶業
1 蠶業概況
公元265年,西晉結束了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統一了中國。司馬氏雖然是一個極其腐朽的集團,但在完成國家統一事業上作出了成績,在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統治集團內部八王混戰,人民顛沛流離,北方少數民族不斷起來反抗司馬氏的統治,316年西晉王朝滅亡。在此后的139多年期間,黃河流域則由少數民族的豪酋各自獨立稱王,先后陷于二十幾個地方政權的爭戰之中,所謂十六國時期,經濟遭受到嚴重的破壞,造成“人皆疏散”,“千里無煙”的慘景。直至鮮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才結束了北方長期分裂的局面。
北魏至明帝時(409年)已非常重視農桑生產,采取屯田,計口授田,勸課農桑等措施,使農桑生產在北魏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原來的畜牧業比重相應地逐步降低。在整個北魏統治時期的一百多年間,差不多始終貫徹著恢復和發展農桑生產的政策,賈思勰(xie)寫的《齊民要術》至今仍然是一部重要的農業百科全書,它的產生是與北魏的時代環境分不開的,其中有一卷專論種桑柘,收入前代的蠶桑科技成就以及當代的生產經驗,想必在指導當時的蠶桑生產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北魏的重視農桑,對后來的東西魏(534~556)、北齊(550~577)、北周(557~581),甚至隋、唐也有相當的影響。
西晉對農業土地的生產和分配,采用占田制和戶調,北魏將這一套制度整個承襲了下來,并進一步調整生產關系而采取計口授田,雖然統治者有嚴重剝削的一面,但對恢復和發展生產,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收到比較良好的效果。繼北魏之后,北方又相繼建設了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是為北朝。
與此相平行地進行著的是,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被推為晉王,建立起東晉王朝,統治著長江流域,這是百多年來相對地比較安定的地方,此時,經濟和文化較前有一定的發展,但由于統治集團政治腐敗和各地藩鎮割據,公元420年被劉裕所滅,由劉氏建立起宋王朝,以后劉宋又相繼為齊、梁、陳王朝所代替,是為南朝。
我國蠶業生產在這300余年間,無論在產繭量、蠶業地區,還是在絲綢品種以及絲綢貿易方面,都起著急劇的變化。
左思《魏都賦》描寫出曹魏時河北的清河、房子、朝歌盛產綿纊和羅綺,并與河南襄邑的錦繡相媲美,這也反映了兩晉初在兩河平原仍是主要的蠶絲產區,又鉅鹿,清河以北的趙郡、中山和常山等處所產的縑也很有名[19]《初學記》卷29“絹”第九引“晉令”。陜西的蠶桑仍很旺盛,關中平原“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20]潘發仁《西征賦》。
當北方流離期間,太行山以東的蠶業有了新的發展,河北的冀州和定州,北魏政府一年內的征絹額達30萬匹以上,認為“國之資儲”,“唯借河北”[21]《北史》卷17“常山王遵傳”。所以《齊民要術》上提到自河以北,大戶所收的桑椹在百石以上,小戶也可收到數十斛。到了稍后的北齊,這里的絲織品更加精良,“河北婦人織紅組紃之事,黼黻錦繡之工,大優于江東”[22]《顏氏家訓》“治家篇”,在統治區域內,山西的司(今大同)、秦(今永濟),河北的冀(今冀縣)、定(今定縣)、相(今臨漳),陜西的雍(今西安)、華(今華縣),河南的洛(今洛陽)、懷(今沁陽縣)、兗(yan,今滑縣)、陜(今陜縣),山東的青(今益都)、齊(今齊南)、濟(今長清縣)、東兗(今舊滋陽縣)等,處在黃河流域的15個州,以及豫、徐、東徐、南徐等處在較南的地區,都要交納綿和絲綢,可見當時主要蠶區大致與前代相仿。
北齊政府也重視蠶桑生產,河清三年(564)下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23]《隋書》“食貨志”。
北燕在馮跋統治時期(409~428),也獎勵蠶桑的發展,下詔書說:“桑柘之生,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在大凌河流域種桑,比原來蠶區的北限平城更為北進了。
慕容魔于公元307年在遼河兩岸自稱大單于,為前燕建國打下了基礎,那時他曾想在這一帶發展蠶業,“先是遼川無桑,及(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來”[24]《晉書》卷124“慕容寶傳”,平川在今遼寧省遼陽市一帶,說明江浙的桑品種到北方移植成功。待至慕容銧(337~370)正式建立前燕國時,他曾“躬巡郡縣,功課農桑”[25]《前燕錄》。,直到公元370年前燕亡于秦前后,這里還有桑樹的栽種,“晃之遷于龍城,植桑為社主。及秦亡燕,大風吹拔后,數年度,社處有二處生焉”[26]《后燕錄》,可是,已遭到嚴重的破壞了。
處在西北的甘肅,在三國曹魏時就開始經營蠶業,延至西晉末年,司馬保為劉曜所攻向西遷徙,一直到桑城[27]《晉書》卷103“劉曜載記”,地以桑名,說明桑樹的種植較多,桑樹在今甘肅臨洮縣境。嘉嶺關壁畫上有不少蠶繭、絹帛、絲束以及少數民族婦女在樹下作采擷狀的采桑畫像,證明西晉時河西地區,蠶業已是農業的一部分了。
北朝時,蠶業已擴展到新疆,“于田城東三十里,……土宜五谷并桑麻”,“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28]《北史》“魏書·西域傳”。高昌國也“宜蠶”[29]《隋書》“西域”;《北史》“西域傳·高昌國”,可能新疆是新發展地區,繅絲的技術還沒有掌握,生產的蠶繭主要用于絲綿制作。
當北方處于戰火滿天的長期歲月中時,長江以南則處于相對穩定的社會局勢中,大量北方人口南遷,將北方先進生產技術帶到南方,經歷孫吳、東晉和南朝勞動人民的辛勤墾殖和經營,蠶業生產欣欣向榮,以致“荊城跨南楚之富,楊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30]《宋書》卷54“傳論”。如“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苧,各盡其方”[31]《宋書》卷5“文帝紀”,又“舊巷綠藩,必樹桑柘”[32]《宋書》卷42“周朗傳”。“孝武(454~464)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
梁時,浙江東部山區開始發展蠶桑生產,如公元498年沈瑀為建德縣令時“教民一丁種十五株,女丁半之”[33]《晉書》“食貨志”,可見當時南朝的糧食生產已超過北朝,而紡織業仍較北朝為遜。
處于漢中的兩湖,也在發展蠶業,如在西晉時,“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34]《吳越錢氏志》卷23“志余”。“但愿桑麻成,蠶月得紡績”[35]《宋書》“周郎傳”。南齊時,王嶷(yi)為“南蠻校尉,荊湘二州刺史,南蠻資費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近代莫比也”[36]陶潛“擬古詩”,則說明兩湖和江西有一定水平的蠶絲生產。南朝梁天監六年(507)時,孫謙為零陵太守,“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于鄰境”[37]陶潛“田居詩”。
處在西南地區的四川,仍保持著蠶絲生產的傳統。巴地“桑、麻、蠶、……皆納貢之”,蜀地有“錦、繡、桑,……之饒,故多斑采文章”,“成都江水濯錦則鮮明”[38]《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傳》。
地處今云南的永昌郡,亦有“桑、蠶、綿、絹、采帛、文繡”[39]《梁書》卷53“良史”。晉詩“綿州歌”中說,“織明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都表明西南蠶織業之盛。
新疆蠶絲業始于公元3~4世紀。尼雅遺址中曾發現蛾口繭一顆,時間最遲不晚于4世紀;出土的吐魯番文書中有“建初十四年(418)嚴福愿賃蠶桑券”和“賃叁簿蠶桑”的記載。哈拉和卓1999年出土的“某家失火燒損財物表”中有“蠶種十薄、綿十兩、綿經緯二斤、絹姬(機)一具”等物品的記錄。另在“高昌永康十年(475)用綿作錦絳線文書”中記載有:“須綿三斤,作錦絳”。其它出土的文書中有丘慈錦、疏勒錦、高昌所作丘慈錦等記載,說明當時新疆地區的尼雅(今民豐)、丘慈(今庫車)、疏勒(今喀什)和高昌(今吐魯番)等地已經有蠶絲生產了。
2 蠶業技術
2.1 栽桑技術
北魏規定每一男丁所分給的1.33 hm2桑田,限令種桑50株,作為私人產業可以傳給子孫,對發展蠶業是有促進作用的。《齊民要術》上記載著的栽桑技術,比之前代進步和詳盡得多。
(1)桑種和培苗
有女桑、檿桑、荊桑、地桑、黑魯桑、黃魯桑等名稱,并認識其中的優良種是黑魯桑,直至近代,黑魯桑仍不失為山東的主要桑品種,女桑指矮小的桑樹,地桑是低干桑。不是種類上的差別,檿桑據作者考證,乃是今所稱的柞樹。
播種法是收取桑椹后,在水中淘洗種子,干燥后,散播在濕潤的畦上,經常鋤盡雜草,到明年春季即可移栽。
柘葉亦作為蠶的飼料之一。種柘時,先耕熟土地,將柘子散播,勤拔雜草。
另一種是壓條育苗法。在一、二月把桑樹下部的枝條下壓著地,待條上生葉高數寸時,即用燥土將條埋入,讓其發根,到翌年正月切斷為苗,待后栽種。壓條苗的生長較實生苗快速,因此,僅在不能壓條的情況下,才采用種子播種法。
(2)栽桑
不論實生苗或壓條苗,都以正月栽種為最好,二月次之,三月較差,株行距各為五尺,間作綠豆和小豆,在二、三年間概不采葉,以免影響幼桑的生長發育。待幼桑枝干長成手臂樣粗時,然后移栽定植。十步(六尺為步)一株,對角線栽種,稀植的目的是為了要間作禾豆,既收獲了豆類,又肥了桑地。甚至在桑樹四周一步處撒插蕪菁子,收割后在地上任豬取食,增加桑地有機質肥料,對疏松土壤的效果較之用牛翻耕更好。
對栽好所有樹木,其中包括桑樹在內的共同經驗是:“欲記其陰陽,不令轉易(陰陽易位是難生,少小栽者不煩記),大樹髡(kun)之(不髡,風搖即死),小則不髡。先為滌坑,內樹訖,以水沃之,蓋上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搖則泥入根間,無不活者,不搖根虛多死,其小樹則不煩爾),然后下土堅筑(近上三寸不筑,取其柔潤也),時時溉灌,常令潤滑(每澆水盡,則已燥土覆之,覆則保澤,不然則干涸)。埋之欲滌,忽令撓動。風栽樹訖,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觚突”《齊民要術》。
(3)條葉的收獲和修剪
養成的喬木桑,在冬季進行修砍,最遲不過二月,以免傷流而損傷樹勢和減少產葉量。對不同桑樹的修砍標準是:繁盛的多修,枝少的少修。秋條雖然多砍可以促使春條茂盛,但應避免在日中進行,而冬春修砍則不受時間的限制。采春葉要在早晚進行,對每一枝條的葉必須采盡,免得多發側枝(雞腳)。秋葉必須在以后將砍去的條上采摘,并且不能多采以損桑條。從此可見,迄至6世紀前期,我國北方飼養二化性蠶(春蠶經夏蠶后才至秋蠶)仍是非常普遍的。
南朝的桑樹也多喬木桑,采桑時必須“采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40]佚名詩“采桑度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