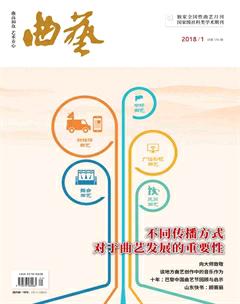在《曲苑雜壇》的日子里
陳連升
《曲苑雜壇》是中央電視臺推出的以曲藝、雜技為主,薈萃古今中外文化藝術,深受廣大觀眾喜愛的綜藝欄目。這個欄目創始于1991年,收官于2011年,足足火了20年。欄目開播100期的時候,曾有位觀眾寫了這樣一幅對聯贊譽《曲苑雜壇》。上聯是“曲苑雜壇良師益友人人愛看看不夠”,下聯是“新聲古韻美酒佳肴人人爭夸夸不完”,橫批是“《曲苑雜壇》繁花似錦”。對聯說得沒錯,那時候人們不管多忙,只要聽到“相聲、小品、魔術、雜技……”這個耳熟能詳的片頭曲,就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計,圍坐在電視機旁,這幾乎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曲苑雜壇》欄目和觀眾心貼心,為滿足觀眾的欣賞興趣和審美需要不斷地改版:從《相聲電視》到《絕活系列》,從《說唱電視》到《四不像》《信不信由你》,從《中國雜技金牌榜》到《魔術集錦》,乃至膾炙人口的系列《洛桑學藝》《聰明的劇務》《放驢小子》等,年年推出一些新的節目形式,年年奉獻出一批有趣的節目內容,還培養包裝了一大批身懷絕技的青年演員,始終躍動著活力。
榮幸的是,我從電臺一退休,就被中央電視臺文藝部聘請到《曲苑雜壇》當臨時編輯,一干就是三年多。剛開始,組里給我安排了四項工作。一是給每期節目寫電視報介紹稿;二是匯總每期的觀眾來信,上報給臺領導和職能部門;三是主持人錄“串聯”的時候,欄目完成后期制作的時候,檢查錯別字;四是為制片人汪文華起草一些重要會議上的發言稿草稿。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組內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這些活兒在我眼里不算太重,稍花點心思,費點力氣便能完成。可看看組里的兩位在編人員(包括汪文華),她們除了負責定期播出的《曲苑雜壇》,還負責每天兩次播出的《電視書場》欄目,實在是太忙了。尤其是汪文華,身兼主持人、導演、制片人三項職責,干的活比別人都多,整天不是錄“串聯”,就是外出采訪、組織節目,再不就是泡在機房里做后期,一點沒有空閑時間。雙休日與她無緣,就連國慶節法定的休息時間她也繼續堅守在工作崗位上操勞。她們的拼搏精神、吃苦精神激勵著我,感染著我。我想,我應當沖上第一線,多干點實際工作為她們分憂。我知道組織節目是編輯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我首先關注這一工作。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資源,我向組內推薦許多適合電視播出又非常討巧的節目,像曲藝絕活“五音聯彈”“含燈大鼓”,新編群口相聲《五福捧壽》,山東濟寧拔尖曲藝人才劉心科創作的山東琴書《孔子拜師》,還有山西大同柴京云、柴京海創作表演的大同數來寶《家丑外揚》等,這些節目汪導都一一采納,并錄制播出。
一次我從觀眾來信中得知,安徽有一家人都會雜耍,特別是五歲的兒子既會打擊樂,又會吹嗩吶,很有特色,我就推薦給組里。汪導認為這很不錯,有看點,能調動觀眾的興趣就制訂了錄制方案,還請編導組鄭天庸參與演出。她給這個節目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歡樂家庭》。沒想到這個節目一播就火了,觀眾紛紛來信贊揚。有一位來信說:“《歡樂家庭》帶來了歡樂的感受。舞臺上一家三口,各顯技藝,特別是五歲的兒子,更是不凡,玩打擊樂,還會吹嗩吶。我們驚喜的不僅是節目的精彩,更在于嘆服《曲苑雜壇》在新世紀改革中的大手筆,它開創了名牌欄目讓觀眾成為表演主體的先河。實現了演員與觀眾、專業與業余并舉的兩條腿走路。它的影響是深遠的,社會意義是巨大的,因此也是可喜可賀的。”說真的,我沒想到,我推薦的一個節目會產生這么大影響。
我原來是搞廣播的,進入電視領域等于跨界,跨界的人通常對周圍的事物比較敏感。初來時,我認為,在綜藝節目漫天撒網,流行歌曲狂熱炒作的情況下,《曲苑雜壇》能堅持繼承和發揚民間藝術,真是了不起。后來又看到《曲苑雜壇》藝術品位很高。它每期50分鐘,精品節目一個接一個,汪文華的主持儀表端莊、態度和藹、語言精練到位,這在綜藝節目中猶如一股清流,實屬難得。后來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曲苑雜壇》欄目有許多風格特色是別的綜藝欄目所不具備的。例如,在欄目特點上:1.拒絕過度的商業色彩,樹立節目正氣。2.力求改變以往曲藝雜技類節目布景單調、表現力平淡的不足,借助電視手段拓展舞臺空間,豐富藝術表現力。3.薈萃了中外各種表演形式,藝術種類繁多,節目類型豐富多彩。又如《曲苑雜壇》欄目節目創意有以下特點:1.周末時間播出,以輕松為基調,以歡樂為主旨。2.各種藝術形式取長補短,融會貫通打造曲藝綜藝節目新形式。例如,將口技與手技結合,相聲和魔術、雜技結合,評彈與現代舞相結合的嘗試等。3.在不斷挖掘優秀作品、展示前輩藝術家風采的同時,著力挖掘新人新作,為大批新秀提供大顯身手的機會。《曲苑雜壇》在運作方式上也有特點:1.布局合理的人才結構,取老、中、青三代之所長,發揮各自優勢,保證節目的健康發展,用八個字概括就是“新老結合,通力合作”。2.在當今信息傳媒日益發展的時代,借鑒其他藝術類型與節目風格,取其精華為我所用,另外與國內同行多交流,取長補短,厚積薄發。3.優秀的節目是保障《曲苑雜壇》收視率和良好口碑的根本,為此欄目開拓思路,利用自身的優勢與各地曲協、雜協、藝術團體通力合作,不斷地把各地的優秀節目推薦給觀眾,同時與一些有才華的作家簽約,源源不斷為欄目創作高質量的作品。我把以上的發現與思考寫成了一篇題為《〈曲苑雜壇〉創意分析》的文章交給了文藝部,沒想到獲得大家一致認可。《曲苑雜壇》制片人汪文華還把我的創意分析當成對欄目的整體介紹,加以廣泛宣傳,這讓我心里感到熱乎乎的,工作也更有動力了。2001年,組里要增加新內容《南腔北調》,汪導不僅讓我參與策劃,還把寫“串聯”的任務交給了我。
2000年8月,《曲苑雜壇》播出100期,在此之前,考慮到欄目在社會上的廣泛影響,我建議搞一次《曲苑雜壇》百期征文活動。汪文華很支持,經她同意我在《中國電視報》上發了征文啟示,還不到兩個月,稿件就像雪片一樣飛來。來稿中有薛寶琨、王兆一、王肯、夏雨田、沈永年等專家學者寫的評論,還有笑林、王謙祥、郝愛民、種玉杰、韓寶利等著名演員寫的參加節目錄制的心得、感受。來稿最多的還是廣大普通觀眾,他們暢談了對《曲苑雜壇》的贊美、眷戀與期待。有一位觀眾的來稿令我印象最深,他寫道:初觀《曲苑雜壇》是一幅畫,畫中山清水秀,涓涓細流;靜觀《曲苑雜壇》是一部書,書中酸甜苦辣,飽含人生真諦;細觀《曲苑雜壇》是一首歌,歌中喜、怒、哀、樂,頌揚人間情真意切;慢觀《曲苑雜壇》是一條路,路上坎坷不平,引導人們從容走過……這篇征文就像一首長長的抒情詩,使人產生很多聯想。汪導看征文質量不錯,就以我為主,組織了一個小的評審班子,對來稿逐一評審,最后選上了89篇優秀征文,給作者發了獎。我尋思有了這89篇文章,下一步該出《曲苑雜壇》百期紀念文集了。于是,我對這些獲獎征文逐一進行了文字勘正、校對,生怕有任何一個錯別字,按照一定格式把這些文章排好前后順序,插圖也進行了考慮,還草擬了序言,就等汪導一聲令下出書了。等啊等,汪導終于發話了,她說:“咱們組已被選為‘全國十佳攝制組,多次獲得全國優秀節目一等獎,優秀欄目獎,現在在觀眾中又有了這樣的口碑,這就足夠了,這都是激勵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如果現在出書,勢必別的欄目組也要效仿,容易產生不必要的攀比心理,另外也會對一些暫時還不如我們的欄目形成一定壓力,考慮再三,我們不帶這個頭,不開這個先例,你說好嗎?”這便是汪文華,關鍵時刻她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欄目組,而是大局,是方方面面的問題。看來我心胸還是小了一點,我想的是重要事上紙端,人過世,字可見;看歷史,靠字傳,只想著《曲苑雜壇》能在曲藝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曲苑雜壇》這三年使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才干,受益匪淺。如今這一切都成為往事,我多么希望中央電視臺能再出現像《曲苑雜壇》這樣好的綜藝欄目,繼續發揮弘揚曲藝主陣地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