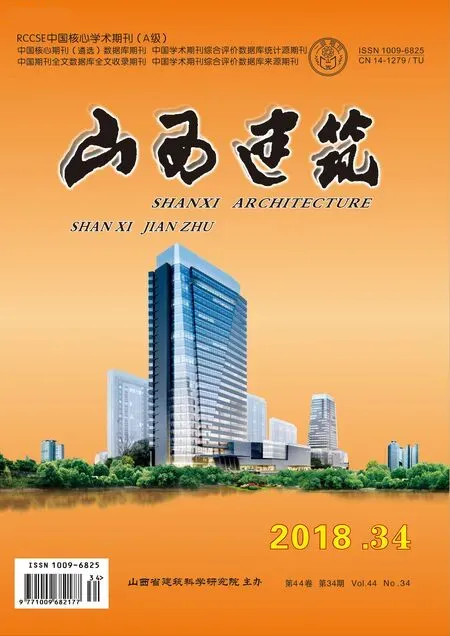水系地理變遷對平遙縣域鄉村空間體系的影響
溫 俊 卿
(山西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1)
1 平遙縣域自然地理條件及村莊現狀
平遙縣總面積1 262.5 km2,處在兩個三級構造單元的邊緣交叉地帶,地貌景觀復雜多樣,總體上屬于黃土高原的一部分。東南方依太岳北麓,主要山脈為東南走向,山勢由東南向西北緩傾而下,到西北部成為汾河河谷,整個地形特點是東南高、西北低。總體來看,全縣可劃分為4類地貌類型區:構造剝蝕的中低山區、切割強烈的黃土溝梁區、沖洪積傾斜平原區、沖積平原區,各地貌類型區域的村莊呈現不同風貌特點。
構造剝蝕的中低山區,包括孟山鄉和朱坑鄉、東泉鎮、卜宜鄉、段村鎮的一部分,面積557.88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44.2%,海拔1 000 m以上,相對高差900 m以上,最高1 962 m(孟山)。此區域為土石山區,范圍較大,鄉村居民點分布少、規模小、村莊多依地形靈活布局,村莊建設用地緊張、農業耕作條件較差,主要以森林植被自然景觀為主。
切割強烈的黃土溝梁區,包括朱坑鄉、東泉鎮、卜宜鄉、段村鎮及襄垣鄉、岳壁鄉、中都鄉的部分地區,面積181.62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14.4%,海拔800 m~1 000 m;此區域范圍較小,是中低山區下降的過渡地帶,兼有山區和平原區的特征,河流水系發育,農業耕作條件較好,居民點數量、規模開始擴大。
沖洪積傾斜平原區,包括古陶鎮、中都鄉、襄垣鄉及洪善鎮的部分地區,面積173.62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13.8%,為汾河二級階地,海拔750 m~800 m;此區域基礎地質條件較好,農業耕作條件較好,土壤類型為濕陷性黃土,也是常用的村莊居民點建筑原材料。礦產資源豐富,村莊居民點數量多、規模大,布局較為集中、多堡寨形式,是縣域資源、經濟、生產活躍度較高的區域。
沖積平原區,屬堆積地形,分布在汾河兩岸的平原地帶,包括香樂鄉、寧固鎮、杜家莊鄉、南鄭鄉及中都鄉、古陶鎮、洪善鎮的部分地區,面積348.51 km2,占全縣總面積的27.6%,為汾河一級階地,海拔735 m~750 m;此區域地形平坦,農業資源、交通運輸條件好,村莊居民點普遍規模較大,現代化程度高。
2 昭余祁澤藪的變化
《水經注》記載:“《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巖,有草無木,泉源導于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峰接勢。”“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為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是為山西境內河湖的概述。
《墨子兼愛中》:“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滹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據學者考證,后之邸即昭余祁,滹池即滹沱河。
《周禮·夏官·職方氏》出現并州藪,《呂氏春秋》稱昭余祁為全國的九藪之一,《漢書·地理志》:“九澤在(鄔縣)北,是為昭余祁,并州藪。”清末學者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對“九澤”解釋為“陂澤連接,其藪有九,故謂之九澤,總名日昭余祁”。表明曾經的昭余祁澤藪,已從大湖縮減變成九個較小湖泊了。
據以上文獻分析,昭余祁澤藪是山西中部的古代湖泊,也稱古晉陽湖,位于晉中盆地偏南部,其水源主要是上游的汾河,及其瀟河、文峪河、昌源河等汾河支流。眾水匯集昭余祁大湖,再通過雀鼠谷下泄,湖面方圓數百里,范圍包括今太谷、祁縣、平遙、文水、汾陽等地。后因氣候變化,一說大禹治水“打開靈石口,空出晉陽湖”,這個古代大湖在唐、宋時期已近湮廢,元代前后徹底干涸消失。
3 昭余祁澤藪影響下的平遙聚落發展
據考,平遙縣域最早的聚落在距今6300年前開始繁榮,區域即為今縣域東南部的丘陵地帶,因西有昭余祁大澤、東有高山阻隔,東南丘陵地區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地區。此時的昭余祁澤藪在平遙境內的邊界,據推測應該是襄垣鄉青沙,朱坑鄉山坡頭、花堡、賈家坡、興旺、東郭休、郭家坡、龍峪、六莊,東泉鎮水磨頭,岳壁鄉原家莊,卜宜鄉梁家灘、棗樹坪,段村鎮廉莊、橫坡、普洞一線。這一線海拔高度約1 200 m,常見有沉積的卵石沙層,推測為湖水沖刷所致。花堡村附近的“石魚灘”化石遺址更是佐證了這一論點。
夏商時期,昭余祁澤藪面積縮減,湖水邊界下降至海拔800 m左右,這一海拔高度廣泛分布著龍山文化遺址,如羅鳴遺址、段村遺址、北堡遺址、北羌遺址等,這一時期昭余祁澤藪的邊界,據推測應該是襄垣鄉羅鳴,朱坑鄉北堡,中都鄉梁趙,段村鎮弓村一線。人類逐水而居,聚居點向西擴張。
春秋戰國時期,昭余祁澤藪面積進一步縮減,湖水邊界下降至海拔760左右,這一線開始廣泛分布春秋時期的遺存,如梁趙墓群,這一時期的昭余祁澤藪的邊界,據推測應該已近今古城一線,西部與汾陽、文水、介休交界處仍為水域。
漢朝時,昭余祁澤藪面積進一步縮減,湖水邊界下降至海拔750左右,這一線開始廣泛分布漢代遺址遺跡,如東大閆墓群、金陵城遺址、中都城舊址等,這一時期的昭余祁澤藪的邊界,據推測應該已至北長壽、南長壽、北營、東山湖、曹冀、洪善、南政、北良如、橋頭一線,西部與汾陽、文水交界處也有部分陸地出露。
北魏時,昭余祁澤藪已縮減為數個小湖泊,《水經注》載:“汾水于(大陵)縣左迤為鄔澤”又載:“候甲水(今昌源河),出谷西北流,經祁縣故城南(今祁縣祁城村附近),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余祁矣。”此時的昭余祁澤藪已被分成為“晉澤”“洞過澤”“祁藪”“鄔澤”“文湖”“武澇泊”“伯漁泊”等九澤,“祁藪”靠近祁縣、“鄔澤”靠近鄔縣(今介休縣東北),分別用“迤為”和“連延”說明古湖的淤積情況。唐《元和郡縣志》中有“鄔城泊在縣東二十六里”的簡單記載,并未提及“祁藪”,推測“祁藪”此時已消失。隨后平遙縣境內的鄔澤又別陸地分割為“小橋泊”和“張趙泊”。元代張趙泊逐步萎縮、干涸變為濕地,最終于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因汾河改道而消失。
隨著昭余祁澤藪的變化,平遙境內的村莊分布也逐步發生著變化,基本演變趨勢可概況為:“滄海桑田、澤退人居、逐水西移”,主要有三個時間階段:東南部丘陵地區的村莊建村歷史普遍較早,是平遙縣域早期人類生產生活的主要區域,中部沖積平原傾斜區和縣域西部的村莊建成年代略靠后,中西部村莊形成時間最晚。
4 昭余祁澤藪變遷所體現的村莊空間體系特點
梳理村莊的形成、變遷歷史脈絡能夠最直接地了解縣域歷史文化的發展順序,能夠比較準確地尋找重要歷史節點可能存在的重要歷史遺存及其背后可能蘊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盡管現在遺存的古村落多為明清建筑,但還是在村莊選址、與自然環境的依存度、村莊空間格局、遺留歷史構筑物等方面存在相應的時代特征:
1)從村落形成時序上講,東南部丘陵山區自古就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村莊聚落形成時間早,很多村落格局都沿古制;中部沖積平原傾斜區和西部縣界處村落多形成于漢唐,隨古城的建設達到一定的興盛;中西部平川區村落多形成于元明清,為適應人口數量的增加和社會活動的多樣性而建設。
2)早期形成的古村落多人口大村,如喬家山、彭坡頭、梁坡底,這些村莊并不具備現代意義中的便利區位條件,如交通便利、用地條件優等,成為規模較大的村莊不能排除歷史積淀的因素。
3)早期形成的古村落中多古樹。在東南丘陵地區的古村落中,隨處可見超高樹齡的大樹古樹,從人類活動與樹木植被的親密角度,也驗證了村落的歷史性。
4)不同時期村莊的名稱自成特點。早期形成的村莊,名稱多不能直解,或反映物質特點、或蘊含一定寓意或希望、或無可考證,如東勝、龍峪、黃倉、豐盛、興旺等。中期形成的村莊因時代更迭、時有戰亂,村莊名稱多反映一定功能,如南羌、北羌、西羌、大羌、軍寨、官地、營里等,顯示其最初的軍事功能。后期形成的村莊則更接近現代常見村莊的命名方式,直接以聚居人口的姓氏命名,如杜村、曹村、王家莊、郝家堡等。
5 結語
本次研究重在從空間角度理出自然山水格局變遷對鄉村聚落發展產生的影響、留下的痕跡,為求能夠在已經支離破碎的歷史文化信息中重新建立起內在邏輯,為縣域散落的鄉村找到其發生發展的本源動力及路徑,為縣域鄉村振興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更長時間序列、更廣地域范圍的文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