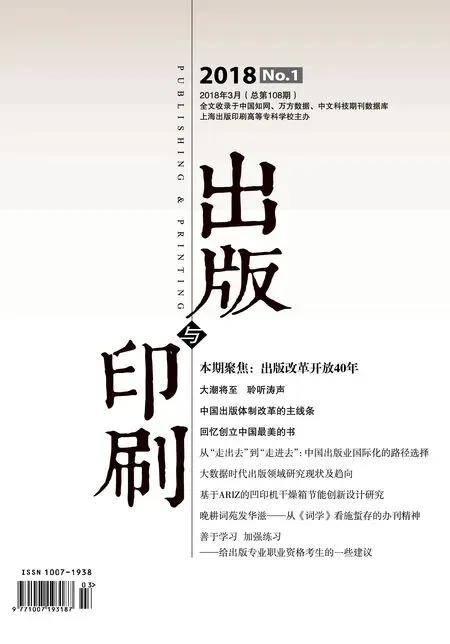服務與活動:全民閱讀推廣的兩種方式
——以“流動書包”與“丟書大作戰”為例
段 弘
2016年年底,我國制定的首個國家級“全民閱讀”規劃《全民閱讀“十三五”時期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印發,全民閱讀工程被列入“十三五”時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表述上,《規劃》將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倡導全民閱讀”變更為“推動全民閱讀”,對各級政府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換句話說,對于全社會,閱讀可以“倡導”,但對于政府而言,閱讀作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則需要“推動”。
當前我國全民閱讀整體情況雖有所改善,但與“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推廣強度并不相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于2017年4月18日發布的第十四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為68.2%,較2015年上升了4.2個百分點;圖書閱讀率為58.8%,較2015年上升了0.4個百分點;當年全國成年國民人均圖書閱讀量為7.86本,較2015年增加了0.02本,其中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65本,電子書閱讀量為3.21本。在對國民個人總體閱讀情況進行調查時,表示滿意(包括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的占19.6%,比2015年的20.8%有所下降;表示不滿意(包括比較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的占18.5%,比2015年的17.4%有所提升;另有47.6%的國民表示一般。[1]橫向對比來看,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顯示,北歐國家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已經達到24本,韓國為11 本,日本和法國為8.4 本。[2]由此可見,全民閱讀推廣尚存一定的提升空間,“政府主導的服務型閱讀推廣”應與“社會參與的活動型閱讀推廣”有效融合,形成“服務與活動相結合”的全民閱讀推廣模式。
一、閱讀推廣的概念界定
閱讀是讀者“使用符號引導自己激活記憶中的信息,然后運用被激活的信息構建對作者所傳達信息的合理解釋”。[3]因此,閱讀是一種需要長期大量訓練才能習得的能力,只有存在明確的閱讀需求或適宜的閱讀環境與條件,人才會成為閱讀者。[4]所謂閱讀推廣(reading promotion),簡言之就是由主體開展的、針對讀者對象,推動、倡導和促進其閱讀意識,提升其閱讀興趣,促使其實施閱讀行為。
1.閱讀推廣三要素
閱讀推廣概念難以形成有效邊界的原因是由于其三要素——閱讀推廣主體、閱讀推廣客體、閱讀推廣內容都很復雜。
(1)閱讀推廣主體。針對不同的劃分標準,閱讀推廣主體可分為不同的類型。
按照主體在閱讀推廣工作中的具體分工,可分為策劃主體、實施主體、宣傳主體、營銷主體、分析主體等。不同環節,可由同一主體擔任,也可由不同主體擔任;同一環節,可以是單一主體,也可以是多個主體。
按照閱讀推廣主體的性質,可將其分為兩大類,即政府主體與社會主體。政府在開展閱讀推廣時,是將多種公共資源配置到此項工作中;而社會作為閱讀推廣主體,主要調動的是社會資源。
(2)閱讀推廣對象。不同的閱讀推廣工作,其針對的目標對象是不同的,即使有明確的目標范圍,其指向仍然難以明晰邊界。
按推廣對象的閱讀能力可分為:缺乏閱讀意愿的對象、有閱讀意愿而不善于閱讀的對象、有閱讀困難的對象、有較好閱讀能力卻無閱讀內容的對象。[5]
按照閱讀對象的服務定位劃分,可將閱讀推廣的目標人群設定為有特殊閱讀需求的人群,可對其進行服務策略研究,如親子閱讀推廣、兒童閱讀推廣、學生閱讀推廣、女性讀者閱讀推廣(再細分為城市女性與鄉村女性,職業女性與家庭女性等)、老年讀者閱讀推廣、商界人士閱讀推廣、學者群體閱讀推廣等。
(3)閱讀推廣內容。正如定義中所言,閱讀推廣具體行為主要包括三個層面,即閱讀意識、閱讀興趣和閱讀行為。
針對不同的層面,閱讀推廣內容可選擇相應重點,比如倡導閱讀意識的話題討論,提升閱讀興趣的新書推介會、作家簽售,促進閱讀行為的讀書會等。
2.閱讀推廣概念辨析
閱讀推廣這一概念經常會與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等混用,造成概念內涵與外延的諸多混亂和模糊。嚴格說來,閱讀推廣是一個操作性概念,其目標在于提升閱讀推廣對象的閱讀素養,包括其終身學習和非正式學習方面的能力。這四個概念在邏輯上有聯系,后三個概念的主體是第一個概念的對象。
同時,閱讀推廣也經常與圖書宣傳推廣、閱讀指導等概念混用,同樣存在語義指向歧義:閱讀推廣是一種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和公共服務;圖書宣傳推廣則是有利益考量的具體行為,針對的是圖書產品;閱讀指導是針對具體閱讀障礙與能力缺失的輔助行為。
二、政府主導的服務型閱讀推廣與社會主導的活動型閱讀推廣
在對上述概念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政府和社會這兩個主體為標準,可將閱讀推廣分為兩大類,即服務型閱讀推廣和活動型閱讀推廣。
1.政府主導的服務型閱讀推廣模式
服務型閱讀推廣,簡言之就是以服務的方式開展閱讀推廣。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閱讀推廣是一種服務受益讀者相對較少,服務成本相對較高的服務。[6]因此,服務型閱讀推廣的主體為政府,或以政府為主體的圖書館等事業機構為主要承載者。其主要經費來源于政府公共財政的配置,包括公益性投入等,其關注的推廣對象和目標人群廣泛,需要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儲備充足。
“流動書包”是典型的服務型閱讀推廣方式。該公益項目由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主辦、成都傳媒集團和成都地鐵公司承辦、成都地鐵傳媒有限公司執行。與此前同樣由政府主導,但需要讀者主動性更強的“地鐵圖書館”相比,“流動書包”可謂是升級版的服務型閱讀推廣,為閱讀推廣對象提供了“被動接受即可實現”的可能,極大降低了讀者的獲知和借閱成本。
“流動書包”項目從2016年10月18日啟動,持續至2017年3月,具體操作方式是典型的服務方式:志愿者每天上午和下午,身著印有活動二維碼的統一T恤,背著裝有數十種書籍、印有地鐵標識的“流動書包”,在成都市的四條地鐵線車廂內走動,供乘客任意挑選。乘客通過掃碼關注“地鐵e號線”,可以在3分鐘內免費借走1本書,并能帶出地鐵站,借閱時間為兩周。
2.社會主導的活動型閱讀推廣模式
活動型閱讀推廣的主要特點是活動,即以大眾媒體為媒介和渠道,開展有計劃、有目的的策劃,制造有社會影響力的閱讀推廣媒介事件,以公眾為目標群體開展閱讀推廣。
一般而言,活動型閱讀推廣的主體是非政府的多元社會主體,由于其在閱讀推廣中所能調動的人力、物力、財力無法與政府相提并論,只能采取“四兩撥千斤”的手法,通過策劃活動來引發關注、引導輿論、形成熱點,從而將推廣對象的閱讀意識、興趣與行動裹挾進來,在活動中形成閱讀認知。
擁有數百萬關注者的文藝自媒體、微信公眾號“新世相”是閱讀推廣活動策劃經驗比較豐富的社會組織,此前已經成功開展過通過社交媒體強關系的“新世相圖書館”讀書活動,因此,2016年11月14日,由其啟動的“丟書大作戰”迅速引發輿論關注,可謂是一次典型的活動型閱讀推廣。
該項目的策劃起自2016年11月4日新浪博主“@英國那些事兒”發送的一條微博,內容是英國女演員艾瑪·沃特森在倫敦地鐵里藏了100本她精心準備的圖書《媽媽和我和媽媽》(Mom & Me & Mom),并在書中附上親自手寫的紙條,通過她的社交賬號號召粉絲們去尋找,引發了“圖書尋寶行動”。僅12天之后,“新世相”就與英國活動方聯系并取得授權,啟動“丟書大作戰”的閱讀推廣活動。
活動開展期間,“新世相”邀請了眾多作家如蔡崇達、李銀河、樂嘉、張曉晗等,眾多明星如黃曉明、徐靜蕾、張靜初等作為“丟書人”,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鐵、順風車等“丟”10 000本圖書。圖書封面上貼有“丟書大作戰”的醒目標志,通過邀請相關人士直播丟書的整個過程,引發粉絲的關注、轉發、評論、點贊與參與。從閱讀推廣效果上來說,這個活動不啻為一次成功的媒介事件。
3.服務型閱讀推廣與活動型閱讀推廣的區別
從三要素角度看,以上兩種閱讀推廣模式有以下三個區別。
第一,推廣主體不同。
服務型閱讀推廣的策劃主體是政府或以政府為核心組建,實施主體、宣傳主體、營銷主體一般由政府工作人員或由政府臨時聘用人員擔當,人力成本和推廣成本基本由政府以公共財政的方式支出。在閱讀推廣中,各環節主體要對政府負責,任務結項由政府或其聘請機構人員核檢。
活動型閱讀推廣的策劃主體是非政府性質的其他社會主體,無權調動社會公共資源,在實施、宣傳和營銷等各個環節主要依靠活動策劃,吸引或聚合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的名人參與,共同引導輿論走向和評價,在活動中尤其注重社會參與度、討論度等指標,在選擇合作方時特別注重其知名度和美譽度等指標,通過為媒體設置議程,間接引發各類傳媒的報道,最終提高閱讀推廣活動的社會參與度。
第二,推廣內容不同。
服務型閱讀推廣的基礎是公益性和非贏利性,圖書來源主要通過政府采買方式實現,由政府“買單”。同時,閱讀推廣的一些隱性開支,如項目工作人員、服務人員或志愿者的基本費用、設備設施等費用也由政府支出,推廣費用比較可觀。在程序運營方面,服務型閱讀推廣強調“方便快捷”與“貼身服務”,比如,“流動書包”首次借閱成功只需3分鐘,即在通勤途中,推廣對象可以享受“遇見、掃碼、選書、借閱、帶走、閱讀、歸還”的全新服務流程。
相比而言,活動型閱讀推廣則要注重成本節約原則,圖書來源多為與出版機構合作,即通過“雙贏式”說服和吸引出版社捐贈部分圖書參與閱讀推廣活動。以“新世相”的“丟書大作戰”活動為例,許多民營出版機構如果麥文化等與之合作,把部分暢銷書作為帶動活動的引爆點,同時加入其他圖書,帶動行人和粉絲關注“丟書大作戰”的活動,引發話題討論,激發閱讀參與熱情。
第三,推廣客體不同。
服務型閱讀推廣的客體是可接觸到此項服務的、有閱讀可能性或至少有閱讀意愿的讀者,著重點在于服務,尤其是“介入式服務”,通過降低獲取圖書的成本開展閱讀推廣。從本質上說,服務型閱讀推廣的關注點依然是傳統借閱關系,只是將雙方的權力關系“反轉”——借閱者在服務過程中處于“權力方”,推廣者則處于“懇請方”,推廣效果的考量標準是有多少客體因主體的服務而愿意實施閱讀行為,至少產生閱讀興趣。
活動型閱讀推廣的客體是因閱讀推廣活動而與閱讀發生關聯的人,尤其是與活動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它不僅包括在具體時空中直接參與閱讀推廣活動的人,還包括在各種媒體平臺上獲得閱讀推廣活動資訊的人,即使不處于具體活動中,也會由于關注此事件的資訊而成為活動的接受或評價與再傳播的載體。活動帶動客體形成的轉發和評價、點贊或因參與帶來的關注度,最終在社會層面達到其影響力。可以說,活動型閱讀推廣的主產品就是社會影響力,至于閱讀本身,則退到次要位置。
三、服務與活動相結合的全民閱讀推廣策略
與居高臨下的閱讀指導、閱讀分享不同,閱讀推廣自帶一抹平權民主的色彩。辯證地看,服務與活動的有機結合,有助于實現二者的優勢互補。
1.活動型閱讀推廣的局限
活動型閱讀推廣以公眾影響力、輿論熱度和話題討論為考評指標,其短板也隨之而來,即因活動本身的特性,很容易被貼上炒作和目光短淺的標簽,讓人感覺是浮于表面的熱鬧與喧嘩,甚至讓推廣對象因對活動的厭惡而產生對閱讀本身的疏離。
以“新世相”開展的“丟書大作戰”活動為例。單純從熱度上來說,在百度搜索輸入“丟書大作戰”,截止到2016年底可得到191萬條相關結果。此活動在“百度指數”30天整體搜索指數和移動搜索指數分別達到1 192和694。PC端搜索峰值出現在2016年11月16日,即活動開展的次日,搜索量為1 917;移動端搜索峰值出現在2016年11月20日,搜索量為3 097。此后兩種搜索量一直處于持續走低,徘徊在300~500之間。
在2016年11月14日至20日為期一周的“丟書大作戰”活動高峰檢索期中,處于搜索上升量較大的關鍵詞的搜索量高達16個,其中與閱讀推廣相關度較高的有“圖書”“簡書”“廣州”“地鐵”“新世相”“新世相圖書館”等,但從相關性看,與“丟書大作戰”活動相關度最強的詞卻是“赫敏”“艾瑪”“尷尬”,由此可見公眾已經看清了其“借勢營銷”的本質。搜索上升度較高的“地鐵”“廣州”“明星”“活動”等,也顯示其社會評價已偏離了“閱讀推廣”這一核心宗旨,與閱讀推廣真正有關的只有搜索上升緩慢甚至處于下降趨勢的“新世相圖書館”“圖書”等關鍵詞。
從歷時性角度看,從2016年11月21日至27日,“丟書大作戰”的相關性搜索就僅剩“新世”(原文如此)“地鐵”“赫敏”“藏書”等,同時添加了搜索上升的詞匯“尷尬”“評論”,且有大量與此無關的“丟了”“丟手絹”等。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4日,除了“赫敏”“新世”“活動”“評論”還處于檢索上升詞外,其他的都處于檢索量下降的情況。可見,活動是短期性的行為,持續力不夠,且與中心詞的距離遙遠。
就反映傳媒對活動開展報道和傳播的“新聞監測指數”來看,高峰出現在活動啟動前后的2016年11月14日至16日,此后就一路下滑。與“丟書大作戰”相關度最高的報道《丟書大作戰遇尷尬,沒人看的被保潔收走》有120條。由此可見,“丟書大作戰”閱讀推廣在傳媒平臺中被標以“尷尬”標簽,對閱讀本身并無正面推動作用,導致活動型閱讀推廣偏離其主旨,推廣后勁和持續力不足。
2.服務型閱讀推廣的局限
正如前文所言,服務型閱讀推廣強調政府主導的服務性、公益性和持續性,以服務意識為著重點,注重維護推廣主體即政府的權威和正面形象,注重避免因不當評價而引發的批評甚至是不同意見,因此比較內斂和低調,形式比較僵化,容易走向“形式主義”。在媒體渠道上,由于政府在傳播口徑等方面仍有一定的把控主動權,因此,服務型閱讀推廣在媒體選擇上仍傾向于選擇傳統媒體或政府自媒體。當然,也因為此類媒體關注人數少、使用黏度低,導致其在社會影響力方面無法與活動型閱讀推廣相提并論。
以成都市委宣傳部主辦的服務型閱讀推廣項目“流動書包”為例,截止到2016年12月16日,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輸入“流動書包”,雖然可以查到163萬條相關結果,但大多數與此項目無關。在“百度指數”上輸入“流動書包”,則數量不足,無法顯示結果,可見其在公眾中的認知度之低。
而來自此項目主辦者的相關數據顯示:“流動書包”活動首月,有超過400種名目的圖書列入此項目,“流動書包”志愿者已經實現書籍發送總量6 984冊次,借書總量6 044冊次,借書比例達87%。[7]
主辦方數據顯示的服務效果,與公眾傳播平臺上的悄無聲息形成鮮明對比,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共識:政府作為全民閱讀推廣主體,放下身段、提供服務、力度較大,卻并未造成一定量級的社會影響,或者說其影響力只局限于區域或內部,未能成為話題,更遑論全民熱點了。
3.活動與服務相結合的閱讀推廣
閱讀推廣既需要積極服務民眾的閱讀生活,也需要將此信息以活動方式推廣到社會中,二者的結合就是活動與服務相結合的閱讀推廣策略。
具體來說,兩種模式的閱讀推廣主體要打破原有觀念局限,將服務與活動相融,用服務深化活動,使推廣項目真正圍繞著“閱讀”這一核心宗旨進行;同時用活動帶動服務,使推廣項目獲得更多的民眾參與和討論。在項目推廣前,兩類主體可以深度合作,在策劃期間就要注意設計容易引發目標讀者群關注的活動,在執行期間,可以借助互動性、參與性與討論性較強的社交媒體,與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名人合作,由此帶動輿論,將閱讀推廣“包裝”成一種具有社會知名度的項目,并在推廣期間,輔之以針對讀者的持續性的服務工作。
[1]孫山. 第十四次國民閱讀調查報告:62.4%成年國民在2016年進行過微信閱讀[N]. 中國青年報,2017-04-20(7).
[2]解艷華.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第十次國民閱讀調查:我國公民閱讀狀況不容樂觀[N]. 人民政協報,2013-05-22(C02).
[3]史蒂文·羅杰·費希爾.閱讀的歷史[M].李瑞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
[4]于文. 出版商的誕生:不確定性與18世紀英國圖書生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6.
[5]范并思. 閱讀推廣為什么[J].公共圖書館,2013(3):4.
[6]范并思.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問題分析[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4(9):4-13.
[7]楊心璐. 地鐵書香 全民閱讀新風潮[N]. 新城快報,2016-1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