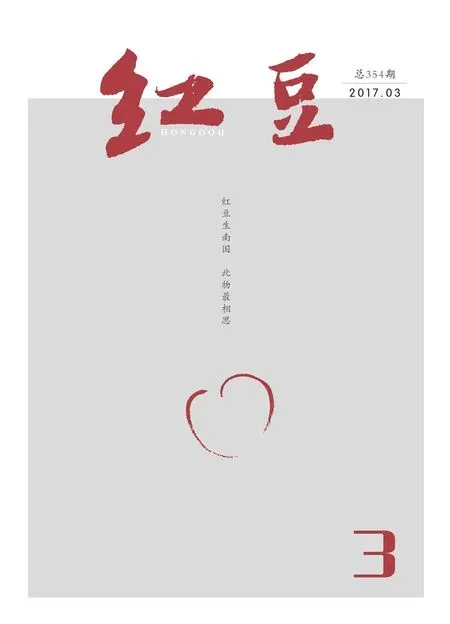一個人的根系
曹文生,1982年生于河南杞縣,現居陜西洛川。作品散見于《散文海外版》《作品》《山西文學》《時代文學》《奔流》《延安文學》《星星詩刊》《河南日報》《華商報》等報刊。
中原記
一個人,是有根的。
如果把中原比喻成一片菜園子,那么父親是菜園子里那個勤勞的耕種者。
他用豫東的風俗,為我們保墑。直到現在,我還無法理解,父親一輩子固守中原的勇氣源自何處。
中原,是父親一個人的圖騰。
他在莊稼里穿越,像一個永不疲倦的夸父。他流汗,他吃苦。他一個人,在生活的夾縫里,喂養三個叛逃的孩子。姐姐去了山東,我去了陜西,留下他,在回憶著我們的童年。
星子是一個坐標。他定位著父親起床的時間,父親是舊式農民,他信仰雞鳴和星子,勝于時鐘。
一個人遠走他鄉,總是用故鄉去丈量一個地方的好壞。我在小城里,總是逃避別人不敬的言辭。河南、中原,總有遭遇一些貶義。
故鄉是一個人的參照物,它映照著遠方的現實。我,父親,都是上面的一個刻度。
鄉村的外部,總是透著荒涼。
一個人總是背著一個概念行走,無論如何努力,我都扔不下它,我的背景,是黃河沖洗過的土地。
在我的意念里,我把故鄉當成一個精神的王朝。我推舉父親為王,我供奉他,朝拜他。
其實,現實生活中的父親,遠非如此高貴,他膽怯而木訥。他沒有出過中原,他面臨新事物,總是一臉茫然。我羞于提起他,害怕別人嘲笑我,我總是將他埋在記憶里。
只能在夜深時,偷著想他,我有一個土氣的尾巴。或者說,我有一個貧瘠的故鄉,那里安放土氣和自卑。
一個人經營文字,就像經營靈魂的棲息地。魯迅的魯鎮,莫言的高密,都是私密的花園。我雖卑微,但我也想構建一座黃金的宮殿,里面有父親高貴的靈魂。
父親不善言談,但煙癮大。煙在鄉村,是一個梯子,總會爬到鄉村的生活里。與煙相遇,便是與父親相遇的最好途徑。我試著抽煙,終于有所小成,但父親看到后,卻戒了煙。我知道,我這一行為,讓他丟掉了30多年的煙齡,我有些慚愧,也在父親的世界里,斷了抽煙的念頭。
父親一輩子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來陜西,那是給我訂婚。我不知道膽小的父親,是否在異地會有些緊張,但是父親站在一片人群里,是那么的另類。他瘦小的身子,刺疼了我。父親老了,老到輕飄如葉。
父親唯一的愛好,就是對著一片莊稼聊天。和人說話,總是危險的。一些人,無事可干,便尋找樂子,善意的,惡意的,都有。木訥老實的父親,總是成為他們的目標。
父親覺得莊稼,比人和善,比人淳樸。它們吃的都是干凈的事物,吃風,吃雨,吃土地。也能吃下,父親那一肚子的嘮叨,無非是兒女走得遠了,咋就那么狠心呢。說著說著,淚就流了下來。
每次和父親外出,他都讓我看著行李,自己一個人買票,一個人買飯。他提著熱飯菜,滿頭大汗地小跑著奔向我。我們蹲在地上,我吃著城市高價的溫暖,他卻吃著從家里帶來的干硬的饅頭。我勸他吃熱的,他說他喜歡干的饅頭,有嚼頭。這騙局漏洞百出,我卻不知怎樣去應對。
進城記
高考失利,預示著我的人生,開始進入另一條死胡同。父親一咬牙,進城。在城市,我所擁有的,只有一床被子,一個蛇皮袋子。
在城市的光鮮里,我和父親是如此寒磣。我穿上最好的衣服,也覺得自己是如此不自信。頭不敢高抬,怕別人的目光燙傷我。
我們蜷縮在工地里,像一條條蚯蚓。只是這蚯蚓被貼上標簽,四川的、河南的、山東的。
我們是看見星星最早的人,城市里的星光,也是我們所獨有的。我們在攪拌機的聲音里,打開城市的門。
一個人在星子里,會懷念故鄉,直到現在,我每看到星光,總是覺得像父親的眼,盯著我。
我害怕熱,害怕被陽光的毒燙傷,那一身的燎泡,是我留給這個城市唯一的記號。一想到城市,我就想起,那紅紅的太陽,像一爐火,烤著我。
在陌生的城市的夜晚,父親抱著廉價酒,一口口喝掉時間。
工地吃飯也需要搶,慢一步,只剩下飯底。搶飯是一門技術活,工地的大鍋里,掌勺的人,一抖手,就是一碗清淡寡水的湯。
我也不知道,父親哪來的本事,總是能在眾多的人里搶得滿滿的一碗干貨。他總是將他的給我,然后一聲不響地喝掉我的湯水。
后來我才知道,是父親用一包黃金葉換來的恩惠。我覺得,人生如此悲涼,為了一碗飯而喪失尊嚴。
夜晚城市的大排檔,是適合我們的地方。那些廉價的飯菜,讓我們認清自己的定位,一個鄉下人,在城市里,是如此低下。
一群年輕人,多半在下班后喝酒,有些醉酒的后生,多半經受不住城市文明進化的透明。年輕人,生理危機了,他們和這一片按摩房里的女人混得火熱。父親緊緊地看著我,生怕我和他們鬼混,被他們帶壞。我無意對這些女人不敬,而是我們這些卑微的流汗者,和她們一樣,是金錢大棒下的附屬物。
有一次,我在外面喝酒,喝到子夜。父親忽然出現在酒館的門前。原來,父親一條街一條街找來。這是一個多么龐大的工程,他猶如一只螞蟻,在城市的空間里,慢慢地蠕動。
當看到我的那一瞬間,他長出一口氣。在這個城市里,我虧欠父親一夜慌亂的腳步。那個夜晚,我們走在這大街上,人很少,出租車也很少。我們在歸來的路上,大聲地唱歌。這個城市,只有此刻屬于我。我們慢慢地走著,走完一條條街道,如同走完了城市文明的一生。
年底我們一次次在城鄉奔波。過年的錢,被工頭扣在手里。
我們群聚在工地上,無非是想鬧出些動靜來,以此恐嚇工頭。哪里知道,他們對于我們的套路,司空見慣。躲起來,不見人。
我們發誓見了他,要暴打一頓。但是見了面,工頭的幾句可憐話,我們又木訥地不知道說什么好,就這樣,一拖三年。
一個工業文明,在拖欠中徹底失去信譽。我在欺騙的謊言里,徹底絕望。
返鄉記
暑假將近,母親在電話里,壓低聲音說,你父親住院了,快回來。盡管母親故作平靜,但是我能感覺到她的世界正在傾塌。
我從洛川,一路到西安,然后又坐高鐵回到鄭州,然后又連夜回到故鄉。
一天時間,我從一個客居的地方,到達另一個地方。路上我經歷著太多的人。火車上,各種方言交織在一起,他們都有一個終點,只是此刻的肉身,都寄存在火車里。在這些遷移的肉體里,我無法破解一些方言的密碼,一些人膽怯地通話,一些人膽怯地回鄉。
當我回到故鄉小城,在醫院里,我看到瘦小的父親,目光有些恐懼。他說,醫生三天不讓他吃飯,他說他餓了。我偷著給他買了份稀飯,只允許他喝幾口。看父親欣慰的笑臉,猶如一個滿足的孩子似的,這時,我才覺得父親比我想象的要弱小。
醫院里到處是遷徙的人,出院、入院,一些家屬,包括我,躲在角落里,呼吸著醫院的濁氣。
在醫院里,我才能看清父親。父親表面的強大,都在機器面前露出原形。那一串串儀式化的病例,讓我吃驚,父親短短幾年,身體已退化到如此地步。
父親的胃,毀于那一年。在工地上,他總是省錢,吃涼饃,喝冷水。一個冬天,父親吃饅頭就咸菜,但是,又扛著凌晨的星子和夜晚的燈光。
我還記得,那首詩,是屬于我的,也是屬于父親的:“當你老了/一個人的前20年,吃著大鍋飯/貧窮和冷。將人生,種在一畝三分地上/長出愛情和三間土房子。/東邊的一間,埋藏著一個人/半生的氣息。耕地、種田,像奴隸一樣/交出屬于他的契約。/我的前半部分,和他的暗影/重疊。如今,頭發如葦草雪白/最硬的那一根,也懼怕變故。/一個人,等待著:平淡與尚好/心里的刺,越來越短,僅剩的那一截/被孤獨覆蓋。/我一直叫他:父親。/ ”
33年了,每一次發音,都感覺我還是個孩子。
看到醫院,我感覺如此隔閡。看別人游刃有余地奔走,我們為一個床位,在醫院里,一天天等待。在城市里,我沒有人脈,不能享受捷徑的樂趣。
對于我們農民而言,進城無非兩件事:看病和打工。看病是慢慢抽干我們的麥子、玉米和棉花。打工也好不到哪里去,是慢慢抽干我們的健康和青春。
我時常覺得自己是故鄉的過客,我是莊稼的過客。誰是誰的主人,好像也說不清楚了。
我想回鄉,守著父母,但是幼兒尚小,需要我照顧。我覺得自己身上有根扁擔,一頭是父親,一頭是兒子,只是自己有私心,總是讓扁擔一再傾斜,讓父親受到冷落。
父親確實老了。我從千里之外回來,看到他那一雙青筋盡顯的手,早已干枯無比。父親的臉,讓我想起羅中立的油畫《父親》,那青銅色的光,是生活敷衍的顏色。
其實,我也有自己的苦衷。參加工作三年,買房結婚,一塊石頭,懸在頭上。我不敢對父親說這些,每次回鄉,都裝作風光無比,其實,我也是遠方小城里的一只緩慢爬行的螞蟻,嘴里還拉著食物。
父親一點點縮小,他只有90斤了,這是多么可怕的數字啊。他人生開始成等差數列,時間、健康。
父親,請原諒我的自私,我會在年關,早點回家,用一把筷子,一串鞭炮,敲開故鄉的門。
父親,請安靜地坐著,等待我敲門的聲音。
干旱記
六月,故鄉大旱。
鄉人,笑聲停滯了,家鄉人被63年一見的干旱籠罩著,玉米的葉子泛黃,干巴地卷起,一點火就能生煙。
豫東平原上的男人,每天守在土地里。望著受難的莊稼,像拷問苦難。老人們守在家里的佛像前,祈求一場透雨。然而一天又一天過去了,玉米的葉子卷得更加厲害,還沒有要下雨的跡象,鄉親們的臉一天比一天地陰著。
土地難以忍受這不見雨點的日子,也張開大口喘息著。
大地滿是龜裂的口子,是向人類述說著目前的困境,還是譴責這不明事理的神靈?我也被今年的大旱弄得心情不寧。
每次給父親打電話,總是從干旱的玉米談起,然后電話那頭,傳來的是父母在田間一次又一次的奔波。他們必須凌晨兩三點就要起來占井,然后將水泵安好,天不亮就開始澆灌。由于土地很饑渴,流水在田間走不動,每一寸土地必須喝飽吃足才肯放流水前行。
那些日子,幾乎天天和父親通話,每一次通話都能聽見父親沉重的嘆息聲。我知道這一聲嘆息,代表著豫東平原上所有莊稼人的心聲。
父親說,這是第四次給莊稼澆水,這次澆的水,不知道能不能安然撐到莊稼成熟。我也不知道怎樣安慰父親,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遙遠的地方,為家鄉默默地祈禱求雨。
那天夜里12時,我剛睡下,電話就響了起來。一看是父親的電話,我慌忙接起,電話那邊父親的聲音有些顫抖,我心想父親這是怎么了。“小,家里下雨了,你聽這拍打窗戶的雨聲音!”
我聽見一陣急促的雨聲,我想也許此刻的父親定是將電話靜靜地放在窗戶上,讓電話另一端的我,傾聽雨水拍打窗戶的聲響。我聽到豫東平原落雨了,心里樂開了花。
那天父親的話特別多,我記得那是父親話說得最多的一次,往常的他,只是在電話那頭靜靜地聽,等我把話說完了,就嗯一聲掛了。然而此刻的我們,在雨水的滂沱中開始了交流,我們的心突然開了、亮了,電話那頭的父親興奮得像一個孩子,我暗自揣摩,是什么樣的事情,才能讓一個60多歲的老人這么興奮。是雨水,這干旱之后救命的雨水。
玉米是豫東平原上一片站立的生靈,他們經歷了一次次死亡的折磨,然而此刻卻堅韌地活著。
河南這個多難之地,經受住了災年,并且在莊稼人日夜關注的目光下,能再一次聽到夏夜暴雨的聲音,是多么可喜啊!
這個夏天,唯一留給我們的,可能就是這場難得一見的干旱。除此之外,我還見證了父親那執著的心,這是一種精神,包含著苦難與欣喜的體驗。
此刻,在異地的我,仿佛看到秋天農家小院里那黃澄澄豐收的圖景;我仿佛看到了冬季白雪下一家人躲在爐火旁,將玉米剝成粒,然后裝進了囤里;我仿佛看到,豫東平原被一片煙花爆竹,修飾過的新年。
責任編輯 寧炳南
特邀編輯 張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