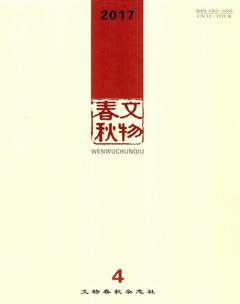齊白石與《吳昌碩花卉屏條》
徐志慧
[關鍵詞]《吳昌碩花卉屏條》;吳昌碩;齊白石
[摘要]《吳昌碩花卉屏條》為天津市文物公司舊藏,圖繪初秋小景,落款“老缶·昌碩”,鈐“缶翁”“蒼石”二印,故定名,后被吳昌碩研究專家邢捷鑒定為贗品。文章通過對《吳昌碩花卉屏條》落款書法、繪畫技法和印章等的辨析,認為這幅作品的真正作者應是齊白石。
吳昌碩(1844-1927),浙江安吉人。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又署倉石、蒼石,號缶廬、老缶、蒼石、苦鐵、大聾、石尊者等,壬子年(1912)后以字行。晚清民國海派書畫的代表人物,以篆籀之筆入畫,尤工花卉,近學任伯年、張孟皋,遠法陳淳、八大,筆酣墨飽,氣勢磅礴。他與任伯年、趙之謙、虛谷齊名,合稱“海派四大家”。其詩書畫印四藝精絕,享譽海內外,對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書畫篆刻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
《吳昌碩花卉屏條》(圖一)為天津市文物公司舊藏,紙本設色,縱147厘米,橫39厘米。圖繪初秋小景,一叢盛開的紅菊,一株花開正茂、枝葉紛披的向日葵。左上題詩“笑爾有心終向日,東籬誰可戰秋風”,落款“老缶昌碩并記”,款下鈐二印“缶翁”“蒼石”。在筆者參加的一次吳昌碩書畫鑒定公開課上,這幅作品被吳昌碩研究專家邢捷先生鑒定為贗品。筆者通過對其落款書法、繪畫技法及印章的考證,認為這幅作品的真正作者應是齊白石。下面略陳己見,還請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一、《吳昌碩花卉屏條》非吳昌碩真跡
首先,《吳昌碩花卉屏條》的落款書法非吳昌碩真筆。“老缶昌碩”是吳昌碩晚年常用落款。吳昌碩有一方閑章:“吳昌碩壬子歲以字行”,“壬子歲”即1912年,也就是說吳昌碩在1912年、時年69歲時始棄“吳俊卿”款識,改用“吳昌碩”落款。同時,就筆者所收集到的材料來看,吳昌碩“老缶”落款最早m現在癸丑年(1913)的《潑墨荷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最晚見于丁卯年(1927)的《花鳥山水冊》(中國美術館藏)。據此推斷,《吳昌碩花卉屏條》應該是1913至1927年間的作品,這一時期屬吳昌碩晚年,其書風是把篆籀與行書熔于一爐,以長鋒羊毫運筆,中宮緊縮,體勢左低右高,筆畫肥瘦互現,姿態奇倔險峻,氣韻蒼辣遒勁。而《吳昌碩花卉屏條》的落款(圖二,1)結體中宮松弛,枯筆側鋒較多,缺乏吳昌碩筆法中肥瘦互現、錯落有致、富有節奏感的律動,雖然竭力模仿吳昌碩的書風,體勢左低右高,字形略有相像,但無吳昌碩晚年人書俱老的斬絕與豪邁。特別是“缶”字,呈縱向的長方形,最后收筆為一橫點,這種寫法在吳昌碩的親筆書法里是找不到的。吳昌碩親筆“缶”字都是呈橫向的扁方形,且末筆是以一豎點來完成的,如作于1915年的《贈少墨集明拓石鼓文字聯》落款(圖三,1)、1918年的《根潔葉香》落款(圖三,2)。因此,我們說《吳昌碩花卉屏條》的書法不符合吳昌碩的用筆習慣,非吳昌碩親筆。
其次,從繪畫技法看,《吳昌碩花卉屏條》非吳昌碩真筆。菊花是吳昌碩作品中的常見題材,一般有三種面貌:一種是勾瓣菊花,如《墨菊圖軸》(中國美術館藏,1923年),中鋒運筆,兩筆勾菊瓣,淡墨點染;一種是點瓣菊花,如《東籬佳色》(天津文物2009年秋季競買會第26號,天津市文物公司舊藏,1918年),先用花青直接點寫花瓣,再以墨色調和花青二次復筆;第三種則是兩種面貌的結合,如《菊石圖》(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1919年),黃菊用勾瓣,紅菊用點瓣法。無論哪種面貌,都是以臨寫石鼓文的筆法入畫,筆墨圓厚飽滿,線條蒼礪古拙,畫面樸茂磅礴,金石氣十足,充滿滄桑感,這也是吳昌碩繪畫的精華所在。此《吳昌碩花卉屏條》的菊花則是以淡色胭脂點寫花瓣,再用深色胭脂勾勒輪廓,其筆法中多用側鋒,與上述三種面貌皆不同。
另外,由于目前尚未發現吳昌碩向日葵題材的其他作品,該《吳昌碩花卉屏條》中向日葵的畫法只能參照《東籬佳色》中菊花畫法進行比較:從用筆來看,線條扁平,不夠渾圓,欠缺吳昌碩筆法中特有的金石氣;花瓣的層次布置,陰陽向背的安排,簡單稚拙,整體畫面較為平淡,不具備吳昌碩樸厚蒼茫的風貌。
最后,從印章來說,《吳昌碩花卉屏條》中“蒼石”“缶翁”二印(圖二,2、3)與《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缶廬印存初編》二書中收錄的吳昌碩印文不符。《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中收錄的“蒼石”印文(圖四,1)結體頎長,布局上嚴下疏,刀法上沖切并用,刀拙而鋒銳,方圓互用,橫豎之筆多平直,轉折處又多圓意;“蒼”字捺筆尖而出鋒,巧藏于拙;印邊右上有倭角,上下寬厚,左右細薄,多沖崩,增加了印文的滄桑感。《缶廬印存初集》“蒼石”161印文結體布局幾乎與《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中的印文相同,倭角、沖崩多有相似之處,只是刀痕更鈍,筆畫更加敦厚,無尖銳之筆。而《吳昌碩花卉屏條》中“蒼石”印文(圖二,2)結體方正,中宮略弛,藏鋒用刀,刀痕圓轉,僅“蒼”字的“口”部右下見方筆,印邊寬厚,右下略有倭角,少有沖崩;“石”字的“丿”筆幾乎與印邊相連,導致布白不足,略有氣滯之感。《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中兩方“缶翁”印文(圖四,2、3)布局較滿,結體瘦長,重心偏上;“缶”字布局呈“風”字形,下部外撇,“翁”字的“公”部布置緊結,體態平扁,“羽”部疏放,刀痕粗細相近。邊緣用切刀法,崩沖不平。《吳昌碩花卉屏條》的“缶翁”印文(圖二,3)則結體疏闊,重心居中,“缶”字方正,無外撇;刀痕粗細肥瘦變化較大,收刀處呈細收狀,突出印文的書法性,但略顯拘謹;邊緣平滑,稍有沖口。由此可見,《吳昌碩花卉屏條》中的“蒼石”“缶翁”二印與吳昌碩印文結體緊結、上嚴下疏的敦茂樸厚風格并不相合。
綜上,《吳昌碩花卉屏條》無論書法、繪畫、印章都與吳昌碩風格相去甚遠,因而并非吳昌碩真跡。
二、《吳昌碩花卉屏條》的作者應為齊白石
齊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原名純芝,字渭清,號蘭亭。后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山人、木居士、寄萍堂主人、杏子塢老民、借山吟館主者、三百石印富翁、齊大等。早年為木工,后學畫,由肖像畫及《芥子園畫譜》人手,拜胡沁園、陳少蕃、王闿運為師學習詩文,習工筆草蟲。后學八大、金農等,畫風古拙冷逸。1919年定居北京,結識李筠庵、陳師曾等人,受陳師曾指導開始學習吳昌碩的書法繪畫及篆刻風格,進行“衰年變法”,放棄徐渭、八大一路冷逸畫風,形成熱烈明快、渾樸稚拙的風格,開創紅花墨葉一派。同時,書法由學何紹基、金農,轉習二爨、李北海、吳昌碩,繼而自創白石體。篆刻也由丁敬、黃易、趙之謙人《祀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并將吳昌碩篆刻中的單刀法發揚光大,成自我風格。1922年,因陳師曾攜其作品參加日本東京舉辦的“第二回中日繪畫聯合展覽”而成名。齊白石與吳昌碩有“南北二石”之稱,與張大干有“南張北齊”之名。筆者從款識、繪畫和印章等角度,斷定《吳昌碩花卉屏條》為齊白石1919年定居北京、學習吳昌碩開始“衰年變法”后的作品。
首先,《吳昌碩花卉屏條》的落款雖竭盡全力模仿吳昌碩的風格,但“笑”“老缶”“并記”等字流露出齊白石60歲左右時的書法特點:總體運筆速度較慢,頓錯感強,講究筆筆送到。尤其是“缶”字的寫法,非常有特點,最后的收筆為一橫點,而非一豎。這種寫法在吳昌碩的親筆書法中找不到,在齊白石的作品中卻發現不少。如《梅花》(胡佩衡藏,約1928年)、《紅梅》(北京畫院藏,約1928年)、《行書》(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1929年)、《白石詩草(庚午至壬申)·自嘲》(北京畫院藏)這些作品落款中的“缶”字都作異形。另外,《行書》(湖南省博物館藏,1924年)、《仙鶴》(霍宗杰藏,1928年)、《葡萄》(北京畫院藏)[姍、《鐘馗》(北京畫院藏)]等落款中“搖”字的“釘”部亦均作異形。《秋蟲圖》(長沙市博物館藏,約1912-1916年)中“匋”字的“缶”部也作異形。綜上,齊白石作品中“缶”字異形寫法基本出現于1912至1932年間,這與《吳昌碩花卉屏條》仿晚年吳昌碩時間相合。吳昌碩的晚年風格正是以1913年為界,直至1927年。“缶”字異形寫法為什么只是階段性的呢?應是齊白石作偽吳昌碩作品時故意留下破綻,留待有緣人破譯,這也是古玩行的一個潛規則或者說傳統。
其次,《吳昌碩花卉屏條》的畫法呈現出齊白石平淡天真、樸實自然的風格。向日葵莖干的畫法與齊白石1919年《蔬果花鳥屏》(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藏)中《甘貧》《廉直》中芋梗、荷梗的畫法幾乎一致,由上至下一筆寫出,帶飛白,底部略有復筆。向日葵花瓣畫法則和齊白石1920年《菊花》(北京榮寶齋藏)的花瓣一致,用直接點瓣法,一筆畫一瓣,不用墨線勾輪廓筋脈。這種畫法盡管源自吳昌碩(如《東籬佳色》),卻無吳昌碩浸淫石鼓文多年的金石之氣,而有齊白石的質樸和稚拙,呈現的是齊白石衰年變法時期學習吳昌碩畫法的探索性。
最后,印文是齊白石私淑吳昌碩的典型。吳昌碩是以石鼓文人篆刻,他曾對弟子諸樂三說:“寫字頂要緊,寫字主要是學篆,篆不好,印怎能刻的好呢?”齊白石則以刀代筆,以《祀三公山碑》《天發神讖碑》做印法,以書法虛實為印法黑白。《吳昌碩花卉屏條》所鈐“蒼石”“缶翁”兩方印章與吳昌碩印形近質殊,即學習吳昌碩的鈍刀法和樸茂磅礴的篆刻風格,呈現的卻是齊白石60歲左右平易與淡然的篆刻特點:結體寬弛,重心居中,運刀緩慢,線條平和,透著生稚之氣。
三、齊白石作偽吳昌碩的可能性
在上文中,我們主要通過作品比較的方法,從書風、畫風、印風的角度將《吳昌碩花卉屏條》的作者初步判斷為齊白石。接下來,筆者將通過各種零散的資料去論述齊白石作偽吳昌碩的可能性。
1.齊白石曾經努力地學習吳昌碩的畫法。齊白石聽從陳師曾建議放棄冷逸畫風,自創風格,開紅花墨葉一派,其實學的就是吳昌碩熱情濃烈的畫風。胡佩衡回憶說:“據我知道,他一直崇拜吳昌碩,只要見到他的精品就要買下來或者借來學習。”“記得當時我看到他對著吳昌碩的作品,仔細玩味,之后,想了畫,畫了想,一稿可以畫幾張。畫后并且征求朋友們的意見,有時要陳師曾和我說,究竟哪張好,好在哪里,哪張壞,壞在什么地方,甚至還講出哪筆好,哪筆壞的道理來。”啟功先生也在回憶齊白石晚年時道:“齊先生最佩服吳昌碩先生,一次屋內墻上用圓圖釘釘著一張吳昌碩的小幅,畫的是紫藤花。齊先生跨車胡同住宅的正房有一道屏風門,門外是一個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時正在開花。先生指著墻上的畫說:‘你看,哪里是他畫的像葡萄藤(先生稱紫藤為葡萄藤,大約是先生家鄉的話),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啊!姑且不管葡萄藤與畫誰像誰,但可見到齊先生對吳昌碩是如何的推重的。”
2.齊白石親筆承認曾經給人“代筆”,并且不止一次。所謂的“代筆”不過是齊白石對自己作偽的一種隱晦的說法,其1919年所作《梅花圖》(廣州市美術館藏)就是他作偽的最好例證。《梅花圖》題記(一):“如此穿枝出干,金冬心不能為也。齊瀕生再看題記。后來者自知余言不妄耳。”題記(二):“此幅本友人強余代筆之作。故幅左已書再觀題記。并蓋白石曾觀之印。乃余自惜年老,不忍以精神如黃金擲于虛牝。吉皆兄深知余意,勸余添加款識,仍為己作。余感吉翁之憐余,因贈之。惜吉翁僅能見此一幅也。”首先,齊白石用“強”字表達了作偽并非心甘情愿。其次,以“如黃金擲于虛牝”抒發了對自己英雄無用武之地,虛度時間、浪費精力的無奈和感慨。最后,以“惜吉翁僅能見此一幅也”暗示自己曾不止一次作偽。這兩條題記明確地記載了齊白石不僅多次作偽畫作,而且還在其作偽品上書寫品鑒意見。
3.齊白石1919年的收入與賣畫情況并不相稱。齊白石最早的潤格是1902年樊樊山給他定的篆刻潤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㈣這張潤格在其遠游十年中一直使用。1920年歲末吳昌碩為他定潤格:“石印每字二元,整張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過八尺另議,屏條視整減半,山水加倍,工致畫另議。冊頁每件6元,紈折扇同,手卷面議。”齊白石曾這樣描述吳昌碩為其定潤格之前的鬻畫生涯:“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來到北京,賣畫刻印,生涯并不好,當時物價低廉,勉強可以維持生活……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0),我五十八歲……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我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來問津,生涯落寞得很。”《齊白石全集·第2卷》之《秋生圖》邊跋也說:“盧江呂大贈余高麗陳年紙,裁下破爛六小條。燈下一揮即成六小屏,倩廠肆清秘閣主人裱褙裱成為(為字后圈掉),南湖見之喜,清秘閣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為不值一錢,南湖以為一幅百金。時流誰何能畫?余感南湖知畫,補記之。璜。”這段題跋也收錄在《己未日記》之中。《秋生圖》的尺寸是縱52厘米,橫16.8厘米,如此六屏,僅賣十元,可見當時齊白石畫價之低。齊白石《己未日記》記載,他收入的錢,都交好友楊度收存:“民國八年七月五日收瀕生交來洋五百元。七月五日收瀕生交來洋叁百元,七月九日收瀕生交來洋貳百元,七月十四收瀕生交來洋壹百元。”閏七月及八、九月,又存楊度處七次約計八百元。白石在九月初九記:“此約楊虎公處二千二百元,后去數筆無細數。”日記所記收入與齊白石自述的賣畫刻印情況及潤格并不相符,這些巨額收入的來源恐怕只有作偽可解釋了。
4.齊白石所作偽品的銷售途徑。齊白石在《癸卯日記》中曾述結識李筠庵,并與其交往頻繁,有時一日之內多封書信交流。“得李筠廣書(并索石印四)。”“嗣元與筠廣來北萍居,相與盡談。”“筠庵來,偕游廠肆。”“筠庵來書,相請一談。即去,得觀畫冊數本……燈下得筠安書,今日與筠廣書二。”“得筠庵書索畫,晚間附書送畫去。”李筠庵曾與張大千仿制古畫,并做了許多石濤的贗品,多次騙過程霖生、陣半丁等人。“廿四日平明使人與筠廣假大滌子畫。”這段文字隱晦地說明齊白石也參與了李筠庵仿制石濤贗品的活動。由此可推,齊白石很可能是與李筠庵合作,作偽的作品是通過李筠庵出售的。
通過以上幾點,筆者判斷齊白石作偽吳昌碩作品是成立的,天津市文物公司舊藏《吳昌碩花卉屏條》的真正作者應為齊白石。四、齊白石偽吳昌碩《花卉屏條》的創作年代
從目鑒的角度來看,齊白石偽吳昌碩《花卉屏條》的紙張為民國時期手工生宣,與機制紙張和現代手工生宣相比,由于青檀皮的纖維搗制工具不同,其纖維更長,分布不是十分均勻,紋路細密,韌性強勁,觸感綿柔;其裝池所用花綾絲質圓厚飽滿,編織緊密,柔韌性強;天桿堅密結實,有泥鰍背之感;地桿以萬字錦為飾;同時,整張畫展開后手感輕薄而堅實,搖在手里響聲清脆,而無悶聲;畫面和裱工都呈現出一種微黃且柔亮的包漿,這些都是民國時期裝裱的特點,說明該《花卉屏條》是民國時期的作品。
另外,上文提到此畫是作偽吳昌碩壬子年(1912)以后的作品,以及吳昌碩的“老缶”落款最早出現在1913年,又據齊白石“缶”字異形寫法的時間是1912-1932年左右,向日葵、菊花的畫法則在1919-1920年左右,那么可推知其繪制時間的上限應為1919年左右。1922年,陳師曾帶齊白石畫作參加日本畫展,經此展覽,齊白石的“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也就不需要作偽他人了。因此,齊白石偽吳昌碩《花卉屏條》繪制下限不超過1922年,時間約為1919至1922年間。
綜上所述,天津市文物公司舊藏《吳昌碩花卉屏條》的作者應為齊白石。該圖在某種程度上還原了齊白石尚未成名時在北京的賣畫生涯,解釋了吳昌碩沒有收齊白石為徒,并出言譏諷“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的原因,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齊白石經由私淑吳昌碩,結合時代潮流,變化出自我風格,最終成為一代大匠的不懈努力和魄力。
[責任編輯:谷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