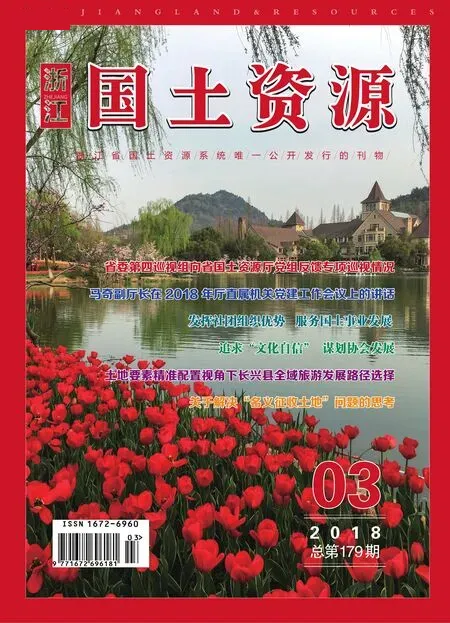關于解決“名義征收土地”問題的思考
□ 嘉興市國土資源局 沃 云
本文所討論的名義征收土地,主要指的是歷年來已經完成對農民的房屋拆遷、土地補償和社會保障等政策處理,但尚未得到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的土地。
一、名義征收土地的成因
其實,名義征收土地在表現形式上由來已久,也是改革開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發展理念的改變,留下了很多“后遺癥”。究其原因,多為三個方面因素疊加而致。
1.主觀上,政府為了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需要
在構筑“大招商、大建設、大平臺”的這種大環境下,為了拓展發展平臺,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在城市規劃區內、工業區內大面積實施農房拆遷和名義征收土地,有的縣(市、區)政府還給各鎮(街道)下達年度農房拆遷、名義征收土地的任務,并將此任務列為鎮(街道)工作考核的內容。
2.客觀上,具體項目報批的需要
很多時候省里下達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和要求上報項目審批的時間太緊,而征地報批前“告知、聽證、確認”的程序時間較長,且有不確定因素,這勢必要提前與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進行名義征收土地等政策處理。
3.農民的普遍要求
由于嘉興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政策、農房拆遷政策對農民極具吸引力,有項目征地時,村、組會提出帶征要求,甚至會提出整組帶征。2003年以后按項目紅線征地事實上已很難做到。
同時,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和集體土地流轉政策試點的全面推廣,各級政府也借力推進城市化的進程,所以農房拆遷、名義征收土地的現象越來越多。
二、名義征收的土地給報批帶來的影響
名義征收的土地尚未得到批準,在法律概念上仍屬于農村集體土地,一旦落實項目、落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后,名義征收的土地就需要上報審批,但仍要按照征地的程序組織材料和編制方案,完成報批手續。由此會帶來一些問題。
1.程序不合規定
名義征收的土地報批時,批前“告知、聽證、確認”程序無法公開落實,很多時候只能形式上到位或做技術上的處理,和村干部一起完成報批材料。有違“征地陽光工程建設”的精神和五公開制度,存在著失職、瀆職的風險。
2.在征地補償方面容易產生糾紛
名義征收土地報批時,如果征地政策作了調整,或者被征地農民知曉之前名義征收的土地尚未得到批準,他們會提出要求,按土地批準的時間節點重新進行政策處理。雖然,政府在農房拆遷、名義征收土地過程中,沉淀了大量的資金,使大部分的農民得到了利益和提前享受了政策待遇,但也有一小部分農民因為年齡的問題利益受損,在征地補償上問題較小,但在社保安置上對這批人有些影響,因為嘉興的社會保障政策是,從16周歲起,按農齡購買社會保障,最高15年。具體地說:不同年齡的人在繳納社保年限和享受安置標準上是不同的。如果是二級區片,利益矛盾會更大,反響會更強烈。
3.土地面積、權屬模糊不清
名義征收的土地在落實具體項目用地前,一般都由鎮(街道)或開發主體在管理、發包、流轉,原有的自然地理分界已打破,按現在征地報批的要求,在對報批地塊進行土地面積、地類、地面附著物及其權屬等進行征地調查確認時,會發現或因土地現狀發生改變,現場調查成果難以與名義征收土地時的補償、安置情況相對應。
4.村民代表會議無法召開
一是村里無法開,怕村民知道名義征收的土地原來還沒有得到批準,當初的征地是缺乏依據的。利益受損的人會要求重新進行補償、重新計算社保繳費年限,容易引發社會不穩定。二是有的村已提前撤村建居,村集體資產也已全部亮化分配,農民拆遷后分散在各個社區,原村干部也各自就業,很難再召集開會,就連原村里的公章也由街道(社區)代管,保管公章的人對地征政策又不了解,且與被征地的村毫無關系,造成推諉扯皮尷尬的局面。
5.土地征收公告無法公開張貼
一般,名義征收土地時的補償標準低,實際項目落實報批時的補償標準可能提高了,政府會顧慮兩個補償標準差異無法公開張貼《土地征收公告》。

▲ 名義征收后的土地目前已流轉用于農業生產
6.征地補償費用無法再落實到被征地村,尤其是撤村建居的村
因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帳戶已被注消,實際征地時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的《征收補償協議》的費用無法支付兌現,也就是說征地補償無法完全履行到位。
三、如何解決名義征收土地問題
名義征收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穩定埋下了安全隱患,一旦處理不好,會引起信訪、上訪,甚至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影響社會穩定。因此,應叫停名義征收土地行為。嘉興市政府在2014年就發文明確了“各類開發主體、鄉鎮工業區凡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沒有落實具體建設項目,沒有落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嚴禁以各類名義對農村集體土地實施名義征收土地等政策處理,近幾年來這種行為得到了明顯有效的扼制。對之前存在的名義征收土地問題的解決筆者有如下建議。
1.做好調查摸底
對之前名義征收的土地要及時進行調查摸底、清理登記,確定四至范圍,并保存好相關補償安置的材料和支付憑證以及被安置人員清單。同時要加強監管,各征地主體要與被征地村進行協商、溝通、明確監管責任,及時對這些土地進行發包、流轉用于農業生產經營,不得拋荒,不得改變原土地用途,更不得進行違法建筑。
2.實行總量控制
對名義征收的土地要實行總量控制,逐步消化,項目經過批準且已落實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原則上不得再征收新的農村集體土地,要在名義征收的土地上落地,征地程序按規定做到位,要嚴格履行征地前“告知、確認、聽證”、批后政府公告等程序和“五公開”制度的落實。
3.謹慎對待批后土地政策處理問題
名義征收的土地經批準后,是否要按批準的時間節點進行政策重新處理,有兩點建議。
一是以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為原則,不宜再重新處理。名義征收的土地,大多數是先實施農房拆遷,然后對其承包的土地按當時的征地政策進行補償,把被拆遷人視作為被征地農民,按規定給予社會保障安置,統一進入社會保障籠子。嘉政辦發〔2002〕44號文件,明確了拆遷農戶家庭人口全部“農轉非”,由市社會保障部門按規定統一進行安置,因此是符合政策的。此外,在當初征地拆遷也是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的有效途徑之一,況且嘉興征地拆遷的政策相當優惠,絕大多數的農戶是受益者,很多提前享受了社會保障和就業政策,因此符合農民意愿。
二是從依法依規、從維護被征地農民合法權益的角度,對名義征收的土地待批準后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征地補償標準調高的這部分,可以直接支付。社會保障安置對象這部分,很難再落實到具體哪個人。(當初是一個村或一個組同時進行政策處理、同時上報人員名單進行安置的,這幾年雖然有部分土地已批準征收,也能夠按人均農用地計算出需安置的人數,但在實際操作中無法確定具體安置是哪個人)。因為不同年齡的人繳納社保年限和享受安置標準是不一樣的。化解這個難題是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名義征收的土地經批準后,按批準的時間節點測算出人均社保安置費用,然后與名義征收土地的時間節點的人均社保安置費用進行比較,超出部分應支付給被征地村集體經濟組織,由集體經濟組織按規定進行量化和分配,批準多少面積,落實多少面積。
將按照批準的時間節點繳納社會保障金標準與提前政策處理時間節點繳納的標準進行比較,按照平均每人交納多少年和人均農用地進行計算,超出部分支付給被征地村集體經濟組織。
四、結論
名義征收土地的問題遠比本文所涉及的內容要復雜得多,解決起來相當困難的。這里,筆者嘗試以依法依規、保護權益、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為原則,提出幾點建議性疏解路徑,權作拋磚引玉。名義征收土地的問題,是不應該被忽視的,要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應及早提上議事日程研究解決。同時,也呼吁廣大學者、專家、法律工作者獻計獻策,為保護好從事征地工作的人員安全和保護好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