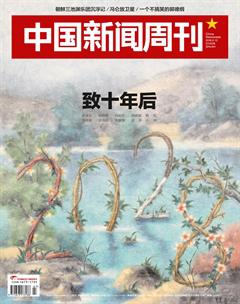中國(guó)文化再出發(fā)
許倬云
討論中國(guó)目前面臨的重要問(wèn)題,這個(gè)使命的框架不應(yīng)局限于眼前正在發(fā)生的一切,而應(yīng)涉及長(zhǎng)久的發(fā)展。因而,我想討論中國(guó)今天和未來(lái)文化發(fā)展應(yīng)有的方向,這個(gè)話題涵蓋的時(shí)間跨度就不只是十年而已了,而應(yīng)是一個(gè)超越世代的重大重建工作。
作為居住在美國(guó)的華人,我既已將他鄉(xiāng)做故鄉(xiāng),國(guó)人或認(rèn)為我已沒(méi)有資格、也沒(méi)有立場(chǎng)討論中國(guó)事務(wù)。可是,作為一名遠(yuǎn)離家鄉(xiāng)的游子,雖然在別處已成家立業(yè),但午夜夢(mèng)回,仍是故國(guó)山水、親友故舊。游子之于舊日家園的興衰禍福,常有切膚之感。
我的專業(yè)是歷史,兼跨人文和社會(huì)兩個(gè)學(xué)科的范圍。我所關(guān)心的事物,也因此既有每個(gè)“人”內(nèi)心的安身立命,也有“人”與群體的關(guān)系。在我心目中,復(fù)雜群體例如國(guó)家,相當(dāng)于軀干;族群歸屬,相當(dāng)于肌膚;經(jīng)濟(jì)流通,相當(dāng)于血液;社會(huì)脈絡(luò),相當(dāng)于神經(jīng);而文化,對(duì)群體而言,則相當(dāng)于人的思想和精神。
這幾個(gè)方面互相依托,不能分離,而人之精神所在與行為準(zhǔn)則,以及思考方式,都是在文化范疇之內(nèi)——這也是我挑選文化發(fā)展方向作為談?wù)撐磥?lái)十年這個(gè)話題的原因。
今日的中國(guó),硬件建設(shè)發(fā)展之迅速眾所周知;而且這一領(lǐng)域的問(wèn)題,我也沒(méi)有置喙的資格。今天重建中國(guó)的事業(yè),亟需補(bǔ)足的部分卻應(yīng)在文化建設(shè),亦即如何充實(shí)硬件軀殼當(dāng)中的靈魂——前述中的思想和精神。
中國(guó)文化的發(fā)展,自春秋戰(zhàn)國(guó)、百家爭(zhēng)鳴,經(jīng)過(guò)數(shù)百年諸家融合,在西漢已組成了中國(guó)文化的體系,具有自己的特色。董仲舒規(guī)劃的“天人感應(yīng)”, 和《易經(jīng)》所表現(xiàn)的“變化的原則是不變”,結(jié)合為一。這個(gè)體系,乃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網(wǎng)絡(luò),其中有各種元素互動(dòng)的趨衡狀態(tài),也有二元互動(dòng)的辯證關(guān)系。這個(gè)網(wǎng)絡(luò)有很多層次,最外層是宇宙,最內(nèi)層是個(gè)人以及身體內(nèi)部各器官之間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間經(jīng)常變化,不會(huì)固定,也不應(yīng)固定。如此動(dòng)態(tài)的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在古代以至于中世代是中國(guó)特有的宇宙論。最近,拙著《中國(guó)人的精神生活》之問(wèn)世,就是論述仍淀集于中國(guó)人生活中的文化與行為模式,也許可與此處所論互相參考。
在古代印度多神信仰中人神之間的混雜,以及在印度發(fā)展的佛教,對(duì)于變化的認(rèn)識(shí)傾向于接受宿命,悲觀而消極。而在歐洲發(fā)展成主流的獨(dú)神信仰中,神是一切的主宰,人并不能參與獨(dú)一真神之下的大系統(tǒng),而只能服從。由于獨(dú)一真神主宰一切的特點(diǎn),固定的秩序或變化的趨衡都由神的意志決定,人是被動(dòng)的。古代中亞近東的波斯信仰系統(tǒng),是一個(gè)二元對(duì)立的世界。二元之間永遠(yuǎn)進(jìn)行著“正、反、合”的辯證變化,其第三個(gè)時(shí)期乃是斗爭(zhēng)之后的解脫。
以當(dāng)時(shí)這三大系統(tǒng)與中國(guó)對(duì)比,中國(guó)的系統(tǒng)是以人為主體的、多層次而多元的大網(wǎng)絡(luò),一層一層都是從個(gè)人向外輻射。在這個(gè)結(jié)構(gòu)下,“人”具有非常尊貴的地位,也正因?yàn)槊總€(gè)人都處于軸心位置,“個(gè)人”負(fù)擔(dān)了無(wú)窮的責(zé)任——對(duì)自己的所作所為負(fù)責(zé)任,也對(duì)群體因此而發(fā)生的變化負(fù)責(zé)任。人為貴,但是人不能妄為。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guān)系,固然是很重要的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也是息息相關(guān)。
如此文化網(wǎng)絡(luò)應(yīng)是開(kāi)放的,可不斷接受外來(lái)的刺激,加以修正、容納以至于消化。外來(lái)因素只是在多元之中增加更多的選擇而已。“海納百川”,由各方河川帶來(lái)的不同土壤和養(yǎng)分,大海不會(huì)深閉固拒。對(duì)內(nèi)而言,吸收了外來(lái)因素之后,這一龐大的多元互動(dòng)系統(tǒng)內(nèi)涵更豐富,變動(dòng)的選擇也更有彈性。因此,中國(guó)特殊的文化體系,可以不斷因?yàn)橥鈦?lái)刺激而自我調(diào)整。
漢代以后、中古時(shí)期、魏晉南北朝和唐代,是中國(guó)吸納許多外來(lái)因素予以綜合的階段。外來(lái)的佛教、祆教、基督教等都進(jìn)入中國(guó),分別被中國(guó)所吸收。在印度沒(méi)有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佛教,在中國(guó)卻是開(kāi)花結(jié)果,直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信眾群還是中國(guó)人。北方草原的胡人甲士曾經(jīng)占領(lǐng)大片中國(guó)土地。北方農(nóng)村中的漢人則以塢堡自衛(wèi),保留中國(guó)的文化;南方的漢族也帶著中原文化,與中國(guó)南方的土著融合。佛教的內(nèi)修和波斯系統(tǒng)的救贖觀念,都被中國(guó)文化系統(tǒng)接納,成為民間信仰的一部分。隋唐帝國(guó)的擴(kuò)張本身就是一個(gè)胡漢融合的過(guò)程,發(fā)展為多姿多彩的盛唐。中國(guó)文化隨之輻射于東亞,也使這個(gè)文化體系的特色,傳布于亞太地區(qū)。
宋代的中國(guó),過(guò)去隋唐帝國(guó)的大片領(lǐng)土都已不屬漢人政權(quán)管轄,宋代的國(guó)家組織有了新的設(shè)計(jì):建立在胡人后裔(亦即五代的沙陀軍團(tuán))武力基礎(chǔ)上的皇權(quán),和建立在中國(guó)文化基礎(chǔ)上的儒生官僚彼此合作。官僚體系屈服于皇權(quán)之下,而掌握文化發(fā)言權(quán)的儒生們則致力于重建一個(gè)文化秩序。
宋代的道學(xué)與理學(xué),實(shí)際上將前述具有強(qiáng)大彈性的民間系統(tǒng)重組為綱常倫理結(jié)構(gòu):在這新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內(nèi),分為尊卑兩級(jí):君臣、父子、男女、陽(yáng)和陰、上和下等等。每一種倫理之內(nèi)都有確定的相對(duì)關(guān)系。于是,這一社會(huì)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網(wǎng),竟將古代中國(guó)具有彈性的網(wǎng)絡(luò)轉(zhuǎn)變?yōu)楣袒慕Y(jié)構(gòu)。一個(gè)固化的網(wǎng)絡(luò)猶如鉆石,堅(jiān)固卻難以調(diào)節(jié)。因此,宋代的政治永遠(yuǎn)是在僵固的結(jié)構(gòu)中糾紛不斷。
倒是在經(jīng)濟(jì)部分,宋代的工藝水平有很大的進(jìn)展。由于外貿(mào)的發(fā)達(dá),生產(chǎn)能力頗有因應(yīng)。在宋代,民間力量也因?yàn)榻?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具有相當(dāng)?shù)淖灾餍浴V袊?guó)固有的多元彈性系統(tǒng)卻存在于民間,始終保持活力,以適應(yīng)宋以后蒙古的征服,和明代繼承胡風(fēng)而建立的專制皇權(quán)。
明代的心學(xué)則將堅(jiān)固的理學(xué)結(jié)構(gòu)徹底予以修正。個(gè)人的自主權(quán)和自尊心,在心學(xué)理論中重新具有重要位置。這一轉(zhuǎn)變對(duì)于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儒家網(wǎng)絡(luò),本可注入新的力量,足以抗拒專制的皇權(quán);再加上明代晚期進(jìn)入中國(guó)的天主教,也將“宗教革命”前西方的自然科學(xué)帶入中國(guó)。這兩個(gè)條件如果配合得當(dāng),也許中國(guó)的整個(gè)文化面貌會(huì)出現(xiàn)重大變化。可惜,明代的專制皇權(quán),承襲了蒙古時(shí)代的暴力傳統(tǒng),不斷地摧殘儒生士大夫的努力。
滿清入主中原,更加劇了種族之間的不平等,強(qiáng)化了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壓制。于是,宋代以來(lái)皇權(quán)和科舉出身的官僚之間彼此合作,掌握了中國(guó)的命脈,也剝奪了中國(guó)人調(diào)整自己文化的機(jī)會(huì)。這一僵化的老大帝國(guó),對(duì)于外來(lái)刺激懵然不知,深閉固拒,迄于 1840年大敗,遂屈服于西方的經(jīng)濟(jì)侵略和文化侵略。此后百年之內(nèi),在政治和文化領(lǐng)域終于二度激發(fā)了革命。
不論是五四群賢領(lǐng)導(dǎo)的文化革命,或是相應(yīng)于兩次政治大革命引起的改變,都犯了匆忙草率的毛病:詬病中國(guó)文化傳統(tǒng),頌揚(yáng)西潮帶來(lái)的現(xiàn)代文明,可是在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圈內(nèi)卻罕見(jiàn)對(duì)中國(guó)過(guò)去持平的檢討;對(duì)于西方文明,無(wú)論是政治、哲學(xué)、經(jīng)濟(jì)等方面,也缺少認(rèn)真的研究和討論。于是,百年來(lái),中國(guó)的命運(yùn)動(dòng)蕩于對(duì)西方的或迎或拒。對(duì)于中國(guó)過(guò)去具有彈性的文化系統(tǒng),卻一次又一次地毀棄。
過(guò)去近七十年來(lái),中國(guó)大陸有一半時(shí)期籠罩在“破四舊”的口號(hào)之下,直到今天才有重新恢復(fù)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提議。在臺(tái)灣,于威權(quán)政治體系下,“傳統(tǒng)”曾經(jīng)是政權(quán)的護(hù)身符;最近三十年來(lái),又因?yàn)橥鈦?lái)與本土的沖突,“中國(guó)文化”四字居然成為禁忌。時(shí)至今日,中國(guó)文化體系又有復(fù)興的契機(jī),我們必須認(rèn)真尋找自己文化的安身立命之基礎(chǔ),而不能僅僅邯鄲學(xué)步,一味模仿西方模式。
我個(gè)人認(rèn)為,西方文明在歐洲和北美,由于科技的長(zhǎng)足進(jìn)步和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沖勁,三百年來(lái)占盡世界各地的資源,竟成全球主流。可是,經(jīng)過(guò)了幾次重大戰(zhàn)爭(zhēng)以后,西方文化本身因應(yīng)著國(guó)家組織和社會(huì)形勢(shì)的改變,原有的文化系統(tǒng)也面臨著嚴(yán)峻挑戰(zhàn)。基督教的影響力日趨式微;隨著工藝與科技發(fā)達(dá),工具性的理性改變了文化價(jià)值的選擇。生產(chǎn)力強(qiáng)大導(dǎo)致了生活的高度物質(zhì)化,也削減了人間精神的發(fā)展余地。人權(quán)觀念的自由和平等,在爭(zhēng)奪權(quán)利的場(chǎng)合中逐漸轉(zhuǎn)變?yōu)楸Pl(wèi)自己利益的個(gè)人主義,自制的紀(jì)律也淪為放任和懶散。一次又一次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改變,給教育的內(nèi)容和居住的形態(tài)引來(lái)新的形式。例如,大部分人口都集中于都市,都市的居民不斷變動(dòng),不遑寧居,社群離散,人情淡薄,遂使“寂寞的人群”只有孤獨(dú)。又如,民主政治是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驕傲,但在個(gè)人主義代替了公民精神后,民主制度的實(shí)踐也就打了極大的折扣。
最近兩三年,歐洲不少國(guó)家的政局都有向右轉(zhuǎn)的趨向,美國(guó)的特朗普政權(quán)也遠(yuǎn)遠(yuǎn)背離了民主的傳統(tǒng)精神。文化領(lǐng)域的活動(dòng)一天天地遠(yuǎn)離心靈的滋潤(rùn),而趨于庸俗的欲望滿足。剩下的一些不甘于粗俗和低劣的文化產(chǎn)品則轉(zhuǎn)而走向消極和悲觀。
以上這些趨向,到了今天已積重難返,很難在枝節(jié)上加以修正。尤其在可見(jiàn)的未來(lái)十年,以走向機(jī)器人和人工智能為發(fā)展方向,個(gè)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精神,在精神物化海嘯的巨浪下,將不再有發(fā)展的余地。原本在人類歷史紀(jì)錄中具有傲人成就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可謂已到日薄西山的黃昏。西方模式有值得參考及學(xué)習(xí)之處,卻也應(yīng)當(dāng)作前車之鑒,讓我們避免覆轍。
從當(dāng)下展望未來(lái)十年,尤其是從更長(zhǎng)遠(yuǎn)的歷史跨度考慮,我呼吁中國(guó)的俊彥之士,在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居住的中國(guó),并正在國(guó)人望治心切的今天,多花費(fèi)精力,也多得到一些空間,努力進(jìn)行推陳出新,在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多元而又辯證性變化的文化基礎(chǔ)上,建構(gòu)一個(gè)可以容納“東”和“西”的新世界文化。這一文化眼光所注視者,也不再是一個(gè)國(guó)家,而是天下;不再是一個(gè)民族、一個(gè)階級(jí)、一個(gè)地區(qū)或是一些人,而是普世眾民。
建構(gòu)如此文化系統(tǒng),不應(yīng)當(dāng)以中國(guó)的儒冠、儒服,或者讀經(jīng)、祭孔等外表的東西當(dāng)作提倡的方式。知識(shí)界應(yīng)當(dāng)嚴(yán)肅地面對(duì)這一重大任務(wù),關(guān)注的核心問(wèn)題是讓每個(gè)人認(rèn)識(shí)自己的尊嚴(yán),同時(shí)也提醒每個(gè)人的責(zé)任感;目標(biāo)應(yīng)落實(shí)在儒家理想,“修己而后濟(jì)眾”“安百姓”;這一“濟(jì)”與“安”的對(duì)象,卻是從自己身邊開(kāi)始,一直推廣到這個(gè)世界的人類。
人類可以從自然取得資源,以利用厚生;但也應(yīng)有所約制,不可過(guò)度。要完成如此任務(wù),不應(yīng)僅僅寄望于領(lǐng)導(dǎo)者,而應(yīng)是全民的投入。我們也盼望整個(gè)社會(huì)開(kāi)放討論空間,為了中國(guó)與世界的發(fā)展共同努力——對(duì)這個(gè)嚴(yán)肅的議題不應(yīng)設(shè)置禁區(qū)。
- 中國(guó)新聞周刊的其它文章
- 麗麗? 唐納森 百合也艷麗
- 健康新知
- 潮流新品
- 狗搶頭條
- 聲音?數(shù)字
- 你用“筆記本電腦”做筆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