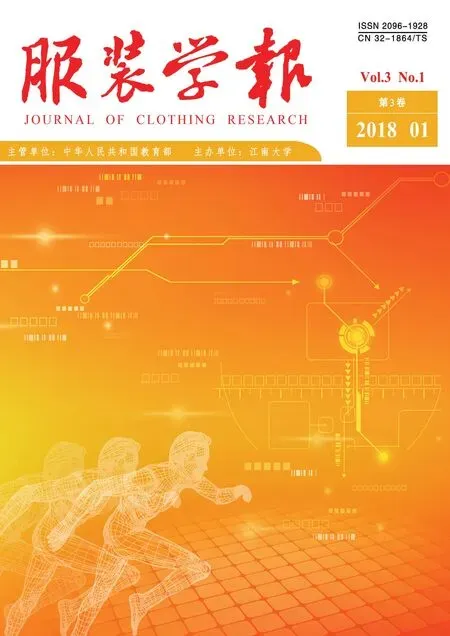實踐、包容與開放的“中式服裝”(上)
周星
(日本愛知大學 國際中國研究中心,日本 愛知 453-8777)
所謂“中式服裝”,主要是指具有中國服飾文化史的淵源,根植于一般民眾服飾生活的土壤,為中國最大多數(shù)的民眾所接受,同時又在與以“西式服裝”體系為主的他國服飾文化的比較中得以自認,或被他者認為是具有中國服飾文化屬性及特點的服裝。文中擬在近現(xiàn)代中國歷史波瀾壯闊的大脈絡(luò)之中較為系統(tǒng)地梳理中式服裝不斷被創(chuàng)造和建構(gòu)出來的進程及其成就。2006年5月,時任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曾在國務(wù)院新聞辦公室召開的記者招待會發(fā)言:“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漢服,但是我到現(xiàn)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裝是能夠真正成為代表中國的服裝,這恐怕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困惑。總體上我的觀點是,吃飯也好、飲食也好、穿戴也好,各有所愛,百花齊放,都是他個人的事情。但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們能夠創(chuàng)造出廣受大家歡迎的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服裝。”[1]這個表述說明,能夠代表中國的服裝眼下仍是一個困惑,國家尊重人民衣著的自由,但也推崇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服裝。文中也正是在這個思路上,希望對中式服裝的建構(gòu)實踐及其可能性予以新的探索。
1 20世紀中國人服裝生活的巨變與方向
在20世紀的一百年里,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的震蕩和變遷。以服裝的變革為核心,中國民眾的身體形象、自我認同、服裝生活方式及精神面貌均出現(xiàn)了徹底的改觀。服裝的變遷既是人民日常生活層面不斷追求的結(jié)果,同時也是各種政治力量及意見人士熱衷于爭執(zhí)和倍感焦慮的話題。按照文化人類學的觀點,“‘服飾’可以說是個人或一個人群‘身體’的延伸;透過此延伸部分,個人或人群強調(diào)自身的身份認同(identity),或我群與他群間的區(qū)分。因此,服飾可被視為一種文化性身體建構(gòu)”[2]。但另一方面,服裝也是滿足人們溫飽生活的基本條件,它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顯然,一百年來的“中式服裝”既是在上述意義上被不斷地建構(gòu)著,同時它也需要具備遮體御寒的功能,以及最低限度地維持民眾得體的服裝生活。
從清末到民國前期,中國民眾的服裝生活呈現(xiàn)出空前的混亂和多元化,“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3];與此同時,這種狀況也預示著新的中國人形象呼之欲出。在香港、澳門、臺北等殖民地,在上海、廣州、天津、大連等通商口岸及各國租界,從事洋務(wù)買辦與海外貿(mào)易的商人,以及留洋歸國的“洋學生”群體,逐漸邁向“文明開化”,掀起了洋裝熱,西服洋裝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國;但清王朝的遺老遺少和士紳階層的長袍馬褂卻沒有輕易地退出民眾的生活;知識階層和年輕學生們的長衫、西褲和皮鞋、禮帽以及連衣裙、短衫闊裙等,均反映出時代特有的風尚;勞工和鄉(xiāng)民階層的大襠褲、短襖、大衫子、繡花鞋、布鞋和草鞋,依舊根深蒂固,且受到生計的制約而難以改變;當然,還有國內(nèi)各少數(shù)民族款式眾多的民族服裝,固守著其族群身份的標志。此外,從軍警官憲以軍服為范本的多種制服,后來又發(fā)展出“中山裝”,成為以國民黨干部為主的群體的摯愛;以十里洋場的交際花、娛樂明星的衣著最為醒目,都市里從大家閨秀到小家碧玉,包括闊太太們分外鐘情的旗袍和西式大氅等。在很長一段時間,服裝成為中國社會百花筒里最為繁雜的圖案,也屢屢成為扎眼的社會文化問題。以服裝表達主義者有之,以服裝表現(xiàn)身體曲線者有之,反對以制服束縛自由者有之,致力于服裝復古者有之,主張全面洋裝化者有之,慨嘆某些較大尺度裸露的時裝有傷風化者有之。但無論多么復雜紛擾,民眾的服裝生活尤其是在生活方式層面卻逐漸地形成了既定而又明確的方向,盡管變遷歷經(jīng)曲折迂回,但以下幾個方向相互交織而促成的大趨勢卻日趨顯現(xiàn)。
1)西裝化、短裝化和類西裝款式的普及。清末民初,以東南沿海城市為核心,西服洋裝迅速在中國社會落地生根,各類西服或類西服開始流行,并成為時代的風尚。早在清末戊戌維新前后,服裝改革便已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甚至有“欲更官制、設(shè)議院、改試令,必自易西服始”的說法[4]。可以說,辛亥革命內(nèi)在的“易服”需求,主要是由西式服飾予以滿足的。所謂“易服”其實就是當時新政的一部分,方向是學習西方文明,而不是走向復古。康有為上《請斷發(fā)易服改元折》,就提到“萬國交通,一切趨于尚同”,故大清無法“衣服獨異”,他甚至主張西服也是符合中國古制的。后來雖然維新失敗,卻促進了民眾服裝生活西化的大趨勢。民國初年的輿論傾向認為,民國新服制應取向大同主義、平等主義,學習西方的簡便方式,采用西式。所謂“大同主義”,就是“與歐美同俗”,與世界各國的服裝大體一致。當時的革命派大都是大同派,因此,革命成功后,他們最常穿著的西服洋裝便進一步影響到全社會的服裝風尚。當時的人們除了以西服洋裝表達時代感、開放感甚至某種優(yōu)越感(同時也內(nèi)含著自卑感)之外,軍警制服的廣泛影響和后來象征革命的“中山裝”的推出,均促使國人(主要是男性)服裝生活逐漸顯現(xiàn)出以西式為現(xiàn)代性的基本形貌。
2)中式服裝的建構(gòu)實踐,不斷地在摸索中前行。在西式服裝涌入的同時,固守中國傳統(tǒng)服飾文化的力量依然雄厚地存在著;不僅如此,在人們意識到“西式服裝”的前提之下,重新定義和規(guī)范“中式服裝”的動向始終非常活躍。除了民間層面的穿著實踐,政府通過頒行新的服制或相關(guān)條例,也為以長袍馬褂為基調(diào)的中式服裝保留了一席之地。重要的是,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nèi),中國基層的鄉(xiāng)土社會為此種中式服裝提供了溫存的土壤。但中式服裝的建構(gòu)并未就此完成,而是在此后一個多世紀中,時不時地就會成為熱門的公眾話題,并不斷地被付諸新的建構(gòu)實踐。每逢此時,中國古代數(shù)千年的服飾文化史,多民族中國的多元服飾文化體系,以及大面積地存續(xù)于國內(nèi)各個地方的地域性“民俗服裝”[5],便都會成為建構(gòu)中式服裝的文化資源。
3)在中式服裝和西式洋裝相“并置”的格局當中,卻也有另外一個和市場經(jīng)濟、消費社會、流行文化相適應的趨勢,亦即民眾服裝生活的自由化和時裝化。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大趨勢的意義上,服裝越來越成為個人的自由選擇;雖然在階層分化、貧富差距嚴重的社會背景下,服裝依然成為社會分層的符號之一,但它和固定不變的身份逐漸發(fā)生了脫節(jié),不再有絕對的禁忌。伴隨著服裝自由化而來的,便是時裝化,人們通過服裝來表現(xiàn)個性和追逐時尚,這與伴隨著現(xiàn)代化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消費社會、時裝市場、以及方興未艾的大眾媒體密不可分。服裝的自由化和時裝化,尤其以女裝最為突出,故時人指出:“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稱闊者,或有步塵俳優(yōu),務(wù)時髦者。”[6]與此同時,在社會保守理念濃厚的時代里,對于各種“奇裝異服”的指責和質(zhì)疑也始終是如影隨形。
4)服裝的意識形態(tài)化和去意識形態(tài)化。在中國的歷史文化流脈中,向來有一個以服裝來表現(xiàn)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主張或倫理觀念的傳統(tǒng)。清末以前的封建帝制,服裝被視為等級身份甚至官職的象征,而新興的(多)民族國家,則需要通過服裝來建構(gòu)國民認同、形塑國民文化,于是,就出現(xiàn)了影響至今的有關(guān)“國服”的思想和理念。由孫中山親自倡導并施加了其影響而得以創(chuàng)制的中山裝,被認為實用、樸素、大方,富于時代感,但它在相當?shù)囊饬x上,也滲透著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后來甚至成為“三民主義”的物質(zhì)載體之一。20世紀50年代以后,共產(chǎn)黨人在此基礎(chǔ)之上,將其改進為“人民服”,使它更進一步地具備了“階級”、“革命”、“正統(tǒng)”等激進意識形態(tài)的內(nèi)涵。在截至“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之前,人們無論上班、聚會,還是出門訪友,接待來賓或出席鄭重的會議等,均穿著中山裝以為應對,以至于形成了特定的“制服社會”。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因為它具有太過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遂導致其在改革開放以后,廣大民眾便迅速、決絕地放棄了中山裝,這一改變深刻地意味著國民服裝生活的去意識形態(tài)化。
5)近代以來并不富足的漫長年代里,一般民眾的服裝生活總是以經(jīng)濟、樸素、沉穩(wěn)為基本,多是從日常生活的平凡性、便利性和舒適性為著眼點,通常較少為社會上層和知識精英的服裝理念及其服裝建構(gòu)實驗所左右。而任何旨在推動服裝變革的嘗試,只是在契合了民眾服裝生活的真正需求之后,才有可能程度不等地獲得部分成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服裝觀念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普通國民逐步淡化乃至于破除了曾經(jīng)附加在服裝上的意識形態(tài)涵義,服裝生活空前自由。鑒于著裝自由成為國民服裝生活的主旋律,因此,可以說中國從曾經(jīng)的“制服社會”進入到了“時裝社會”。另一方面,由于國門洞開,西方服飾文化的影響再次大舉進入中國,于是,中國社會在大面積地接觸國際服裝潮流的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本土的傳統(tǒng)服裝文化。進入21世紀以來,持續(xù)的經(jīng)濟高速增長將國民的物質(zhì)生活較大幅度地帶入溫飽有余、初步小康的境地。盡管依然存在著貧富分化,但人們的穿衣問題業(yè)已基本解決。以此為前提,當代中國服飾文化的發(fā)展或人們在衣著方面之生活方式的動向也就日趨活躍,一方面是時裝化、個性化、品牌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便是回歸傳統(tǒng)以尋找和重構(gòu)民族服飾之認同的各種動態(tài)。前者表現(xiàn)為層出不窮的時裝秀、模特大賽、品牌觀念、流行款式、西裝的普及和中國服裝工業(yè)的強勁擴展;后者則主要表現(xiàn)為中式服裝的回歸、民俗服裝的重新興起,“新唐裝”的流行、現(xiàn)代時裝或其相關(guān)品牌對中國元素的汲取、漢服運動的勃興,以及“新中裝”的嘗試等。
2 辛亥革命前后:曇花一現(xiàn)的“漢衣冠”
在20世紀中國人服裝生活的大變局、大潮流中,曾于辛亥革命前后,有過“漢衣冠”的曇花一現(xiàn)[7]。辛亥革命革除了數(shù)千年的封建帝制,徹底顛覆了異族的高壓統(tǒng)治,它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現(xiàn)代的(多)民族國家。由于清朝不僅形成了完整的封建等級服制,還始終堅持把接受其服飾視為漢族及其他異族表示臣服的標志,并不惜以暴力手段來實行,因此,當清朝搖搖欲墜時,人們往往就以“剪辨”“易服”作為象征來表達反抗及革命的志向。諸如太平天國時期的“蓄發(fā)易服”、清末結(jié)社如南社,以及革命黨人如同盟會的“剪辮易服”、海外留學生的“剪辮易服”,最后發(fā)展到新軍內(nèi)部的“剪辮”及易裝等。
有清一朝,極少數(shù)漢族士人對于漢家衣冠的歷史記憶始終不絕如縷[8]。道光時期,曾有士人向朝鮮使臣表示身穿滿族服裝和剃發(fā)并非由衷,乃不得已[9];和朝廷的“生從死不從”政策不無關(guān)聯(lián),為數(shù)眾多的漢族士人堅持葬禮著漢家衣冠入殮,于葬俗中寄托對傳統(tǒng)的執(zhí)著,例如,黃宗羲死后遺囑,希望“以所服角巾深衣殮”[10];章太炎家族的葬禮“皆用深衣殮”“無加清時章服”[11]等。當初革命黨人推翻清朝的訴求之一,便是“復我冠裳”,如鄒容的《革命軍》痛陳:“嗟夫!漢官威儀,掃地殆盡;唐制衣冠,蕩然無存。吾撫吾所衣之衣,所頂之發(fā),吾惻痛于心。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吾惻痛于心;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吾惻痛于心;吾見官吏出行時,荷刀之紅綠衣,喝道之皂隸,吾惻痛于心。辮發(fā)乎!胡服乎!開氣袍乎!紅頂乎!朝珠乎!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滿人之惡衣服乎?我同胞自認。”[12]由此可知當年在宣傳革命時,漢衣冠往往成為頗具悲情、適于社會動員和最易獲得民眾共鳴的符號。
章太炎流亡日本時,曾經(jīng)改和服而標“漢”字,故被認為是近代復興漢服第一人[13]。辛亥革命爆發(fā),有關(guān)“漢衣冠”的想象就變成了實踐,它主要表現(xiàn)為在南方很多城市光復之時,一些人特意著明朝古裝(往往就是戲裝),頭系方巾,上街以為慶祝。據(jù)親歷者回憶,當時守衛(wèi)武昌大漢軍政府的士兵“身穿圓領(lǐng)窄袖的長袍,頭戴的是四腳幞頭,前面還扎一個英雄結(jié)子”,使人疑惑是否剛從戲臺下來[14]。武昌城內(nèi),有青年“身著青緞武士袍,頭戴青緞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紅絨花,足穿一雙青緞薄底靴,同舞臺上武松、石秀一樣打扮,大搖大擺,往來市上。大概是“還我漢家衣冠”之意[15]。這種情形在其他發(fā)生革命的地區(qū),也幾乎是同時出現(xiàn),一般以軍人、士人為主,也有部分民眾響應,但由于日常生活并不存在漢家衣冠,所以,就直接把戲服拿來臨時借用,這是因為人們認為戲裝較多地保存了漢家古衣的風貌[10]。在長沙,光復后的大街小巷,經(jīng)常出現(xiàn)模仿戲臺上武生打扮的青少年;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以后,成都和附近一些縣城的街頭也出現(xiàn)了許多頭扎發(fā)髻或戴方巾、身著圓領(lǐng)大袖寬袍或戲裝的人,以及腰配寶劍、足登花靴而招搖過市的人。據(jù)說當時的川西同志軍,“為了恢復漢族衣冠,許多人奇裝異服。有的綰結(jié)成道裝,有的束發(fā)為綹,有的披頭散發(fā),有的剪長辮為短發(fā)。”[16]
當時的不少知識精英除了身體力行的穿著實踐,例如,夏震武、錢玄同等,還多利用報紙媒體,在“易服”的輿論方面做出很多努力,或為新生的民族國家提供服制改革方面的建議。較為著名的如錢玄同,他曾研究上古文獻,做“深衣冠服考”,并自制深衣;而在《民立報》1911年10月28日登載的“中國革命本部”的宣言書中,則直言中夏的“衣冠禮樂,垂則四方,視歐羅巴洲之有希臘,名實已過之矣”[17]等。
與革命之初漢衣冠在民間的曇花一現(xiàn)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后來的洪憲帝制運動也曾把它作為繼承中華文化正統(tǒng)的象征而予以利用,于是,漢衣冠成為袁世凱稱帝的政治合法性依據(jù),其在祭孔、祭天和稱帝儀典中大規(guī)模采用上古禮制的祭祀冠服,以表現(xiàn)漢官威儀,所謂“有歸漢官之盛儀重睹”[18];所謂“中華民國之首出有人,復睹漢官威儀之盛”[19]云云。然而,帝制復辟的失敗促使?jié)h衣冠在當時的封建性含義迅速凸現(xiàn),緊接著的新文化運動對封建傳統(tǒng)的猛烈批判,則進一步促使復興漢衣冠的思潮自行消退,并最終銷聲匿跡[20]。唯獨在臺灣于20世紀60年代末還曾明確制定涉及祭孔的冠服,這大概可以視為歷史的一點遺緒。
辛亥革命前后的“易服”曾經(jīng)有一個可能的選項,便是恢復古代漢人的服裝,但其時的國內(nèi)形勢和國際潮流卻均使復古訴求不再具有現(xiàn)實的可行性。魯迅曾經(jīng)談到漢服后來的不合時宜,他指出:“恢復古制罷,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臺上的裝束罷,蟒袍玉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吃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wěn)。”[21]漢服曾經(jīng)重現(xiàn)街頭的事實表明當時確曾有過此類實踐,但它無疾而終卻也是有若干深刻的緣由。
1)“易服”訴求所積累的張力,被“剪辮”運動及其成功所釋放,因為剪辮基本上實現(xiàn)了對于清朝暴力統(tǒng)治漢人之身體的符號性顛覆。1912年3月5日,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通令全國剪辮:“滿虜竊國,易于冠裳,強行編發(fā)之制,悉以腥之俗。……今者滿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滌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以除虜俗而壯觀瞻”。剪辮運動迅速蔓延全國并獲得成功,這在相當程度上初步滿足了革命的訴求。
2)當時更多的有識之士認為,“易服”就是脫去滿清強加的衣冠,至于換上何種服飾,卻未必一定要回歸古代,換上西裝革履,也是“易服”。換言之,西服洋裝提供了比古代漢服更為可能和現(xiàn)實的選項。對于當時的普通民眾而言,錢玄同等人提供的深衣玄冠實在是過于陌生和玄乎,故對它有很強的拒斥感。和西服洋裝相比較,深衣漢服絲毫沒有顯得更加現(xiàn)實或具有可操作性。從清末至民國初年,民眾對西服洋裝的穿著實踐,早已經(jīng)比零星的漢服更為普及,而且,其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性也使之具備了全新的時代感。特別是在上海、武漢、天津等城市,穿用西式服裝已成潮流,以至于要從海外大量進口,從而引發(fā)了對于國貨不振的擔憂。各大衣帽公司競相在《申報》發(fā)布公告,以西式服飾招徠顧客,其廣告用語往往標榜“傾向大同”[22],相比之下,傾向大同的理念顯然要比深衣漢服所內(nèi)涵的“復古”理念,更加容易獲得民眾的共鳴。
3)積貧積弱的新興國家,缺乏全民換裝的經(jīng)濟實力。一般民眾艱難的生計狀況很難支撐漢服,尤其是深衣玄冠、峨冠博帶的造型款式。事實上,民國初立,政府內(nèi)務(wù)部的意見就考慮到經(jīng)濟方面難以支撐全面易服:“國民服制,除滿清官服應行禁止穿戴外,一切便服悉暫照舊,以節(jié)經(jīng)費而便商民。”[23]
4)若要實現(xiàn)全民換裝,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習俗改革運動,其工程之巨大、之艱難,很難一蹴而就。以當時的中國社會而言,尚有很多遠比復興漢服更為急迫的社會風俗改革任務(wù),諸如剪辮、放足、破除迷信、婚姻自由等。
5)雖然清初的滿族入關(guān)伴隨著武力征服,進而通過高壓實現(xiàn)了文化的征服,亦即強迫漢人放棄衣冠而改穿滿式服裝,但在幾百年之后的20世紀初葉,卻已經(jīng)形成了兩個基本的既成事實:一是除了服飾以外,清廷乃至滿族在很大程度上反倒被漢文化所同化,清王朝自詡“中國”王朝,以“中華”正統(tǒng)自居;二是除了少數(shù)漢人知識精英之外,絕大多數(shù)民眾均已經(jīng)將長袍馬褂視為理所當然的衣著,它已成為服飾民俗的一部分。因此,異族的政治高壓一旦解除,幾乎失去了進一步換裝的內(nèi)在驅(qū)動。
6)也有論者認為,辛亥革命成功后未能兌現(xiàn)恢復漢衣冠的口號,主要是因為傳統(tǒng)漢服的寬衣、博帶、長裙有礙勞作,與現(xiàn)代社會生活已不相適應,再加上建立在等級制基礎(chǔ)之上的漢服體系難以符合現(xiàn)代民族國家有關(guān)人民一律平等的基本理念。的確,相對于地域、職業(yè)、階級等結(jié)構(gòu)異常復雜的中國社會,曾經(jīng)主要是古代士大夫衣著的深衣漢服,很難一下子就被普羅大眾所認可。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早在清王朝崩潰之前,中國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西裝化的趨勢。新生的中華民國實際上面臨著全球化進程中西方文化潮水般涌來的格局,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深衣漢服顯然是無法在和西服的競爭中取勝的。
3 民國服制與中式服裝的誕生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易服”就不再只是民間的實踐,它還成為政府施政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雖然在涉及“易服”的討論中,不乏封建王朝時代“易姓受命”“王者改制,必易服色”之類通過“易服”重建“正朔”的傳統(tǒng)觀念,但在另一方面,通過確立新的服制以建設(shè)國家形象和提振民氣以及推動社會更新,則是更為一般的意見。民國的國家體制和清末以前的帝國體制根本不同,故民國服制雖然也有歷史繼承的一面,但還是應該將它與歷史上的封建服制區(qū)別看待。清王朝及以前的封建服制,是以朝廷的冕服[24](“冕服”是指周朝君臣的禮服和祭服,它被視為禮制的體現(xiàn)或載體。但歷代對它的演繹和詮釋,通常總是伴隨著程度不等的想像、誤讀和重新建構(gòu),從而使這一問題高度復雜化了)為主體、以官僚等級制為核心,旨在區(qū)分尊卑、親疏和內(nèi)外的文化象征體系[25],民國的建立促使幾千年的封建服制亦即所謂的“衣冠之治”趨于解體,而伴隨著新的社會改革進程,服裝革命自然也就成為當時社會生活中的重大命題。
在新的政府治理下,全社會主導性的服裝話題,與其說是通過恢復漢服和漢官威儀來建構(gòu)正統(tǒng)性,不如說是在西服洋裝已成趨勢的格局下,如何既貫徹服式基本采取的“大同主義”,接受西式服裝的合理性,同時又較快、較好地成功建構(gòu)新的中式服裝,以繼承中華服飾文化傳統(tǒng)和凝聚國民認同。換言之,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服裝作為族際標識的意義,比起漢滿之間而言,更重要的是在中西之間。新生的民國政府采取了中西兼取并置的策略。在百廢待興的民國初年,政府較早地頒布了服制條例,正是為了及時回應當時社會輿論對于易服的高度期盼。
孫中山和袁世凱相繼主導了制定民國服制的工作。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的孫中山,曾于1912年1月5日,頒布了幾乎完全是學習西式軍服的《軍士服制》;在同年4月11日,孫中山提出的政綱,也包括“繪制服圖”。1912年5月22日,《申報》發(fā)表消息公布了民國新服制的草案:國務(wù)院現(xiàn)已將民國服制議定,大別為三:西式禮服,公服,常服。如禮服純仿美制;公服專以中國貨料仿西式制用;禮帽也是西式的等。袁總統(tǒng)要求法制局“博考中外服制,審擇本國材料,參酌人民習慣以及社會情形,從速擬定民國公服、便服制度,繪圖具說,經(jīng)國務(wù)會議同意后即呈,由本大總統(tǒng)提交參議院議決,頒布施行”。“惟禮服不僅上級官廳應有,即下級官亦應有;不僅官家應有,即平民亦應有。故現(xiàn)又重新議定,分中西兩式。西式禮服以呢羽等材料為之,自大總統(tǒng)以至平民其式樣一律。中式禮服以絲緞等材料為之,藍色袍對襟短褂,于彼于此聽人自擇。此亦過渡時代之一法也。”[26]《大公報》1912年5月23日也登載一則消息“民國服制之趕訂”稱:“法制局……奉大總統(tǒng)諭,……謂民國統(tǒng)一政府成立多日,各友邦亦將正式承認,尚未有相當服制,殊為不合。應趕即籌訂,以壯觀瞻。務(wù)于六月以內(nèi),核定籌情,并申明意見,大略擬分禮服、官服、常服三項。禮服、官服分別等級,常服普通一律。尤須以保守利權(quán)、符合世界大同及社會習慣為原則……”[27]
1912年9月至1915年11月,北洋政府相繼頒布了22項服飾制度及相關(guān)條令,包括國家公務(wù)員等特殊職業(yè),如軍警、司法、鐵路等的制服,以及分別涉及外交官、蒙藏王公、地方行政官員的公服、祭祀冠服、學校制服和一般國民的男女禮服服制等[28]。根據(jù)《政府公報》第157號:男子禮服分為兩種:大禮服和常禮服。大禮服即西方的禮服,有晝晚之分。晝服用長與膝齊,袖與手脈齊,前對襟,后下端開衩,用黑色,穿黑色長過踝的靴。晚禮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后擺呈圓形。褲,用西式長褲。穿大禮服要戴高而平頂?shù)挠虚苊弊樱矶Y服可穿露出襪子的矮筒靴。常禮服兩種:一種為西式,其形制與大禮服類似,惟戴較低而有檐的圓頂帽,另一種為傳統(tǒng)的長袍馬褂,均黑色,料用絲、毛織品或棉、麻織品。女子禮服用長與膝齊的對襟長衫,有領(lǐng),左右及后下端開衩,周身得加以錦繡。下身著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裥,上緣兩端用帶,下身用黑裙。
若是從1912年《服制》中以圖釋義的上述基本內(nèi)容來看,有關(guān)禮服,確實是做到了官民“式樣一律”,但涉及官服、公服的有關(guān)制度,依然是維持了等級原則。日本學者夏目晶子指出:中華民國前期的服飾制度,禮服制和官服制不同;僅就其禮服制度而言,沒有官民區(qū)別,這的確是一個進步;但官服制的另行存在本身,又意味著官民尚不平等,說明它尚有封建服飾觀念的烙印遺留[29]。至于祭服仍用爵弁、并以章數(shù)為等差,顯然也是古代冕服文化傳統(tǒng)在當代的遺存。
應該說北洋政府確立的服制,其最大特點是中西式并置,以西服為主要導向,這就使得當時中國社會的服飾改革具備了明顯的西洋化和國際化色彩。因為除了禮服中的男子長袍馬褂、女子上衣下裙之外,不僅以西裝為大禮服及常禮服之首選,更多的制服、官服和公服,也都采用源于西方的立體剪裁技術(shù)。對于西服的推崇,其實是對清末民初以來社會現(xiàn)實的一種追認;與傳統(tǒng)的長袍馬褂相比較,西服具有合體、挺括、莊重、簡易,以及便于運動等優(yōu)點,一個時期內(nèi)已然成為文明和開放的象征。然而,新服制也非常清晰地確立了傳統(tǒng)服飾的地位,亦即將長袍馬褂和對襟的上衣下裙與西服相并列,從而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式服裝”的誕生。長袍馬褂之所以在民國年間被官方視為“中式服裝”,同樣也是由于它在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服裝生活里較為普遍地存在這一基本的社會事實。雖然后來有不少人把長袍馬褂視為清朝遺老遺少的象征,但在那個特定時代,民國政府公布的以“并置”為特點的禮服方案依然合情合理地保留了它的位置。當年在北京召開國會時,議員們的著裝一定意義上正是對民國服制的遵從和實踐,當然這也是對當時基本國情的反映和尊重,同時還是對傳統(tǒng)服飾作為文化載體之象征意義的重視。據(jù)說“五四”運動過后,北京大學整飭校風,規(guī)定制服,請學生們公議,但最終形成的議決仍是袍子和馬褂。
“中式服裝”是在和西服洋裝的呼應、對照之中得以定義的,這個過程頗為自然。除了新生的民族國家需要通過它來保持某種文化特性之外,從保護民族紡織工業(yè)的角度,當時的服制也特別強調(diào)采用國產(chǎn)布料和國產(chǎn)紡織品。給中式服裝賦予合法的地位,其背后蘊含著對民族紡織工業(yè)和家庭手工業(yè)、以及女紅傳統(tǒng)亦能獲得發(fā)展的期許。即便是采用了“大同”主義的西式服裝,當時也有為“保存國貨”而突出地強調(diào)“易服不易料”的主張。據(jù)說在漢口,還曾經(jīng)有過紳商學界發(fā)起的漢口國貨維持會,舉凡入會者,“以不著外國衣履帽為第一義務(wù)”。把長袍馬褂明確為國民禮服,有助于改變當時曾經(jīng)有過的將其和辮子、纏足一起視為落后、愚昧之表征的認知,有助于形成中式服裝的正面形象。雖然民國服制對傳統(tǒng)服裝的溫存,并不意味著其具體形制有多少變化,但在和西服的對比、參照中,它卻具備了不同于清及以前封建王朝以等級制和皇權(quán)至上的服飾制度的全新意義,亦即它是新民主國家致力于建構(gòu)新國民文化的一部分。
隨后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施政中依然把服制改革視為建構(gòu)新國民文化的重要路徑。從1928年11月起到1933年1月止,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14項涉及服制的條例或法規(guī)[30],除了警察、軍隊、鐵路、司法、海員等國家公務(wù)人員的制服之外,以1929年頒布的《學生制服規(guī)程》和《服制條例》影響最大。通過這些條例或法規(guī),南京國民政府對北洋政府時期制定的服制做了大幅度改進,例如,取消了外交及地方行政官員的制服;簡化了各種制服形制,如對上裝的長度予以改短、減少鈕扣等;并大幅度地修訂了《服制條例》。與北洋政府時期的《服制》相比,主要是禮服制有所不同,南京國民政府的《服制條例》既對一般國民禮服有所規(guī)定,也對國家公務(wù)人員的制服有所規(guī)范。難能可貴的是,《服制條例》對禮服和制服的規(guī)定,并不包含公務(wù)人員服裝優(yōu)越或高于一般國民的寓意。
《服制條例》規(guī)定的禮服更加重視中式服裝,男子的長袍馬褂曾被規(guī)定為一律用黑色,這時則改為藍袍黑褂;女子禮服則增加了前期服制中沒有的藍色旗袍。北洋政府時期的女子禮服曾被規(guī)定為上衣下裙,要求對襟,身長至膝,周身加繡飾,衣料無顏色限制;南京國民政府規(guī)定的女子禮服保留了上衣下裙形制,但上衣和旗袍均要求“齊領(lǐng)前襟右掩”(近似于右衽),衣長改短為過腰,顏色設(shè)定為藍色,裙子為黑色。這些改動使得女子的著裝相對而言,顯得更加活潑、明快。至于以西服洋裝為禮服的思路依然存在,但只簡單地表述為“因國際關(guān)系服用禮服時得采用國際間通用禮服”。南京國民政府在國民禮服方面,強化了中式服裝的重要性而對西服有所淡化,其優(yōu)先順位發(fā)生了從西服到中式服裝的逆轉(zhuǎn)。
《服制條例》中涉及制服的部分,主要是針對除軍警、鐵路等特殊職業(yè)之外的國家一般公務(wù)人員而言。女子以旗袍為制服,作為禮服的旗袍和作為制服的旗袍,不同之處在于制服的規(guī)定是顏色不拘,此種簡約規(guī)范為旗袍在公共場合的表現(xiàn)提供了自由。男子制服規(guī)定為褲子采用西褲,上衣用立體形制,和男學生制服類似,胸前裝有三個暗袋,服色為冬黑夏白。1936年2月出臺的《修正服制條例草案》更是明確地將中山裝列為公務(wù)員制服:“制服:男公務(wù)員采中山裝式,女公務(wù)員采長袍式,均得并用西式服裝。”與此相關(guān)的“說明”則提到:“現(xiàn)行服制條例所定男公務(wù)員制服,式如學生裝,實行以還,各機關(guān)迄未嚴格遵守,誠以此項款式,未盡妥適,致推行不無窒礙……”由此可知,此前的《服制條例》因?qū)δ行怨珓?wù)人員制服款式描述過于簡略,又與學生制服接近,未盡妥適,故未能嚴格遵循,于是才有了予以修訂的必要。
民國服制對于學生的制服較為重視,這是因為國家在建構(gòu)新的國民形象之際,男女學生的形象更加容易引起關(guān)注。北洋政府時的學生制服,規(guī)范籠統(tǒng),男生制服形式,“與通用之操服同”,夏天用白色或灰色,冬天用黑色或藍色,帽子與“通用之操帽同”,或用本國制草帽,靴鞋也用本國制造品;大學生制帽,“得由各大學特定形式,但須呈報教育總長”。女生“即以常服為制服”“著裙,裙用黑色”。所謂“操服”“常服”的具體款式并不清楚,或可推測“操服”大概是對當時軍服的模仿,“常服”的不確定性則為各學校自由發(fā)揮留下了余地。比較而言,南京國民政府對學生制服的規(guī)定要更加體系化和具體化,從相關(guān)規(guī)定看,也是更多地受到了軍服和西式服裝的影響。
總體而言,南京政府對民國服制的改革,突顯了中式服裝的地位,將其置于比西式禮服更為重要的地位,包括將旗袍確定為民國禮服和女性公務(wù)人員的制服等,可以說尊重了民眾服裝生活的基本現(xiàn)實。民國服制對當時和后來很長一段時期內(nèi)中國民眾的服裝生活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也推動了一般國民逐漸形成新的現(xiàn)代服飾意識。民國服制是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急劇變遷之過渡階段的歷史性產(chǎn)物,如果說北洋政府時期的服制主要是回應“易服”的時代性課題,試圖通過服制確立新政府的權(quán)威性,那么,南京政府在前期基礎(chǔ)之上經(jīng)由服制改革確立的新服制,更多地是要建構(gòu)新的國民文化,亦即制造新的“國民”。因此,在兼顧西式禮服和西式制服的前提下,中式服裝得到了更加明顯的強調(diào)。
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民眾的服裝生活方式總體上出現(xiàn)了短裝化走向,民國服制也直接推動了人民著裝由傳統(tǒng)寬大松緩向現(xiàn)代簡短精干的方向轉(zhuǎn)換[31]。以女學生的著裝為代表,改良式女裝的一般特點是上衣較短、長不過臀,整體裝束追求樸素大方。長袍馬褂則有了兩個分化的支流,一是從長袍發(fā)展出了中式長衫,二是從馬褂演繹出各種中式短裝。單布長衫或夾層長衫,曾經(jīng)是20世紀30—40年代知識分子的典型裝束,和長袍馬褂之長袍相比較,長衫更加合體貼身,袖口也趨于緊窄,再配以西褲、皮鞋、禮帽等,顯然是一種亦中亦西的穿著;長衫的線條比較簡練,布料比較隨意,剪裁制作也比較簡單,可與之搭配的配裝(鞋、禮帽、圍巾等)也有較多選擇,因此,它和現(xiàn)代旗袍能夠構(gòu)成一組相互呼應的男女服裝。此種中式長衫主要在經(jīng)濟條件一般的知識分子、公務(wù)員或大學生中較多穿用,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后才慢慢消失,進而中國人的男裝就徹底實現(xiàn)了短裝化。
與通過國家權(quán)力建構(gòu)服飾制度以引導或介入民眾服裝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近代以來中國服飾文化變遷更加具有重要性和關(guān)鍵性的,則是普通民眾的穿著實踐。無論是禮服、還是常服,抑或是勞作時的穿著,民眾服飾生活以約定俗成為原則,同時也在不斷地實踐著改良和革新,其中包括對服飾自由化和時尚化的追求。在老百姓日常的服裝生活中,還有很多中式服裝的其他形態(tài),例如,民國時期的傳統(tǒng)男女褲很多都是平面剪裁的“緬襠褲”,中下層勞動階級的男子往往還要扎著褲腳,只是因為它們太過民俗而沒有被服制改革者所關(guān)注而已。
致謝:應“漢服北京”邀請,2017年9月10日,筆者在北京市西城區(qū)第一圖書館,以“漢服運動與中式服裝的可能性”為題做了講演;應江南大學崔榮榮教授邀請,2017年12月30日,筆者參加在無錫召開的“由宮廷到民間——服飾文化遺產(chǎn)的考鑒與傳承學術(shù)研討會”,并以“實踐、包容與開放的‘中式服裝’”為題做了主題報告。此文是為這兩次講演和報告準備的文稿,并先后得到崔榮榮、李宏復、楊娜、牛犁諸位學界友人的指教,在此謹致謝忱!
[1] 陳玥.孫家正談漢服運動:我不清楚什么能代表中國服裝[EB/OL].(2006-05-25)[2018-01-08].http://www.cctv.com/science/special/C15516/20060525/102405.shtml.
[2]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川西羌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8:14.
[3] 佚名.閑評(二)[N].大公報,1912-09-08.
[4] 胡珠生.宋恕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3:502.
[5] 周星.鄉(xiāng)土生活的邏輯——人類學視野中的民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63-266.
[6] 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冊[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29.
[7] 周星.新唐裝、漢服與漢服運動——21世紀初葉中國有關(guān)“民族服裝”的新動態(tài)[J].開放時代,2008(3):125-140.
ZHOU Xing.New Tang suit, Hanfu and Hanfu movement-new trends of "national costum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J].Open Times,2008(3):125-140.(in Chinese)
[8] 楊娜.漢服歸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18-19.
[9]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J].史學月刊,2005(10):42- 49.
GE Zhaoguang.Where are the hats and clothes of ming dynasty nowadays[J].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2005(10):42- 49.(in Chinese)
[10] 孫靜庵.明遺民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74.
[11] 王玉華.多元視野與傳統(tǒng)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24-125.
[12] 鄒容.革命軍[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28.
[13] 章太炎.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Z].1914-05-23.
[14] 任鴻雋.記南京臨時政府及其他[M]//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辛亥革命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777.
[15] 程潛.辛亥革命前后回憶錄[M]//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辛亥革命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107.
[16] 王蘊滋.同盟會與川西哥老會[M]//中國人民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220.
[17] 佚名.中國革命宣言書[M]//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8] 楊度,孫毓筠.與孫毓筠等促袁世凱登極折[N].政府公報:第1304號,1915-12-25.
[19] 劉晴波.楊度集[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604,607.
[20] 李競恒.衣冠的背影:清末民初政治思潮與實踐中的“漢衣冠”想象[EB/OL].(2011-02-27)[2018-01-08].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070.html.
[21] 魯迅.洋服的沒落[M]//花邊文學.上海:上海聯(lián)華書局,1936.
[22] 李躍乾.論辛亥革命前后的服飾改革[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1999,21(2):127-131.
LI Yueqian.On clothing reform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J].Journal of Huaiyin Teachers College,1999,21(2):127-131.(in Chinese)
[23] 內(nèi)務(wù)部.關(guān)于一律剪發(fā)暫不易服的告示[G]//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政協(xié)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匯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721.
[24] 閻步克.服周之冕——《周禮》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M].北京:中華書局,2009:13-23.
[25] 張法.中國服飾: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演化的第一次浪潮[J].天津社會科學,1996(1):65- 68,95.
ZHANG Fa.Chinese clothing:the first wav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evolution[J].Tianjin Social Sciences,1996(1):65- 68,95.(in Chinese)
[26] 佚名.袁總統(tǒng)飭定民國服制[N].申報,1912-05-22.
[27] 佚名.民國服制之趕訂[N].大公報,1912-05-23.
[28] 印鑄局官書科.第十七類·服制徽章[M]//印鑄局官書科.法令輯覽:第9冊.北京:中華民國國務(wù)院印鑄局.1919.
[29] 夏目晶子.清末至民國時期中國服飾文化變遷與社會思想觀念[D].天津:南開大學,2009.
[30] 中華民國立法院編譯處.中華民國法規(guī)匯編:第8冊[M].北京:中華書局,1934.
[31] 丁萬明.民國初期服制變革的成效及其文化意蘊[J].社會科學論壇,2012(3):221-227.
DING Wanming.Effec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reform in the early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2012(3):221-227.(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