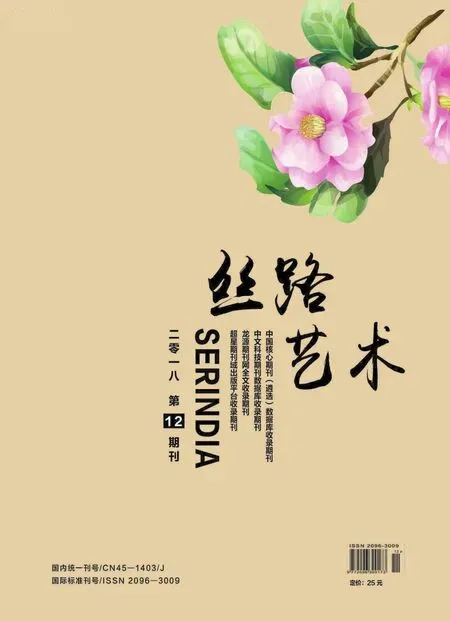白先勇與桂林
黃怡(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0)
前言
籍貫為桂的作家有很多,像白先勇這樣享譽海內外且被夏志清教授譽為“短篇小說的奇才”的他確是第一人。法國著名學者丹納曾在《藝術哲學》中把文學創作的三大要素歸納為:環境、種族、時代,他在書中寫道,“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要了解作品,這里比別的場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啟發作品的風俗習慣,產生作品的環境”。由此可見,地域對于作家的文學創作有著深重的影響。無論是沈從文筆下純美的湘西風情,還是老舍眼中幽默逗趣的北平人,這都無不體現著文學作品中隱含的地域標簽。而在白先勇的文學作品中,桂林作為其故鄉也是屢屢被提及,它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位置,更是白先勇魂牽夢繞的故鄉,它是指向白先勇內心最深、最軟的抽象化的精神家園。
一、創作之源
白先勇曾輾轉于多個城市之中,國內有上海、香港、臺灣等地,海外亦有芝加哥、紐約,其在桂的時間不過短短七年,但正是這一段匆匆而過的歲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極深的烙印。《驀然回首》中白先勇直接提到了他的文學啟蒙——“講到我的小說啟蒙老師,第一個恐怕要算我們從前家里的廚子老央了。老央是我們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說慣道的口才,鼓兒詞奇多。因為他曾為火頭軍,見聞廣博,三言兩語,把個極平凡的故事說得鮮龍活跳。”廚子老央便順理成章地成了指引白先勇文學道路上的第一盞明燈。
“群峰倒影山浮水,無水無山不入神”,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既是白先勇的故鄉,也是他文學靈感之源。白先勇的小說《玉卿嫂》、《悶雷》、《我們看菊花去》、《花橋榮記》都與桂林息息相關。其作品在內容上將桂林元素納入其中,如桂林人物刻畫、桂林飲食的書寫;在寫作語言上,其清秀、別致的語言更是和這一片秀美的土地密不可分。
在人物設置上,白先勇筆下的米粉丫頭和玉卿嫂就是不折不扣的桂林人。《花橋榮記》中,白先勇借米粉店老板娘之口說道,“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到底不同些。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著幾分山水的靈?”字里行間都透露出白先生對故鄉之人的贊美。《玉卿嫂》中,白先勇借描寫保姆玉卿嫂的樣貌來大贊了一番桂林人,“好爽凈,好標致,凈粉的鴨蛋臉,水秀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們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個戲子還俏幾分。”民以食為天,在飲食上白先勇也對桂林的飲食文化加以熏染,“我對食物的描寫,除了口腹之欲,還有一種中國文化的驕傲,一種潛意識的文化沙文主義。只有在食物上,我們有一種文化上的驕傲感。”《花橋榮記》中,白先勇對桂林馬肉米粉更是鐘情,就是那一碗碗熱騰騰的米粉成了流落在臺北的廣西人最佳的精神慰藉。
桂林的沃土滋養了白先勇的文學創作,在其語言上便可見一斑。白先勇的小說中,其語言風格的特色之一是靈活運用地域方言,增強人物的個性色彩,使文章具有別樣的生活氣息。如《花橋榮記》多次不著痕跡地運用桂林方言,使米粉丫頭這個角色異常生動。又如《玉卿嫂》中說道,“玉卿嫂這個人是我們桂林人喊的默蚊子,不愛出聲,肚里可有數呢。”這樣的比喻既通俗又形象地道出了玉卿嫂的性格特點。
二、情感之基
《紐約客》中,白先勇以清冷的筆法描摹了海外游子的蒼涼之心,而在短篇小說集《臺北人》中,白先勇作品中的悲劇色彩更是愈加強烈,這烈如勁酒的情感則大部分源于他對往昔的留戀與內心濃得化不開的鄉愁,這一系列悲苦之感很大一部分則又是故鄉桂林所賦予的。
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中家鄉與故土是最為溫暖與神圣的,白先勇的短篇小說集題名雖是“臺北人”卻在講著廣西人的故事。那些遠離故土的廣西人在異鄉日日夜夜都思念著家園,日子漸久,家的概念也逐漸模糊,只得看著桌上的桂林馬肉粉品一品米粉中的鄉愁。《臺北人》這十四篇小說中囊括了社會階層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妓女、男傭、老將,還有一些普通的知識分子,甚至還包括劇場里的名伶。這些各色各樣的人物無一例外的染上了深重的悲涼感,這一切在開篇就有所暗示。“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白先勇用唐人劉禹錫的詩歌《烏衣巷》作為開篇,其背后的深意讓人遐想無限——烏衣巷本是六朝貴族居住之地,本最為繁華,今日有名的朱雀橋邊竟然荒草叢生,烏衣巷口再不見來往的馬車和行人,只有單薄的夕陽懶懶地照在昔日的深墻上,簡單的二十八字便已給文章定下哀婉的基調。潛藏于《臺北人》的主題是非常復雜的,如學者歐陽子所言,“今昔之比”正是白先勇索要表現的主題之一,《臺北人》之“昔”包含青春、美麗、榮耀、希望,而“今”則代表衰敗、丑陋、絕望和死亡,今昔之變道盡了那些從大陸退居遷移臺灣的各色人物在歷史風浪中感知到的世態炎涼與滄桑。
三、對故土和傳統文化的思考與重構
在如今的全球化語境之下,許多遠離故鄉的作家們都會運用文學媒介來展示自己失落的生活境遇。站在故土與他鄉這樣宏闊的視野上關照,故土是現實生活中的家園,而傳統文化則是理想中的精神世界。不可否認的是,《花橋榮記》固然是一篇難得的描寫廣西的出彩小說,但是也要注意到,在白先勇的筆下,他所說的“家”或是“故鄉”其實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臺北是我最熟悉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這里上學長大的——可是,我不認為臺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許你不明白,在美國我想家想得厲害。那不是一個具體的‘家’,一個房子,一個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這些地方,所有關于中國的記憶的總和,很難解釋的,可是我真想得厲害。”實際上,白先勇是在尋找精神上的寄托,構建一個文學家園,以此來抵消現實生活中難以割舍的鄉愁。因此,白先勇和當時的很多臺灣作家一樣“以較為開闊的胸懷和全局性的目光對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命運予以整體性思考和把握,并進行了極為可貴的研究和探索。”
地域文化對白先勇的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白先生將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雜糅在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中,不僅使文學作品的內涵加深,更是凸顯了人物的特殊品格,將一個各色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白先勇通過小說中對桂林的抒寫以及相關人物的細致刻畫,已然構建了一個他心中的烏托邦,在自己精神層面上得以滿足的同時,也是完成了他對傳統文化的回望、思考與重構。
首先,白先勇深受傳統文化的浸潤,曾數次提起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與熱愛。如他從小就喜歡讀《紅樓夢》,還常常在課上教學生《紅樓夢》,他的著作《白先勇細說紅樓夢》更是將自己對這本“天書”的探索和領悟娓娓道來,以一個小說家的藝術敏感將那些文學史上被遺落的人物拾起并歸還其本原色彩。白先勇還酷愛傳統戲曲,如《玉卿嫂》中就有許多看桂戲的片段,《游園驚夢》更是將將一些唱詞融入其中,這些都體現了白先勇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憂思。
其次,白先勇常常輾轉各地,當他站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濃重的鄉愁自然應運而生。此時的白先勇與他筆下的人物一樣,飽受無根漂泊之痛,越來越感受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曖昧和模糊,每當回憶起童年在故鄉桂林的歡樂時光,這些溫暖美麗的記憶在精神世界中被無限放大于是就形成了“原鄉”記憶,這些美麗的過往又與作者在紐約、芝加哥等地的“他鄉”型城市作了有意無意的對比,其光鮮一面被淡化,而粗陋黑暗一面則是被無限放大。原鄉城市以桂林為代表,展示出來的更多是平靜和純美,而紐約芝加哥等地雖是物欲文明發達,更多的是充斥著鋼筋水泥似的冷酷,這就鮮明地顯示出白先勇對祖國文化的留念與捍衛。
結語
因為童年在桂林的美好時光在白先勇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于是在他的文學創作中不斷地出現與桂林相關的內容以及其文學作品中包蘊的今非昔比之感和濃郁的鄉愁都是桂林所賦予的。但是抒寫鄉愁不是白先勇的最終目的,無論是原鄉型故土還是異鄉型城市,都是白先勇對故土和傳統文化的思考與重構。作家與地域文化血脈相連,一方面地域色彩為白先勇的文學作品增輝,另一方面,白先勇也為桂林地域文化奉獻了獨特的文學景觀,奠定了其在當代文學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