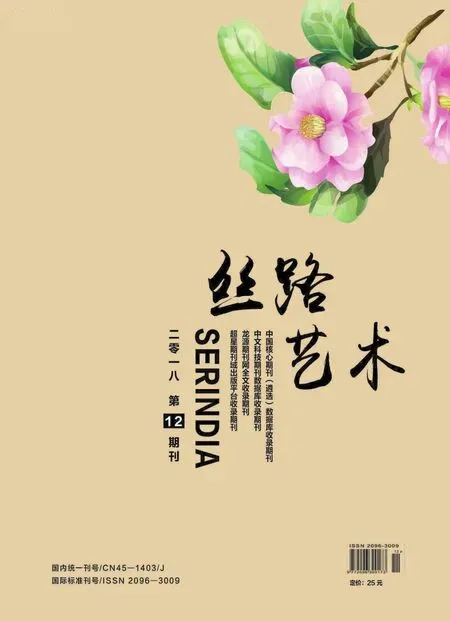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的審美體驗
臧琪(山西師范大學,山西 臨汾 041000)
新編歷史劇《曹操與楊修》蘊含著獨特的美學新風向,它不僅適應了時代發展的需要還關注到大眾審美意識的提高,尤其是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看重。 美麗是具體的,美麗的東西以其特定的形象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曹操與楊修》于1988年首演后引起熱烈反響,此后不斷排練演出,是一部彰顯著強大生命力的戲劇精品。《曹操與楊修》向我們展示了京劇改革的新成就,是新時期以來不可多得的藝術精品。 該劇值得稱道的是它能從歷史和藝術的雙層面出發,兼顧二者來塑造主人公曹操與楊修的人物性格,使觀眾獲得了與眾不同的審美體驗。
一、獨特的敘事
課堂上老師們曾推薦過多部優秀的戲曲作品,如《十五貫》、《牡丹亭》(青春版)、《山村母親》等,可在我腦海中留下最深印象的當屬新編劇目《曹操與楊修》,在觀賞過程中我內心激起強烈的波瀾,我想這種強烈的喚起許是源自劇本所營造出的耐人尋味的意境,亦或是尚長榮先生形神畢現的表演。 文藝美學的觀點提出,藝術審美接受中的“觀”,是指感性方面的關注,觀眾調動起自己機體內的特殊感受器,如視、聽等感覺器,對藝術作品所傳達的感性信息的最初承受。
該劇在三國演義原著的基礎上,增加了誤殺孔聞岱,曹操守靈殺妻等情節,這是曹操與楊修結仇的根源,也讓敘事更為完整且符合邏輯。曹操與楊修,都是出類拔萃之人。但由于性格不同,使他們無法攜手共事,于是,便有了一系時而讓人怦然心動時而又捶胸頓足的戲劇糾葛。楊修終于被殺了,曹操多么不想殺他,又不可不殺;楊修多么不想觸怒曹操,卻又次次得罪了曹操。兩個卓絕的英才,兩個高傲的靈魂,在共事中,一個過早的隕落了,一個也陷入痛苦……是或非、對與錯已顯得不再那么重要,創編人員似乎也沒有要刻意將這些強加給觀眾,而是讓大家自己體會。
二、高超的藝術手法
假設“觀”是對外部形式的直接的整體的感知,則“品”就是對對象意蘊的直覺領悟,是對審美對象深一層次的了解,在此階段我們要用自己的心靈經驗去讀解、體會形象的意蘊。
(一)更為鮮活的人物形象
《曹操與楊修》既沒有去追趕潮流,一味地取悅觀眾,也沒有將京劇獨有的表演形式棄之不用,而是始終把角色塑造放在舞臺創作的第一位[1]。初看《曹操與楊修》,我覺得似乎有把曹操白臉換紅臉化的傾向,被稱為一代梟雄的曹操,他的一句“寧叫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讓大家定性了他品質。但在劇中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了解曹操的塑造:一方面是曹操本人自我的表現,他在郭嘉墓前慨然吟誦“明月之夜兮,短松之崗,悲歌慷慨兮,悼我郭郎!天喪奉孝兮,摧我棟梁[2]。”可見曹對人才的看中,對賢良逝去的悲痛;當曹激動地拉著楊的手說我們相見恨晚,楊開玩笑的說“我也生的晚”,此時曹開懷大笑,不再是我們心中那樣不茍言笑、無情冷酷的形象而是一個人;當曹為孔聞岱守靈時對誤入的愛妻唱到:“我夢中殺了孔聞岱,文武百官盡知情,倘若容你安然去,我網殺無辜擔罪。不舍賢妻難服眾,欲舍賢妻我怎能,事到此間亂方寸,進退維谷南煞人[3]!”這唱出了曹對妻的不舍,同時表露了對誤殺人一事的懊惱,人物塑造有血有肉。另一方面是旁人眼中的曹操,也就是側面來刻畫人物。楊修在和曹操安步當車、深夜交談中不僅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曹二十多年的詩作,更直言“我更敬其人憂國憂民的襟懷如斯也。”;另外,楊與曹初次見面就立下了軍令狀,可見曹在楊的形象無疑是高大的。
其實,隨著劇情的發展細細品來《曹》劇并非如此,除了表現曹是雄心大略、惜才愛才的英雄外,也很好的將曹剛愎自用,不肯放低姿態輕易認錯的統治者思想表現了出來。如本就與孔聞岱有殺父之仇,只是顧及楊修的建議與顏面,遂勉強答應讓孔聞岱擔當重任,但一經小人挑撥便不管不顧殺掉了一位賢才,試想曹完全可以先將孔聞岱關押起來審問,亦可找來楊修對質等,可惜了那歷盡千辛萬苦,為漢室立下大功的孔聞岱,就這樣由于曹始終不能平復存于內心的猜忌成了他的劍俠冤魂。又如曹操命人斬殺楊修,突然密報加急,楊判斷定是軍情緊急,于是和盤托出自己早設有埋伏,果然蜀軍大敗而去。此刻,眾將領嘆服于楊料事如神,于是紛紛下跪愿以性命求曹赦免楊的死罪,原本就不想殺楊的曹大驚,唱到:“平日一片頌揚對曹某,卻原來眾忘所歸是楊修”。作品只是把人物性格塑造的更為人化、更為復雜、更為弧形編創者很好地把握住了曹操性格中的“奸”和“雄”,很成功地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具有多面性格的曹操,,令觀眾對其又愛又恨。 難得的是,《曹》劇并不是單單推翻傳統藝術作品中曹操白臉的形象,作品摒棄了嘩眾取寵與虛華浮躁,不是刻意塑造一個與傳統截然對立的形象來試圖擦亮觀眾的眼睛,提起觀眾的獵奇興趣。它的妙處在于通過人物性格所帶有的自我矛盾,來揭示戲劇中悲劇發展的必然性,進而來塑造一個不同以往版本的曹操形象,從而達到提升作品藝術品位的目的。通過戲本身來解釋故事和人物,將厚實的文化內涵和人類的普遍情感包蘊于戲中,用藝術的語言來撞擊觀眾的心靈,給觀眾自我思辨的空間,這樣的作品無疑是有深度的。
(二)出神入化的表演
尚長榮先生很好地掌握了這個角色,于表演中很到位的滲透著曹操自我人格中的偉大與卑微處,再現了權威和文化、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為我們展示了曹操的新形象,無論是內部心理還是外在特征,這是在以往舞臺的塑造中從未見過它。熟悉尚先生的觀眾都知道,他擅長于花臉的表現,而在此劇目表演中,他不僅保留了原有藝術風格,還在恰當處增加了小生所表現的灑脫與剛健,老生的穩健與沉著。例如在的第三場中,曹頓然明白了是自己錯誤地殺死了孔聞岱,為生動的表現出曹的驚嚇、震驚、懊悔等心態,于是尚先生運用了一個踉蹌。
劇中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品味,那就是先生對于“笑”這一動作的拿捏與表現,尚先生在這出戲中至少呈現了七種笑。當曹操和楊修初相遇時,曹操興奮地說:“你我相見恨晚吶!”楊修忙說:“我生也晚哪!曹操和楊修講完后,曹操和楊修默契的擊掌,同時有一種略顯可愛的噴笑 。以前的藝術家侯希瑞先生曾使用這種笑,現在尚昌榮先生把這種形式巧妙地借鑒了過來。當觀眾看到尚長榮先生在戲劇中的敞懷大笑,有點幽默的趣笑,含有殺氣的獰笑,表無奈的強顏歡笑,滿意的笑,幸福的笑,痛苦的似笑非笑,無心機的天真笑等,我真的不得不佩服他高水平的表現。于我而言,毫不夸張地說我在看到精彩處竟不自覺地感到陣陣戰栗。
三、引發的人生思考
欣賞完一部藝術作品,我都會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的感悟,這個“悟”是思索理解、理性把握,是對藝術的哲學思考也是對生活經驗的積淀和對人生覺解的完善。《曹操與楊修》的故事情節取材于“三國”,題材不算新,甚至有點算是翻老本,但就在老本中卻翻出了新意,闡釋出了深厚的社會與人生思想。 我看過幾遍此劇目后,有兩個方面引起了我的思考,一方面是關于劇中悲劇釀成的思辨,二是關于作品本身的創作方面。
歷史長河中,人們對世界的反映可以有很多種形式,而藝術作為一種精神表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的感知覺、注意、記憶、理解、體驗,甚至包括那些真切的呼吸和體溫,即使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也可以是這樣。而戲劇,它是靠扮演角色來表演故事,是對人的模仿,更成為了一門“人學”。所以,在藝術發展、創新過程中,最大的創新與價值,難道不該是對人的發現以及對這種被發現的獨特表達嗎? 一直很贊同這樣一種觀點,“當我們以一種人類學的思維看戲劇,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戲劇是人的自我實驗。”康德也在《實用人類學》說道:“人們總的來說越文明就越是演員”,巴西導演博奧說得好:“即使我們沒有做戲劇,我們還是劇場中的人。劇中之人才是真正的人類,因為只有人能在行為動作中觀察自己。通過行為中觀察自我,才使得我能夠改便我自己的行為方式[4]。”我們常言性格決定命運,楊修終了還是被押上了斷頭臺,這結果是意料之外但更在情理之中。 楊修無疑是聰明的,從智斗三位商人,設計謀逼迫曹操承認誤殺孔聞岱,巧用兵計讓蜀軍大敗等他屢屢成功,可就是這盡顯無疑的聰明將他一步步推向了絕路。
斷頭臺上,曹操痛惜地喊道:“可惜你不明白,不明白啊!”是啊,可惜了楊修一身智慧,卻偏偏多了份自作聰明、侍才傲上、倔強不改的脾性。可以說他那恃才傲上的個性將他滿腹才華和足智多謀的光環硬生生扯了下來,以致楊修雖早早看透曹操其人品,卻無法做到像他人那樣阿諛諂媚、虛與委蛇以求的保留自身性命,而是事事與曹操作對,場場讓曹操難看,最終引來殺生殺身之禍。 由此,我們應該反思一下該如何做人,固然有些人才能很高,但那不該是他們驕傲與放縱的資本,面對同學、老師、家人、朋友、同事、領導,我們應學會謙虛,學會換位思考,學會大智若愚,不要執著于逞當一時的英雄,而使大家的關系走上不可挽回與修復的地步。
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為當代文化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也對傳統文化與民族藝術的延續和發展提出了挑戰。 在這個大背景下,“戲曲傳承與創新”“戲曲現代化”擺在我們面前。我國戲曲不僅是最能體現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一種藝術形式,更是一個流變的、包容的、吸收的文化系統。它有一種受獨特的文化傳統影響和經歷史積淀而形成的穩定性,而這種穩定不只在嚴謹的藝術規范、熟悉的藝術風格,更在于那整套的的藝術語言。 因此,我認為在對傳統劇目進行表演時,特別是新創劇目時,為了獲得應有的表演生動與觀眾的認同,為了讓原有的形式真正切合新的內容,戲曲家們更要比其他一些非程式化藝術家有一種清醒的認識、突破的創新和有效的能力。 而真正對戲曲表演藝術發展的自覺,應該體現在劇本創作過程中對演員的充分看重,以及演員自我對表演藝術創造的自我肯定與嚴格要求。我們的戲曲是中華傳統文化獨特的藝術存在,其文化品位與內在是博大精深的,我們應更加把戲曲作為一種文化來推廣和發揚,讓其活躍在舞臺上更走進人們的心里來。
注釋:
[1]胡勝盼《曹操與楊修》的啟示
[2]引自劇本《曹操與楊修》
[3]引自劇本《曹操與楊修》
[4]施旭升譯,奧古斯特?博奧 .論戲劇[J].戲劇藝術,2004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