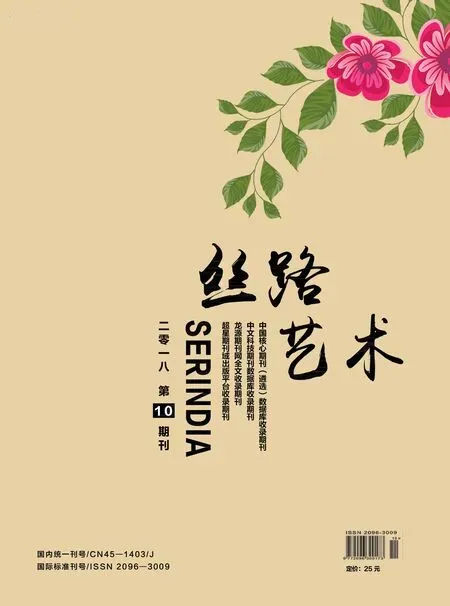從歷史角度看云南回族的形成
李趁基(河南大學,河南 開封 475000)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決定了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客觀性,而中國的歷史現實結構則如實反映了客觀性的內容。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個民族都是五十六個民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每個民族也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回族是我國分布最廣的少數民族,其中云南回族與全國回族同根同源,以元憲宗時期的蒙古軍與回回軍的南下進入云南開始,明清兩朝又各有一次大規模的云南回族人口的遷入,經過元明清三朝的發展與變遷,最終形成了現在云南回族的規模。通過對云南回族的形成研究,有助于地方了解少數民族的歷史,加強民族團結。
一 回族在我國歷史上的形成過程
唐時的回族主要為僑居或在中國安家落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唐代,有僧人鑒真手記記載,天寶年間的海南島就已經存在波斯人聚居地,書中說到:“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
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公元760年,在楊州范圍內發生小規模兵變,其中阿拉伯與波斯商人遭受損失很大。所以可知,中國早在唐朝就已經形成了與阿拉伯、波斯等國的交流與交往,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大量留居中國,形成規模。
宋時的政府實行積極的通商政策,宋朝商貿規模是基于在唐代的基礎上的,其中從事商貿活動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穆斯林大量增加。長期定居在中國境內的穆斯林后代根據宗教信仰的需求,在蕃坊內建立禮拜寺,并進行宗教活動,開始擁有公共性的墓地等。
南宋的方信孺在《南海百詠》中記載:“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北宋的大觀、政和年間(1107—1117),“穆斯林后代在廣州、泉州設蕃學,“蕾客”、“胡商”的子弟成為教育的對象,是回族阿語學校的最早雛形”[1]。
在當時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進入中國的穆斯林與其后代被視作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或外國人后裔,出生于中國的穆斯林,已經具有了漢族的血統,逐漸被融合與同一,所以他們的國家觀念為:將中國作為自己的國家,將阿拉伯、波斯、中亞等作為自己的故國或故土。
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了滿足大量外族人的生活需求,設立“蕃坊”專門供居住,并允許外族人與漢人通婚。每一個“蕃坊”設“蕃長”,主要職責在于管理居民日常事務,并參與、主持宗教性的活動,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得以增強。大量的穆斯林源源不斷進入中國,或置產或寓居或定居,與漢族等民族交流融合成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
元代之前,早期回族從人數與規模上就已很可觀了。宋元之交,周密的《齊東野語》記載:1236年,蒙古軍兵臨襄陽城下,襄陽城內的軍民就有回回人。雖然回族的主體形成年代確切來說始于元代,但是在元代之后,才出現大量回回人與中亞各族穆斯林的遷移,根據“蕃坊”內的共同的語言、文化、經濟生活等方面來看,唐宋時期與漢族和其他民族逐漸融合的蕃客們,是與元代的回族不一致的。
首先元代的大環境比起唐宋時期的回族形成的條件和機遇更有優勢,所以唐宋的穆斯林的后代漢化現象嚴重。因為在當時,許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阿拉伯、波斯血統的回族人自身就具備了漢文化因素,而且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與伊斯蘭文化聯系與交流有限,在生活中被漢文化影響,所以在唐宋時期穆斯林后代融入漢族的比例是較高的。
其次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的長期發展狀況而言,形成一個新民族的趨勢是較為明顯的。
阿拉伯人奈丁的《群書類述入馬蘇第《黃金草原》、福慮格爾的《摩尼師及其著作》等書中記載的大量史實發生的時間大約在中國的五代。這說明當時的吐魯番等地,因為接連著河西走廊,大量的穆斯林在此聚居。
元曲中的《狄青復奪衣襖東》就出現了河西回回兵。西夏滅亡(1227年)之后,馬可波羅歷經河西走廊,見到了大量的伊斯蘭教徒居住于敦煌、張掖等地。這些都是元代以前早期回族形成的客觀因素。
二 云南回族的歷史源流
云南回族是中國回族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具有了自身的特點,但是與全國各地區的回族屬于同一宗源”[2]。據歷史文獻資料記載,早在十三世紀中葉,云南定居的回族先民數量就已經很可觀了,至十八世紀初,云南都是作為回族移居的首選。
在元憲宗三年(1253年)間,回族第一次大量入居云南,當時正逢忽必烈、兀良哈臺為首的蒙古軍聯合西域的回回軍南下,隨軍出征的大多為中亞各族人。“元王朝建設過程中,為了滿足經濟政治等需要,云南各地成為征戰的駐地,在云南范圍內,大量駐軍從事農業屯墾、軍器制造,逐漸將云南作為聚居地”[3]。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沐英等明將率軍平云南,是第二次回族大量入居云南,在二人的軍隊中以江南的回回為主,在云南戰事結束后,此部分回回全部落籍云南,在云南境內長期屯墾,開始逐漸定居。
在明末清初,即公元1644年左右,清兵入關推動了第三次人口大量入居云南,當時南明的桂王政府以云南為駐守,其部下中大量回回隨地轉戰,后來大部分在滇西落籍。清代初期,清王朝的滇東政策“改土歸流”就是針對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
歷史的進程表明了云南回族的發展進程,主要為回回軍士的派駐、作戰、屯墾等形式,以“兵農合一”的生活方式為主。他們與云南境內的漢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白族、彝族等其他民族共同居住、通婚、交往。人口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長,在文化、農業、經濟、商貿等方面逐漸同一融合。出現了回回人聚居“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色與特點;在宗教信仰方面,伊斯蘭教的信仰和生活習俗發揮其統一性的功能,將不同來源回回聯系起來,形成了主觀性的民族心理素質;另外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回回居民與漢族的交流,使得漢文化增強了影響力,漢語被認定為回回民族的共同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