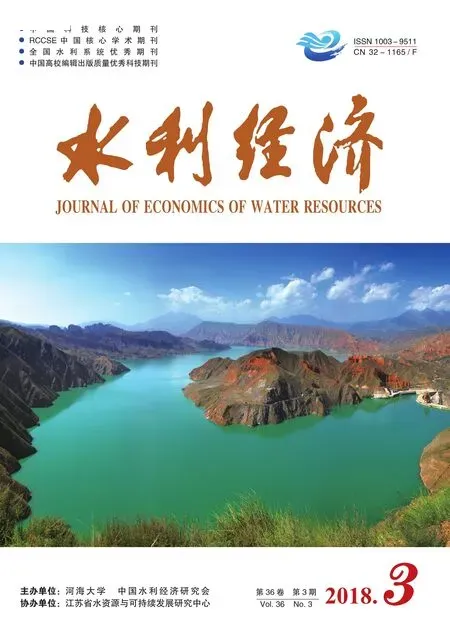流域生態補償理論及其標準研究綜述
劉 洋,畢 軍
(1.濟南大學商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2;2.南京大學環境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流域是自然過程和人文活動相互作用最為強烈的地區之一,與人類生產生活關系最為密切。流域是以自然水系分界的相對獨立、完整的系統,河流作為其中的連續體,承接上下游之間的物質流動、能量交換,各要素之間相互影響。同時,流域又被不同的行政區分割,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經濟技術和歷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流域內人類活動具有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增加了流域系統的復雜性。流域上中下游是利益共同體,上游過度開墾土地、破壞植被、過量取水、排放廢物等,不僅影響當地生態環境,還會使中下游的河道淤積抬高、水量水質下降,造成下游用水危機;如果上游為保護流域水環境,實行更嚴的環保措施和標準,雖然能保障下游用水,但卻使本地喪失了發展機會,影響區域經濟收入和當地居民生活質量。流域上下游之間水資源供給和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水環境糾紛不斷出現。
生態補償作為典型的經濟激勵手段可有效地促進流域上下游之間的協調發展。與傳統的命令控制型手段相比,生態補償更具靈活性和成本有效性;通過政府支付或市場交易等手段向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者付費,從而激勵供給者主動保護環境,實現生態系統服務的持續供給及環境資源優化配置。生態補償研究涉及內涵、主體、標準、方式及效應評價等多方面[1-5],而補償標準是其中的核心問題,影響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及效果[3]。國內外學者針對生態補償標準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尤其是測算方法,諸如市場定價法[6-8]、成本費用法[9-11]、支付意法[12-14]等。然而,目前生態補償標準尚未形成完備、成熟的研究體系,理論和實踐上均有待完善。筆者在流域生態補償理論探討的基礎上,重點針對補償標準的確定方法進行歸類總結,并提出存在的問題和研究展望,以期為流域生態補償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和啟示。
1 流域生態補償的理論概述
1.1 流域生態補償的基本概念
盡管生態補償已成為當前理論和實踐研究的熱點,但目前國內外對生態補償的界定并不統一。在國外,生態補償一般被稱為“為生態系統服務付費”或“為環境服務付費”(Pay for Ecosystem/Environment Service,PES),是對流域生態系統服務供給者給予的付費補償。Wunder[15]認為生態補償是指至少一個買者付費給至少一個賣者之間的自愿、有條件的交易,從而維持可持續的環境管理實踐,促進生態系統服務或環境服務的增加。目前比較有影響的概念分別是RUPES項目和國際林業研究中心(CIFOR)對生態補償的界定,兩者均認為生態補償不同于傳統的命令控制手段,是在一定條件下,雙方自愿的用地行為或交易,并對界定范圍內生態環境服務進行付費[16]。
國內一般將生態補償理解為一種資源環境保護的經濟手段[17],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補償包括對生態系統服務提供者的獎勵和向生態環境破壞受害者的賠償,也包括對造成環境污染者的收費;狹義概念則為生態保護補償,是對人類活動產生的生態環境正外部性所給予的補償。由于概念的不確定,20世紀90年代前期,流域生態補償普遍被認為是流域水污染賠償,隨著源頭控制的水環境管理需求,流域生態補償逐步轉向對上游水環境保護行為所產生的生態效益的補貼。
1.2 流域生態補償的理論依據
1.2.1 公共物品
薩繆爾森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社會產品定義為公共物品[18]。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物品在使用過程中難以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物品的消費,從而導致“搭便車”現象的發生,造成供給不足;由于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使得物品的消費不會引起個體成本的增加,從而導致“公地悲劇”,造成過度使用。自然生態系統及其所提供的生態服務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為避免“搭便車”現象和“公地悲劇”,需要從公共服務的角度,通過付費補償或政府管制的方式進行管理,保障生態系統服務的合理利用。流域生態補償作為保護和改善流域生態環境的行為,其產生的良好水環境可視為一種公共物品,需要下游受益者對上游保護者進行經濟補償,從而促進上游保護者生態建設的積極性,達到優質水環境的持續供給。
1.2.2 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理論是指一方的行為活動對活動之外的第三方產生的非市場化影響,從而造成外加效益或成本產生。外部性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分別是使他人受益而無需付費,或使他人受損而不付代價。如果外部性問題不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將會降低環保行為積極性或加劇環境破壞行為,造成環境質量持續惡化。庇古稅和科斯定理被認為是解決外部性問題的重要手段。庇古稅主張政府采取適當的經濟政策(如稅收與補貼等)進行干預,消除外部不經濟性[19]。科斯定理則認為在產權明晰和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外部性可以通過市場解決[20]。流域環境資源利用中的外部性表現為開發利用造成的外部成本和生態環境保護產生的外部效益。對于水量問題,在中小流域尺度上可以通過明晰產權的方式進行市場交易來解決外部性;對于水質問題,在企業層面上可以通過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等方式解決,但在區域層面上則難以明確權屬,需要通過付費補償來調整上下游的邊際成本或邊際效益,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提高流域整體社會效益,進而促進流域水環境質量的持續改善。
1.2.3 生態資本論
生態資本論認為自然資源及其生態環境是有限、稀缺的,具有使用價值和存在價值,其中食物、生產資料、生活用水等直接消耗的資源具有使用價值;而生態環境自凈能力、水土保護等是生態系統功能的內在價值,對人類來說是非使用的間接價值。Costanza等[21-22]對全球生態系統進行的價值評價、聯合國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23]、美國研究機構發起的自然資本項目[24]以及歐洲環境署主導的“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經濟學”計劃等項目均表明環境和資源的價值論意義。生態資本論為實施流域生態補償提供了理論依據。根據社會需求、效用價值論、勞動價值論等,流域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具有價值屬性,是重要的生態資本。通過實施流域上下游之間的生態補償,下游發達地區通過支付補償費用以獲取上游地區提供的生態服務,從而體現了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1.2.4 可持續發展論
可持續發展是指人類的社會經濟發展應與生態環境相協調,不能超越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保障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永續利用,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間的協調性發展。流域上下游是利益共同體,上游的經濟活動會對下游的水環境造成顯著影響;如果為了保護流域整體環境,上游被迫放棄社會經濟發展的機會,這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公平原則。因此,通過流域間的生態補償政策,下游受益方付費給上游保護者,促進區域發展的公平性。此外,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流域資源環境開發過程中,應維持生態系統的長久效益,避免短期追求經濟利益的行為。通過生態補償機制,完善流域資源環境的長期發展戰略,從而保障流域生態系統安全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2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研究方法
從我國目前的環境經濟政策實施來看,排污收費、環境處罰等流域水污染賠償方面的研究和實踐較多,并有一套相對完善的法規,但流域生態保護補償研究與實踐還處于探索階段,缺乏相應的法律支撐,在補償標準、補償主客體等方面尤為不足。2016年5月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中指出,目前我國生態保護補償的標準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項措施的成效。在生態補償標準確定時,其理論計算方法起到關鍵作用。為此,筆者重點圍繞國內外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理論研究方法進行綜述。
2.1 基于市場交易理論的補償標準研究方法
基于市場交易理論的補償標準研究方法是指根據供求關系的市場原理,將流域上游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商品化,下游通過支付貨幣購買該商品,達成一定的交易價格,即補償標準。該方法多用于流域水資源定價和水權交易研究中。理論上講,該補償標準應按市場交易的均衡價格,即供求曲線的交點;但現實中,與傳統的市場不同,生態系統服務難以按照商品價值定價,一般通過談判協商或拍賣的方式確定補償標準。例如,Guabas河流域下游用水者與上游土地利用者通過協商確定將額外的水費作為補償標準,從而在旱季獲得了相應的供水量[6]。法國Vittel公司與周圍農戶簽訂協議,給其提供資金來促使他們改變用地方式或放棄生產,從而達到維持水質的目的[7]。印度尼西亞的研究者通過模擬拍賣的方式,計算不同拍賣試點的生態系統服務供給曲線來確定補償標準,以其達到解決咖啡豆種植園的水土流失問題[8]。周大杰等[25]應用影子工程法、市場價值法等方法確定官廳水庫流域生態補償標準。江中文在比較了機會成本法、費用分析法和水資源價值法之后,認為水資源價值法可以用作計算漢江流域的生態補償標準[26]。劉玉龍等[27]建立了改進的總成本計算模型,并引入水量分攤系數、水質修正系數和效益修正系數以計算新安江流域的生態補償量。
通過市場理論法確定生態補償標準,可以滿足雙方的利益條件,其結果適用程度較高,因此很多研究都進行了相關探索,包括水資源交易和碳排放權交易。但是由于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復雜性,該方法僅可用于產權清晰的服務類型,適用范圍較小。同時,由于政府或相關組織機構的干預,限制了市場的公平、自由交易。此外,由于生態、社會、經濟在內的不確定因素較多,補償標準計算的準確性有待驗證。
2.2 基于微觀經濟學模型的補償標準研究方法
國外一些學者以微觀經濟學原理為基礎,根據理論上的供給曲線模擬流域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提供者或享受者的微觀決策過程與生態服務的變化關系,以此確定生態補償標準。該方法具有嚴謹的邏輯推理過程,可以應用于不同類型的生態補償研究。例如,Antle和Valdivia 開發了最小數據方法(Minimum-data Approach, MD),利用概率密度函數和其分布函數將個體決策者的經濟生產模型和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通過生態服務機會成本的空間分布來模擬新增生態服務的供給,將支付水平與新增生態服務量有機地聯系起來,從而耦合生態系統服務產生的人文決策過程和自然變化過程。Antle等[28]將最小數據法應用在美國蒙大拿州的糧食生產區,以此計算農戶通過改變用地、提高碳封存而獲得的補償費。同時,研究者也指出該方法雖然為政策者提供了充分且精確的分析結果,但是需要機會成本數據符合正態分布,且假設個體決策者不考慮風險規避。在現實中,這種理想的狀態難以實現。為此,Smart[29]嘗試將風險規避等因素加到MD模型中,并應用到肯尼亞土壤碳封存合約中。結果表明,由于生產存在一定的風險,影響了農戶參與生態補償機制的意愿,進而影響了補償標準的確定。同樣,最小數據法也在我國流域生態補償中有所應用。劉玉卿等[30]用最小數據法和SWAT水文模型分析了黑河流域上游機會成本的空間異質性以及補償價格對上游禁牧比例及水源涵養服務的影響。趙雪雁等[31]采用最小數據方法模擬了甘南黃河水源補給區草地水源涵養服務供給曲線,根據不同的生態恢復目標,確定補償標準,估算新增水源涵養量。
通過微觀經濟學模型方法確定生態補償標準,其所需數據相對少,模擬也足夠精確,可以作為生態補償標準方法研究的理論依據,為決策者提供一定的參考。但由于該方法理論體系尚未完善,且一些假設條件也未被充分認可,因此應用于生態補償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
2.3 基于意愿調查的補償標準研究方法
該方法通過詢問下游補償者或上游受償者對保護環境的支付或受償意愿,以確定補償標準。調查者需要做好充分的前期準備,包括對調查問卷的設計、被調查人群及影響區域范圍的確定等,同時也需要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結果進行擬合、回歸計算。Bienabe等[12]對哥斯達黎加流域居民和旅游者進行了意愿調查,并建立了計算補償標準的多項式邏輯斯諦回歸模型。Moran等[32]對蘇格蘭地區居民的生態補償支付意愿進行了問卷調查,并采用AHP和CE法進行了統計分析。Loomis等[13]對美國Platte河流域5種生態系統服務的總經濟價值進行了討論,并結合支付意愿法研究了支付費用與社會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Van等[33]在局地尺度上采用定性的訪談調查,結合定量的情景條件價值(Contingent valuation scenarios)分析,得出下游城市地區對上游水質改善的支付意愿,為當地環境管理政策提供參考。張翼飛等[34]系統梳理了生態服務及其價值評估、支付意愿與補償標準之間的理論聯系,指出充分考慮利益主體的意愿是科學制定補償標準的必要環節,意愿價值評估法的應用將增強我國生態補償標準的科學性。張志強等[35]以支付卡的方式對黑河流域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的支付意愿進行了調查,從而得到生態補償的經濟效益。
通過對利益相關者進行的意愿調查,能夠更直接地明確成本和期望等因素,理論上應該最接近邊際外部成本的數值,故應用范圍很廣。但是該方法卻存在很大風險,調查問卷的數量和質量以及被調查者的認知情況等因素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結果的真實性,甚至會產生重大偏差。
2.4 基于生態系統服務定量模擬的補償標準研究方法
生態系統服務評價有2種方式,一是根據利益相關者的主觀感知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量化;二是結合生物物理過程的定量研究對生態系統服務的物質量進行精確計算,再借助經濟價值化方法將服務量進行貨幣化,為決策者提供流域生態補償標準值。很多學者提出應該整合多學科方法用于評價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以便為決策者確定生態補償資金提供參考。例如,Fisher等[5]認為在坦桑尼亞的生態補償中應該模擬生態服務產品、過程變化,并懂得不同尺度上生態系統功能與人類福利之間的關系;Kumar[36]認為在諸如印度一樣的發展中國家,為生態系統服務付費需明確并評價生態系統服務需求狀況和導致生態系統服務變化的驅動因素,并借助水文水質模型、社會經濟評價模型等多種方法來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然而,如何評價生態系統服務變化過程,并將評價值與生態補償標準進行銜接是現今面臨的重要挑戰。Daily等[37]指出需要創新或更新方法,用科學的手段明確生態系統產品和服務的產生及變化機制,并在生物多樣性和社會背景下,設計適當的經濟、政策和管制體系,利用激勵或制度法規等方式促進人們更好地認知生態系統,并加以保護。國際上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計劃、自然資本項目也帶動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研究的不斷發展,為生態系統服務精確量化及生態補償標準確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我國的相關研究大多以用地類型和面積為度量單元,借助Costanza等[21]或謝高地等[38]的研究成果,調整不同用地類型的服務價值單價,從而得出研究區總體生態服務價值,并借助社會經濟系數予以修正,得到生態補償標準。例如,牛叔文等[39]對黃河上游瑪曲的生態服務價值進行了估算,結合牧民生活水平,確定了區域生態補償標準。史曉燕等利用Costanza對生態系統服務評價原理,界定了東江源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補償范圍,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評價了東江源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以此計算其補償標準[40]。
縱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針對基于投入費用計算補償標準的研究較多,應用生態系統服務定量評價的研究較少,而且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價多是建立在現狀評估的基礎上的。國外研究者關注生態補償與改善環境、消除貧困等之間的關系,并從生態效益和社會福利供給等角度確定用地管理者的生態補償標準。國內由于生態系統服務研究尚未深入,較少應用生態系統服務定量模擬方法,多是根據生態環境變化的成本費用法進行量化,而該方法沒考慮環境變化對區域生態效益的影響,造成補償標準計算不準確,不利于管理決策的實際應用。
3 存在問題與研究展望
3.1 流域不同類型的生態補償標準測度
流域生態補償一般是針對流域內特定的生態系統服務類型,例如洪水消減、水量供給、水體凈化、水土流失等。其中,對于水資源量這一有形的服務類型可以通過商品交易定價等方式獲得其公允價值,以作為其補償標準值;而對于水質保護這類無形的生態服務類型則較為復雜,難以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計量和定價。此外,不同類型生態補償的作用效果具有顯著差異的周期性。因此,對于水體凈化、洪峰消減等無形的生態服務,需要通過評估方法獲取其公允價值,并從時間和空間多維度分析服務的變化量,以評估促進補償標準的核算。
3.2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多情景分析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可歸結為2種方式:①從環境資源的角度,量化上游環保行為所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按取得的生態效益計算補償標準;②從經濟學成本的角度,量化上游環保行為所承擔的經濟損失,包括投入成本、機會成本等,并按損失的成本計算補償標準。前一種方式由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價方法不完善,使得補償標準計算結果偏大,不能應用于實際管理;后一種方式則難以全面量化成本,使得計算結果偏小,影響補償實施的持續性。因此,在分析流域水污染控制政策的基礎上,建立不同情景的補償方案,充分考慮各自的社會成本和效益,以得到基于特定管理目標的補償標準,為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提供參考。
3.3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的動態優化
流域生態補償政策對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行為產生影響,而行為變化帶來的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果又進一步對管理者的決策產生反饋作用,進而促進補償標準的改變。然而,目前的補償標準確定多是針對當前狀況,沒有充分考慮微觀主體行為變化以及不同行為所帶來的環境效益的改變,使生態補償標準缺乏動態優化機制,進而影響補償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未來研究應結合個體行為分析及其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評估,建立動態優化的補償標準,以促進生態補償政策實施的永續性。
3.4 基于多學科理論的流域生態補償標準研究
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確定生態補償標準是未來主要研究趨勢之一。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量化需要充分考慮地區生態系統結構、過程、功能、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關聯性,建立合理的評價指標及有效的量化方法。因此,在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知識交互作用下,研究符合區域實際情況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量化方法,為生態補償標準的準確制定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CAPLAN A J, SILVA E D. An efficient mechanism to control correlated externalities: redistributive transfer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regional and global pollution permit marke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 49(1): 68-82.
[2] KINZIG A P, PERRINGS C, CHAPIN F, et al. Paying for ecosystem services-promise and peril[J]. Science, 2011, 334(6056): 603-604.
[3] 賴力, 黃賢金, 劉偉良. 生態補償理論、方法研究進展[J]. 生態學報, 2008, 28(6): 2870-2877.
[4] ENGEL S, PAGIOLA S, WUNDER S. Designing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663-674.
[5] FISHER B, TURNER K, ZYLSTRA M. Ecosystem services and economic theory: integration for policy-relevant research[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8, 18(8): 2050-2067.
[6] 王燕,高吉喜,王金生,等.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方法述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1):337-339.
[7] PERROT M D. The vittel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 “perfect” PES case[J].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2006, 9: 24.
[8] JACK B K, LEIMONA B, FERRARO P J. A 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 to estimating supply curve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use of auctions to set payments for soil erosion control in Indonesia[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9, 23(2): 359-367.
[9] WUNDER S, ALLBAN M. Decentralized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the cases of pimampiro and PROFAFOR in ecuador[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4): 685-698.
[10] KALACSKA M, SANCHEZ G A, RIVARD B, et al. Baseline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ayments from satellite imagery: a case study from Costa Rica and Mexico[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8, 88(2): 348-359.
[11] GIACOMO B, LESLIE L, BERNARDETE N, et al.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suppor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nzan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2011, 20(3): 278-302.
[12] BIENABE E, HEARNE R. Public preference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cenic beauty within a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ayments[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06, 9(4): 335-348.
[13] LOOMIS J, KENT P, STRANGE L, et al. Measuring the total economic value of restor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an impaired river basin: results from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urve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 33(1): 103-117.
[14] 李曉光, 苗鴻, 鄭華, 等. 生態補償標準確定的主要方法及其應用[J]. 生態學報, 2009, 29(8): 4431-4440.
[15] WUNDER 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the poor: concepts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J].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3(3): 279-297.
[16] PESKETT L, KATE S, JESSICA B.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for carbon financing in the forest sector: learning lessons for REDD+ from forest carbon projects in Ugand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1, 14(2): 216-229.
[17] 劉傳玉, 張婕. 流域生態補償實踐的國內外比較[J]. 水利經濟, 2014, 32(2): 61-64.
[18] 張真,戴星翼. 環境經濟學教程[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19] 余永定,張宇燕,鄭秉文. 西方經濟學[M].3版.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20] 沈小波. 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政策工具及前景[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6): 19-25.
[21] COSTANZA R, DARGE R, DE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Nature, 1997, 387(6630): 253-260.
[22] COSTANZA R, DARGE R, SUTTON P, et al. Changes in the glob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 2014, 26(2): 152-158.
[23]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our human planet: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5.
[24] KAREIVA P, TALLIS H, RICKETTS T H, et al. Natural capital: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pping ecosystem servic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5] 周大杰, 劉莉, 馬軍, 等. 流域水資源生態補償標準研究:以官廳水庫流域為例[C]∥第六屆環境與發展中國(國際)論壇, 北京:中國環境保護部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0.
[26] 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 生態補償原理與應用[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27] 劉玉龍, 許鳳冉, 張春玲, 等. 流域生態補償標準計算模型研究[J]. 中國水利, 2006(22): 35-38.
[28] ANTLE J M, VALDIVIA R O. Modelling the supply of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agriculture: a minimum-data approach[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6, 50(1): 1-15.
[29] SMART F C. Minimum-data analysis of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with risk averse decision makers[D]. Bozeman: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2009.
[30] 劉玉卿, 徐中民, 南卓銅. 基于SWAT模型和最小數據法的黑河流域上游生態補償研究[J]. 農業工程學報, 2012, 28(10): 124-130.
[31] 趙雪雁, 董霞. 最小數據方法在生態補償中的應用:以甘南黃河水源補給區為例[J]. 地理科學, 2010, 16(5): 748-754.
[32] MORAN D, MCVITTIE A, ALLCROFT D J, et al. Quantifying public preferences for agri-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cotland: a comparison of method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3(1): 42-53.
[33] VAN H G, JOHAN B, WILLIAM F V. The viability of local payments for watershed servic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atiguás, Nicaragu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 74: 169-176.
[34] 張翼飛, 陳紅敏, 李瑾. 應用意愿價值評估法科學制訂生態補償標準[J]. 生態經濟, 2007(9): 28-31.
[35] 張志強, 徐中民, 程國棟, 等. 黑河流域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恢復的條件價值評估[J]. 生態學報, 2002, 22(6): 885-893.
[36] KUMAR P. Capacity constraints in operationalisation of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in India: evidence from land degradation[J]. Land Degradation & Development, 2011, 22(4): 432-443.
[37] DAILY G C, MATSON P A.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theory to implement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105(28): 9455-9456.
[38] 謝高地, 甄霖, 魯春霞, 等. 一個基于專家知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J]. 自然資源學報, 2008, 23(5): 911-919.
[39] 牛叔文, 曾明明, 劉正廣, 等. 黃河上游瑪曲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估算和生態環境管理的政策設計[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6, 16(6): 79-84.
[40] 劉青, 胡振鵬. 東江源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經濟價值研究[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7, 16(4): 532-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