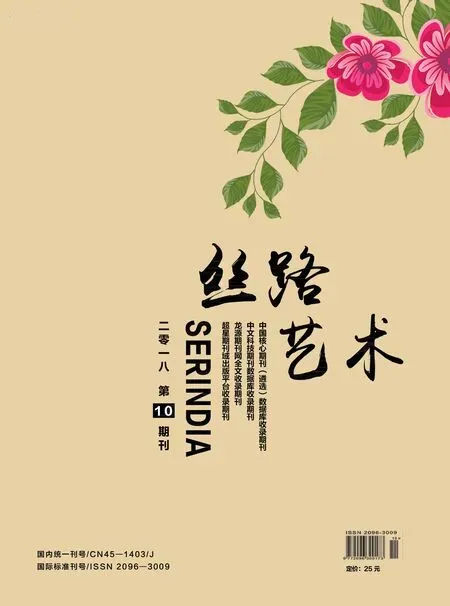《白鹿原》中白嘉軒的人物形象分析
辛達(dá)(曲阜師范大學(xué),山東 濟(jì)寧 273165)
引言:《白鹿原》的開篇引用了巴爾扎克的這樣一句話:“小說(shuō)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民族的秘史。”通過(guò)對(duì)作品中的關(guān)鍵人物白嘉軒的分析,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作品以及作品反映的特定時(shí)代。白嘉軒作為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表現(xiàn)出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道德的兩重性,對(duì)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分析,能夠引起我們對(duì)于個(gè)體命運(yùn)和民族命運(yùn)的深刻思考。
一.“耕讀傳家”的信奉者
(一)“耕”——對(duì)土地愛得深沉
處于關(guān)中腹地的的白鹿原“水深土厚,民風(fēng)淳樸”,在白鹿原上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白嘉軒對(duì)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他深信耕作是立業(yè)之本,他是一個(gè)終生都不肯脫離土地和勞動(dòng)的地地道道的農(nóng)民。白孝文賣房賣地,他表面上不動(dòng)聲色,實(shí)則痛心疾首;在挺直的腰板被打折之后,“凡是用雙手和腿腳操作的農(nóng)活他都不忌諱”“耕棉田翻稻地鍘谷草旋篩子掌簸箕送糞吆牛車踩踏軋棉花等秋冬季農(nóng)活,他和兒子孝文長(zhǎng)工鹿三一起搭手干著”,這反映了他對(duì)土地和農(nóng)活的熱愛;當(dāng)朱先生讓他辭掉長(zhǎng)工自耕自食時(shí),他只聽了先生一半的話,辭退兔娃并撂給他二畝地,“可其余的土地怎么也舍不得撂給旁人”。
(二)“讀”——尊師重教
1.創(chuàng)辦學(xué)堂
白嘉軒成為族長(zhǎng)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創(chuàng)辦學(xué)堂,他要讓兩個(gè)兒子以及本原上的其他農(nóng)家子弟都接受啟蒙教育,這在思想相對(duì)落后封閉的封建社會(huì)可謂是了不起的行為。
2.尊重先生
從全文來(lái)看,白嘉軒對(duì)他的姐夫朱先生懷著由衷的敬意,遇到事情的時(shí)候他會(huì)謙虛地請(qǐng)教朱先生,在學(xué)堂創(chuàng)辦之后,他去請(qǐng)朱先生給推薦一位知識(shí)和品德都好的先生來(lái)教授孩子們的知識(shí),體現(xiàn)了他對(duì)知識(shí)和老師的尊重。
尊師重道正是儒家思想在白嘉軒身上的體現(xiàn)。
二.“學(xué)為好人”的敦厚儒者
(一)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仁”“義”思想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儒家思想認(rèn)為如果一個(gè)人做到了“推己及人”,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白嘉軒的處世之道正體現(xiàn)了儒家“仁者愛人”的思想。
1.對(duì)鹿三不離不棄
鹿三是白家兩代的唯一長(zhǎng)工,雖然和白嘉軒地位懸殊,但卻被白嘉軒如親兄弟般對(duì)待。在鹿三為被田小娥“妖鬼附身”變得呆板遲滯后,白嘉軒并沒(méi)有嫌棄他,而是對(duì)他悉心照顧,當(dāng)發(fā)現(xiàn)兔娃訓(xùn)斥鹿三的時(shí)候,他冷著臉告誡兔娃“說(shuō)話看向著點(diǎn)哇娃子!那是你——大!”;兒子孝武娶媳婦時(shí),他不忘把鹿三請(qǐng)來(lái)。可以說(shuō),在白嘉軒的心中,他早就把鹿三當(dāng)成了一家人。
2.以德報(bào)怨的仁者思想
黑娃小時(shí)候白嘉軒資助他上學(xué),但是黑娃成為土匪后卻打折了白嘉軒曾經(jīng)挺直的腰板,然而白嘉軒并沒(méi)有記恨在心,而是在黑娃落入國(guó)民黨的手中后為了救他奔走呼號(hào);對(duì)于他的老對(duì)頭鹿子霖,白嘉軒始也始終懷著寬恕的仁者姿態(tài)去對(duì)待他,在他早已經(jīng)弄清了兒子孝文墮落的原因后,面對(duì)鹿子霖的鋃鐺入獄他仍然施以援手,他等到了鹿子霖身敗名裂的最好時(shí)機(jī),他本可以幸災(zāi)樂(lè)禍甚至落井下石,可是他沒(méi)有,因?yàn)樗谠诎茁勾迥酥琳麄€(gè)原上樹立一種精神,他要讓所有的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樣為人處世,怎樣待人律己的。
子貢曾問(wèn)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白嘉軒用他以德報(bào)怨的寬廣心胸踐行著儒家思想中的精華。
(二)閑看花開花落的處變不驚
白嘉軒的肚子里沒(méi)有多少筆墨,所以他看不懂古人留下的名言警句,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xué)。他認(rèn)為世事就是福禍兩個(gè)字,“凡遇好事的時(shí)光甭張狂,張狂過(guò)頭了后就有禍?zhǔn)拢环灿龅降準(zhǔn)碌臅r(shí)光也甭亂套,忍著受著,哪怕咬著牙也得忍著受著,忍過(guò)了受過(guò)了好事跟著就來(lái)了”,因?yàn)橛辛藢?duì)人生苦樂(lè)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才能處變不驚,做好自己該做的一切。兒子孝文在聽聞黑娃把老和尚的頭鍘掉后驚慌失措,可是白嘉軒鎮(zhèn)定自若,告誡兒子“要亂的人巴不得大亂,不亂的人還是不亂”,他將粗大的巴掌重重地拍擊到軋花機(jī)的臺(tái)板上;當(dāng)他充分預(yù)感到混亂的來(lái)臨,也做好了應(yīng)對(duì)的策略——處事不亂,他自信未做過(guò)損人之事,所以不會(huì)遭到報(bào)應(yīng);在白鹿兩家的問(wèn)題上,他的平靜和鹿子霖的偏激狡詐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鹿子霖設(shè)計(jì)拉孝文下水,孝文賣房賣地,他能夠談笑自若;鹿子霖被捕入獄,他又出手相救。
歷盡滄桑后的處變不驚,讓白嘉軒這一任務(wù)形象就有獨(dú)特的人格魅力。
(三)剛強(qiáng)堅(jiān)毅的硬漢品格
孔子提出“剛毅木訥近仁”,《易經(jīng)》中直接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的觀點(diǎn),觀全文可發(fā)現(xiàn),白嘉軒剛強(qiáng)不屈的精神正是這種思想的體現(xiàn)。白嘉軒一手策劃了“交農(nóng)事件”,帶領(lǐng)人民用行動(dòng)反抗官府的橫征暴斂;“白腿烏鴉”進(jìn)白鹿原后,面對(duì)楊排長(zhǎng)的威脅,他不屈不撓,堅(jiān)持“虧心的事不能做,沒(méi)道理的鑼不能敲”;即使曾經(jīng)筆直的腰桿被打折使得他活像一只狗,他也依舊“佝僂著腰仰面看人”,折腰給愛面子的白嘉軒的打擊是巨大的,可他倔強(qiáng)的性格告訴他,精神的脊梁必須是直的。
三.白嘉軒命運(yùn)的悲劇性
白嘉軒身處于封建政權(quán)瓦解的時(shí)期,但他的內(nèi)心仍然堅(jiān)守著封建文明,他被封建文化道德所禁錮的身心,與他命運(yùn)中的悲劇性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鹿三的一句“嘉軒,你好苦啊”道出了白嘉軒被痛苦奴役的一生。
(一)親情的缺失
白嘉軒作為威嚴(yán)的族長(zhǎng),為了維護(hù)傳統(tǒng)道德,甚至壓抑了他的人性。他喜愛自己的兒子,卻說(shuō)不出親熱的話、做不出親昵的表示;白孝文犯錯(cuò)后他雖然痛心疾首,卻仍然對(duì)兒子施以嚴(yán)厲的懲罰,與一向看重的長(zhǎng)子斷絕關(guān)系;他疼愛女兒,卻在女兒做出違背祖訓(xùn)的事情后, 又與女兒斷絕關(guān)系,他不得已而變得殘酷,當(dāng)聽到白靈的死訊后他“渾身猛烈顫抖著哭出聲來(lái)”。親情的逐漸疏遠(yuǎn),讓白嘉軒命運(yùn)的悲劇意蘊(yùn)更加濃烈。
(二)面對(duì)時(shí)代變革的困惑
腰板被打折帶來(lái)的痛苦與屈辱只是暫時(shí)性的,真正的悲哀是他在那個(gè)風(fēng)云變化的時(shí)代中越來(lái)越迷失了自己,不得不發(fā)出無(wú)力回天、好自為之的感嘆,他窮其一生捍衛(wèi)的儒家道德與文化傳統(tǒng)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他也陷入深深地困惑之中。
利昂·塞米利安曾這樣寫到“我們看一部小說(shuō),主要看小說(shuō)中對(duì)人物性格的揭示,這是構(gòu)成小說(shuō)的魅力和教育意義的因素。”通過(guò)對(duì)白嘉軒形象的分析,我們能夠更了解《白鹿原》這部偉大的作品,透過(guò)白嘉軒,我們看到特定社會(huì)歷史時(shí)期中國(guó)人的品性,尤其是白嘉軒身上所具有的優(yōu)秀的儒者品格,對(duì)當(dāng)代人和當(dāng)代社會(huì)對(duì)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