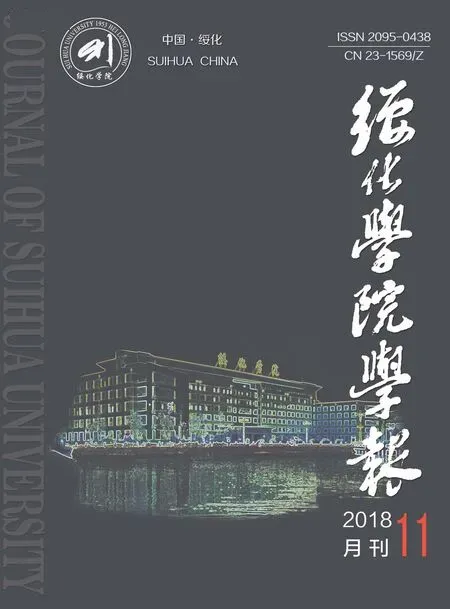略論中國古代嘲謔文學的流變
楊 芃
(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 安徽蕪湖 241100)
一、先秦時期:諧而不虐,寓莊于諧
我國最早關于嘲謔文學的記載,源于《詩經》。在此之前的文字記載,多為對重大事件的簡單記錄或求神問卜,絕少有調笑戲謔性的文字。由此可見,當時的上層社會是幾乎沒有嘲謔可言的,而在《詩經·國風》中則有許多作品具有詼諧幽默的風格。《衛風·淇奧》中以“寬兮綽兮,騎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來形容胸懷寬廣,善于說笑,舉止得體的君子才是惹人喜愛的;《邶風·終風》有“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描寫青年男女見面后相互嬉鬧的景象;《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更是記錄了男女相謔,互贈芍藥的情景。從中可知,在當時的人際交往中,打趣和玩笑已十分普遍,即便玩笑中附帶一些嘲弄之意,也不失為一種對情趣的追求。《詩經》中的某些作品,還詳細描寫了這種調笑戲謔的情景。以《豳風·狼跋》為例,聞一多認為,這首詩的作者正是公孫的妻子,意在嘲弄丈夫身袍寬大,體態臃腫,行動不便。他表示,詩人對于公孫的態度是“一種善意的調弄。”[1]這種無傷大雅的調侃與逗趣,將“諧而不虐”的風格發揮到極致,打造輕松歡樂的整體氛圍。
不僅如此,“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現后,諸子百家著書立說,其中也不乏嘲謔性的文字:《論語》中既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之教,也有“老而不死是為賊”之罵,前者嚴肅正理,后者不失詼諧;《孟子·公孫丑上》中有“揠苗助長”的可笑者,《滕文公下》有明知偷盜非君子所為卻還要“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的攘雞者;《荀子·非相》把儒家先賢的相貌寫得千奇百怪堪稱小丑,而將桀紂之君的儀容說得高大威猛玉樹臨風,令人啼笑皆非;《韓非子》中有人守株待兔,有人買櫝還珠,盡顯嘲弄之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故事雖帶有荒謬嘲諷之意,但最終都服務于諸子各自的思想態度和政治主張。孔子對原壤“老而不死是為賊”的責罵建立在“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論語·憲問》)的基礎上,可見孔子對“禮”的重視,與其積極有為的處世態度;孟子則是以“揠苗助長”說明“養氣”須得循序漸進,用“攘鄰雞者”說明“去關稅之征”不可拖拖拉拉;荀子通過圣賢丑貌而昏君俊顏的對比證明了“論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荀子·非相》)的道理;而法家作為戰國后起之秀,提倡改革,謀求功利,所以韓非用守株待兔、買櫝還珠來嘲笑刻板守舊、舍本逐末之人。很顯然,這些思想家本無意專門嘲笑他人,只是借此表達自己的思想主張,以一種“寓莊于諧”的方法更快地求得他人的認可和君主的任用。
除此之外,嘲謔性的語言還時常見于外交場合。晏子出使楚國,面對楚王的嘲諷,他用委婉玩笑的方式成功自衛,巧妙回擊,既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和齊國的國格,又不會傷了雙方和氣,阻礙兩國交往。又有戰國時秦宣太后公然對外交使臣講黃段子:“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戰國策·韓策》)意思是幫助韓國代價太大而好處太少,不是一筆好買賣。床幃之事本是夫妻私事,以房事喻國事,也是典型的寓莊于諧。不難看出,先秦時期的嘲謔文學除了調笑戲謔外,更加具有思想性與政治性。
另外,將調笑、戲謔作為本職工作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的專門負責取悅統治者的俳優。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群以滑稽調笑為本職工作的人,卻往往以“戲言”的方式實現了對現實的考察和干預,形成了意義深遠、備受好評的“優諫”傳統。當然,俳優不能算作純粹意義上的文學。但其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群體,對后世嘲謔文學的創作和發展影響深遠。
二、兩漢時期:表達自我,追求娛樂
與先秦時期相比,兩漢時期的嘲謔文學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是在戲謔、游戲的筆調中加入了對自身價值的思考和自我命運的反思,其二是對娛樂特性的自覺追求。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說立而經學時代始。”[2]在這種大環境下,“士”的地位相比之前有所下降。他們不再需要滔滔雄辯,不再可能“為帝王師”,而只能做建言獻策的參與者,或是吟詩作賦的調劑品。漢武帝時期以滑稽聞名的文臣并不少,東方朔更有“滑稽之雄”的稱號。而在東方朔的文章里,除了機智調侃式的滑稽之語,更可以看到他對自我價值的思考和尷尬處境的自嘲。
一方面,他在《上書自薦》中寫道:“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責,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3]自認為是高大英俊無所不通的完美人才。這種大肆渲染極盡夸張的自我吹捧近乎戲言,讓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他又因不被重用而寫了《答客難》。在這篇以“懷才不遇”為主題的作品里,很難見到作者對社會的不滿與鞭撻,反而對當今社會給予高度贊美:正是由于當今社會君主圣明,國泰民安,和春秋禮崩樂壞戰國諸侯爭霸不同,即使是蘇秦、張儀、樂毅、李斯之流在今天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自己好歹官至侍郎,而這些名臣在今天可能還不如自己呢這種先自夸再自嘲后自慰,既滿腹牢騷又歌功頌德的寫法,本身便充滿了調侃幽默的意味,其中更有在時移世易的環境下對“士”階層處境和出路的思考。與此相似的是揚雄的《解嘲》,同樣是以滑稽諧謔的筆調發泄心中牢騷,劉勰曾評價揚雄此文:“雜以諧謔,回環自釋,頗亦為工。”[4]在《逐貧賦》中,揚雄借乞兒之口與“貧”交流,描寫了由“貧”帶來的種種困擾和“貧”具有的種種好處,通過從“逐貧”到“留貧”的態度轉變,表達了自己甘于清貧自守的價值選擇,于詼諧談笑中完成對自我的反思。
除此之外,漢代嘲謔文學也有對娛樂的自覺追求。《漢書·東方朔傳》中,就記述了東方朔和郭舍人打謎互嘲的過程,其目的就是取悅皇帝,爭取寵幸;[3](P2844)王褒《僮約》寫自己與仆人的爭執表現出一種脫離政治遠離宮廷的生活化調弄。東漢時期儒學的神圣化和讖緯之說的盛行,一度使嘲謔文學歸于沉寂。直到漢末時由于儒學禮教的松弛和統治者的娛樂需求,使得嘲戲之風又起,出現了一批篇幅短小的嘲戲形貌的作品,如戴良《失父零丁》、蔡邕《短人賦》等,都是拿別人容貌玩笑取樂的作品,這類作品沒有什么深刻價值,但帶有明顯的游戲娛樂傾向。
三、魏晉時期:擺脫束縛,迂回反抗
《文心雕龍·諧隱》有言:“魏晉滑稽,盛相驅扇。”[4](P89)可見魏晉時期嘲戲之風大熾。此一時期還出現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笑話集《笑林》,《文心雕龍·諧隱》更是第一次對諧謔性的文字做出了理論總結。魏晉南北朝時依然存在大量篇幅短小的“嘲人賦”:如劉思真《丑婦賦》專門嘲笑女子貌丑;朱彥時《黑兒賦》嘲弄別人皮膚黝黑……這些作品與東漢《失父零丁》、《短人賦》等如出一轍。但是,魏晉時期的嘲謔文學又不單單是上一時期的簡單復制,它有其自己的特點,即擺脫束縛,迂回反抗。魏晉文人的一言一行往往流露出一種“擺脫束縛,保持我素”的態度,即使在嘲謔時也不例外。這一點在《世說新語》里有明確體現:
“王渾與婦鐘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5]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5](P494)
元帝喜得貴子,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勛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勛邪?”[9](P486)
從以上幾則記載中不難發現,魏晉時期的人們早就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原則,妻子可以揶揄丈夫基因不好;孩子可以對長輩反唇相譏;甚至皇帝也會拿自己的子嗣與臣子開玩笑可謂毫不避諱,隨性言語。曹丕與大臣之間的往來書信也不乏笑語,如《借取郭落帶嘲劉禎書》和劉禎《答魏太子曹丕借郭落帶書》完全以嘲戲為之,沒有一般的君臣對話那樣等級分明。甚至對可能改變天下局勢的軍政大事,也可調侃一番,裴松之注《三國志·鐘繇傳》引用了《魏略》中的一段記載:孫權向曹魏稱臣后又獻上關羽首級,太子曹丕在與鐘繇的書信中提及此事,鐘繇回信曰:“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6]因孫權已經臣服又斬殺關羽,鐘繇便用“了更嫵媚”形容昔日敵人,字里行間充滿笑謔,完全是有意拿昔日政敵打趣。
魏晉時期的散文創作也多嘲謔之筆。曹丕評價孔融的文章:“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7]劉勰也說他“但談嘲戲”[7](P119),錢鐘書先生也評價過孔融的嘲戲略似“《史記·滑稽列傳》所載微詞譎諫”[7],但兩者雖在手法上有相近之處,前者卻更具攻擊性和反抗性。以《圣人優劣論》為例,其將圣人喻為“狗馬”,用“狗馬”之行有先后暗示圣人之中有優劣,手法高明,戲謔中可見其對虛偽禮法的反抗。
總體說來,魏晉思想解放,崇尚自我,許多文人都對動蕩不安、虛偽黑暗的統治失望不已。然而,并不是每個人都如嵇康般慷慨任俠,更多的時候,“嘲謔”便成為一種手段,讓他們在謔浪笑敖中“非湯武而薄周孔”。相比較而言,兩漢的文人常常以玩笑嘲弄的口吻發牢騷,而到了魏晉,牢騷漸漸變成了一種迂回曲折的抗爭。但無論如何,從先秦到兩漢再到魏晉,嘲謔文學一直在“自覺”的道路上快速發展。
四、唐宋時期:無所不謔,雅趣十足
唐宋時期作是封建社會物質精神文明之高潮期,嘲謔之風得以延續。這一時期的嘲謔文學數量豐富,包羅萬象,幾乎達到無所不謔的程度。
首先,嘲謔文學作品的體裁呈現多樣化的特征。幾乎每一種文學體裁中都有大量的嘲謔文學作品。《全唐詩》中有“諧謔”四卷,幾乎都是娛樂調笑性的作品對宋代諧謔詞的發展進行記載的是王灼的《碧雞漫志》:“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于至和……娛戲污賤,古所未有。”[8]韓愈散文亦有“以文為戲”的特色,他的《毛穎傳》被認為是“以文滑稽”,《送窮文》被黃庭堅稱為“諧戲”,《進學解》被看成“《送窮》之變體”;同期柳宗元也有此類名篇,如《愚溪對》《乞巧文》等,亦頗具“以文為戲”的風采。小說方面,唐代的很多筆記小說都為嘲謔性的文字設有專章,在《本事詩》中有“嘲戲第七”,在《因話錄》中有“諧戲附”,《唐摭言》有“輕挑戲謔嘲詠附”,宋人李昉的《太平廣記》中有“嘲誚”“詼諧”類,也記載了很多唐代的嘲謔故事。另外,戲劇領域也不乏嘲謔的內容。劉大杰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所謂參軍,便是戲中的正角……兩者相互問答,其作用則調謔諷刺,兼而有之。”[9]
其二,參與嘲謔或從事純粹嘲謔文學創作的群體擴大。《隋唐嘉話》中就記載了唐太宗宴請眾臣,相互嘲謔打趣的故事,[10]《本事詩·嘲戲》記載有優人唱《回波詞》調侃唐中宗怕老婆,還有長孫無忌和歐陽詢兩位名臣互相嘲弄對方外貌身材的掌故。[11]宋代歐陽修與眾多禮部大臣的所寫的唱和詩即“時發于奇,雜以詼嘲笑謔。”[12]在這里,王公重臣都是成了嘲謔性事件的發起人或當事者,而不再僅僅是中下層文人或俳優們需要取悅或諫言的對象。
再者,唐宋時期嘲謔文學的交游功能開始凸顯,出現了大量的戲贈詩。這種詩唐前很少,唐初亦未成風氣,但中唐白居易的詩集中多有“朋友戲投”之詩,到宋代廣泛流行于各大詩人、詩派之間,有蔚然成風之勢。[12]這種詩記載著朋友之間的交流往來,內容也就更加日常化、細碎化。如《圣俞墜馬傷臂以其好言兵調之》《順之將攜室行而苦雨用前韻戲之》《聞曼叔腹疾走筆為戲》《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等。詩中描寫墜馬、下雨、生病、納妾等多種場景,完全是對生活瑣事的有心記錄。總之,無論是從體裁、題材還是參與者的角度,都不難看出唐宋時嘲謔文學無所不謔的特點。
此外,唐宋時期的嘲謔文學體現出明顯的“雅化”特征。首先是思想內容雅。韓柳散文中的許多戲言都是對自身經歷和士人命運的一種感慨,帶有濃重的“感士不遇”色彩。如果說韓愈、柳宗元等人的“以文為戲”還可看作是對東方朔、揚雄等人譏時書憤、自慰述志風格的繼承,那么興于唐盛于宋的“戲贈詩”與前代“嘲人詩”相比,確實是一大進步。“嘲人詩”幾乎都是以嘲謔人的生理缺陷為樂,大有“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之嫌唐宋時戲贈詩則更能給人以風趣活潑之感。如李白自己嗜酒成癖,就調笑不喝酒的朋友,寫了《嘲王歷陽不肯飲酒》;李白作詩援筆立成,便用“離別之后太瘦生,仍為之前作詩苦”來調侃杜甫為作詩而折騰自己的身體;南宋楊萬里和尤袤之間更有“尤楊雅謔”的故事傳世。[13]于其他日常題材中,唐宋時人也頗見雅意。如岑參“道旁榆芙仍似錢,摘來沽酒君肯否”將買酒賴賬描繪得清新脫俗;羅隱“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流連風月也可自抒懷抱。即使面對“老之將至”這樣殘酷的主題,唐人都可以生出喜悅之情,寫出《覽鏡喜老》《喜老自嘲》這樣的詩篇,絲毫不見遲暮之悲。另外,宋人喜“以理入詩”,即使是調笑性的詩篇也不例外。如蘇軾《薄薄酒二首并引》,雖然在序言中說明“可發覽者之一噱”,但也充滿了冷雋深沉的歷史性反思和一種道家式的理想主義人生觀。
其次是表現手法雅。唐宋文人嘲謔,除了常用的比擬、夸張等修辭外,在手法上加入了更多“書卷氣”。時而拆解文字:唐時狄仁杰調侃同朝為官的盧獻:“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乃是煮熟狗。’”[10](P134)時而歪解詞句:“蘇軾夜讀《阿房宮賦》,二老兵事左右,不堪其擾,夜不能寐。一人抱怨:“知他有甚好處?”又一人曰:“有好句一者,吾獨愛‘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14]時而引經據典:如某日尤袤對楊萬里說:“楊氏為我。”(語出《孟子》)楊萬里回應:“尤物移人。”(語出《左傳》)時而運用典故:辛棄疾《卜算子·齒落》一詞:“說與兒曹莫笑翁,狗竇從君過”借《世說新語·排調》之典故,《卜算子·用莊語》“一以我為牛,一以我為馬”用《莊子·應帝王》中的秦氏故事……這些帶有“書卷氣”的手法,無疑更使唐宋嘲謔趨于雅化,尤其是“使典為戲”這一條,正是宋人好以才識學問作詩這一特點在嘲謔文學領域的體現。
五、元明清時期:由雅轉俗,笑罵世情
元明清時期嘲謔文學由雅轉俗的特征,從嘲謔文學的體裁上便可見一斑。元曲不僅使元代文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古代俗文學的代表之一。嘲謔性的散曲在元代屢見不鮮,笑話作為俗文學的又一代表,更是嘲謔文學的集中體現,在明清兩代取得了長足發展。笑話集在魏晉時期就已出現,但數量不多,有些已經散佚,唐宋時期的笑話大多都是由文人創作,常常涉及真人真事,內容大都是當時的文壇掌故或野史趣聞,對民間通俗笑話記錄不多,而明代文人則不避俚語笑談,不廢滑稽科諢,崇尚詼諧調侃。[15]而明清時期的笑話集往往“更具有通俗性,即使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也不能改變它作為民間文學的根本特性。”[16]元明清的小說戲劇中亦不乏嘲謔,但篇幅較長,本文中暫不討論。
元明清嘲謔文學由雅轉俗,在內容上表現為對“傳統”的消解和對“淺俗”的自覺追求。元曲語言的通俗性自不必多說,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明時期,文壇中出現了文學思想多元并存的局面,其中之一就是追求真情與淺俗。嘉靖年間,徐渭、李開先等人都有意追求詩歌創作的通俗淺近,這種風格在戲謔性的詩作中體現得更加明顯。[17]到萬歷時期,衍生出“以文為戲,適俗療俗”的文學思想,[17](P809)馮夢龍《古今譚概》《笑府》等笑話集相應問世。明代笑話集中的部分笑話語涉猥褻,鄙陋下流,這一方面是作者本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是迎合底層人民的娛樂需求,同時還是晚明淫逸世風的真實體現。
清朝時,性靈派詩人袁枚曾作詩嘲謔翁方綱的詩學主張:“天涯有客號泠癡,誤把抄書當作詩。”[18]自己作詩也力求通俗:“手制羹湯強我餐,略聽風響怪衣單。分明兒鬢白如許,阿母還當襁褓看。”[19]雖有點打油詩的味道,但玩笑之中亦體現人間至情。
同樣是懷才不遇的牢騷詩,鄭板橋曰:“教館本自是下流,傍人門戶度春秋……課少父兄嫌懶惰,功多子弟結下冤仇……”[20]直接表達對生活現狀的不滿,和兩漢、唐宋時期將不滿與牢騷匿于歌功頌德、安貧樂道等情緒之下的含蓄風格大相徑庭。即使同是使典為詩表達同一主題,典雅與淺俗也一目了然。蘇軾和徐渭都曾經作詩嘲謔張姓朋友老年納妾的行為,詩中均含有大量典故。試比較二詩末句,蘇詩曰:“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徐詩曰:“正宜七十張公子,夜夜香衾比目魚。”[21]雖都是用典,但后者更加直露淺白。
元代以后嘲謔文學的另一特點是笑罵世情。這段時期的嘲謔類作品的社會性和諷刺性較唐宋時期而言無疑大大增強。中國文學的諷刺特點早已有之,早在先秦時期的《詩經》便有“美刺”傳統,《相鼠》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碩鼠》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甚至《尚書》中還有要和統治者同歸于盡的憤恨,如“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然而這些詩文都毫無戲謔之意。而將諷刺與嘲謔相結合,所產生的效果必定介于強烈的攻擊性與溫軟的調侃性之間,將“咒罵”變為“笑罵”。元代時散曲盛行,其中多有描述官員收受賄賂之作:“那的是為官富貴,只不過多吃些宴席,更不呵安插些舊相知,家庭中添些蓋作,囊篋里攢些東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16](P144)表面好似為官家辯護之詞,實則有揭露之意。明代詩文里也不乏詼諧嘲謔的諷刺作品。小品文領域,王思任、顧大韶、沈承等人也都有許多滑稽生動的諷刺之作,但是,最能體現“笑罵世情”這一特點的,還是明清之際的笑話。明清時期的笑話是諧謔與諷刺的結晶。除了上文所說某些粗俗猥褻的笑話反映了晚明縱欲放蕩的社會風氣之外,明清笑話還以嘲謔的方式,反映了更廣闊的社會內容,表達了人民群眾的愛憎心理。官府的黑暗,科舉的弊病,世風的敗壞,常常成為明清笑話的“笑罵”對象。描寫官員貪得無厭:“來時蕭索去時豐,官帑民財一掃空;只有江山移不去,臨行寫入畫圖中。”[22](P315)描寫不懂裝懂的監生:“有督學策問“姚江學術”,監生回答“有謂江之學勝于姚者,有謂姚之學勝于江者,似難分其優劣。”[22](P519)在調侃戲謔的背后,反映出科舉制度的僵化與變質。晚明的世風日下在笑話中也有充分體現,不但官員貪得無厭,商人唯利是圖,就連普通百姓也吝嗇到一毛不拔的境界。父親溺水,兒子呼救。父親命懸一線時仍不忘叮囑:“是三分銀子便救,若要多莫來。”[23]除了吝嗇至極以外,更有和尚誘人妻女,道士坑蒙拐騙,娼妓只問金錢,道學先生頑固迂腐……農商百工、富人乞丐、盜賊無賴等都成了可笑之人,成了被“笑罵”的對象。這些笑話雖然也有批評譏刺之意,但少有“予與女偕亡”的強烈憤恨,而是用一種插科打諢的方式表現出來,讓人看到其中荒誕丑拙的一面時首先感覺到可笑。
綜上所述,嘲謔文學在先秦時期就已存在,歷經漢魏、唐宋、元明清各朝,直到今天尤未斷絕。各代嘲謔文學因受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總的來說,在先秦時期可以說是嘲謔文學的萌芽期,在百家爭鳴時期由于政治和學術的需要,常被當作申述主張的工具;漢魏時期嘲謔文學的娛樂功能開始體現,同時,已有文人將嘲謔作為表達身心情感的手段加以運用,使其走向自覺;唐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物質精神文明的高潮期,此時的嘲謔文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內容更加廣泛,手法更加多樣,處處透著文人雅趣;及至元明清三代,封建社會高潮期已過,文人失去了優游生活的土壤,雅文學衰落,俗文學發展,嘲謔文學也不可避免地由雅轉俗。再者,明清時期已是封建社會末期,各種弊端日漸顯露,整個社會百病叢生。嘲謔文學在調侃戲謔引人發笑之余,亦發揮出投槍匕首似的刺世功能,體現出笑罵世情的風采。直到今天,嘲謔文學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說,嘲謔文學不僅是生活的調劑品,還是研究社會世情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