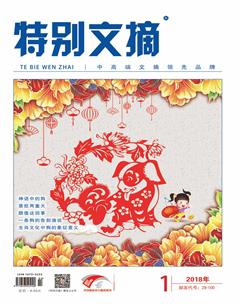秋聲乍起 最宜飲茶
潘向黎
疲勞類似于微醺,而連續七天工作的疲勞,是薄醉了。10月15日,寶貴的休息日。睡眠的主要作用不是充電而是清空,通過切斷白天辛苦的思維和各種夢的釋放,將所有的壓力送入另一個空間。然后醒來,迷迷糊糊地覺得一切都還來得及。
秋天了,天薄陰。滿屏都是諾貝爾文學獎和鮑勃·迪倫,初聽見這個消息,自然是瞪大眼睛的,然后便笑起來了。一半藝術,一半娛樂,多么好。除了極少數睡里夢里也想獲獎的人,所有人都在笑,多么好。
諾獎不諾獎,民謠不民謠,吃茶去。我喝我的茶。
用一柄掌心大小的淺豆綠色段泥壺,樣子是一粒珠,壺鈕下多一圈柿蒂紋,色調和式樣,泡大禹嶺都很適宜;壺嘴短,出湯非常暢快,不用濾盞,直接斟進天青色龍泉杯里,水聲泠泠悅耳,方覺清香繞鼻,又見色澤悅目,啜一口,口腔頓時蘇醒,再一口,喉嚨里隔夜的悶氣也散了,一時間五感全開,有幾分重新做人的喜悅。
秋天了,我已經不能喝綠茶了,這么些年,向來只有夏天一季能喝一些綠茶,入了秋,就都是烏龍茶,由秋入冬,則一半烏龍茶一半紅茶。烏龍茶系列很多,各有妙處,比如眼前的大禹嶺,香高而清爽,滋味爽利而歸于圓潤溫文,不像凍頂那么撲烈鈍重,也不像武夷巖茶般帶一些荒涼蠻力,特別適合充當早上的“還魂茶”。
隨手拿起顧隨先生的書,一讀,又處處覺得他可愛。
“唐人詩不避俗,自然不俗,俗亦不要緊。宋人避俗,而雅得比唐人俗得還俗。”做人也是如此,有的人刻意避俗,結果讓人發現其俗在骨;若是認定“俗也不要緊”,就不會起念造作,自然就舉止大方。
說到“大方”,顧隨說初唐作風,有一點“是氣象闊大,后人寫詩多局于小我,故不能大方”。局于小我,是小氣;氣象闊大,才是大方。
“‘定于一是靜,而非寂寞。”此語是極。如今往往苦于不得清靜,日日嘈雜,心里反而寂寞。
說李白《烏棲曲》“東方漸高奈樂何”一句“不通”。但是李白是用古樂府的《有所思》中“東方須臾高知之”句呀,顧隨誰的面子都不給,直批“古樂府此句亦不好解”。真正的學問家,在于別人看不明白的地方他看得明白,別人都自以為明白或者不明白裝明白之處,他敢于說出其實根本看不明白。
關于讀書人,他說“一個讀書人一點‘書氣都沒有,不好;念幾本書處處顯出我讀過書,也討厭”。這是真話,卻率真任性,令人莞爾。
他又說王維,說王右丞的詩韻長而格高、境高,“雖寫起火事,而心中絕不起火”,但“古書中所謂‘高人,未必是好人,也未必于人有益”。他拿陸游來對比——“放翁所表現的不是高,不是韻長,而是情真、意足,一摑一掌血,一鞭一條痕”。從未想過,醍醐灌頂。
杜甫的“莫思身外無窮事,且進生前有限杯”,一般人看作牢騷,或者無奈頹唐之語,顧隨卻說這看似平常,其實“太不平常了”。“現在一般人便是想得太多,所以反而什么都做不出來了。‘莫思身外無窮事是說‘人必有所不為,‘且進生前有限杯時說‘而后可以有為。”別出新解,啟人新思。
他說中國文學缺少“生的色彩”,欲使生的色彩濃厚,須有“生的享樂”“生的憎恨”與“生的欣賞”,“不能鉆入不行,能鉆入不能撤出也不行。在人生戰場上要七進七出”。這樣的話,我等虛弱怯懦、“不中而庸”的人,連擊節都不配。
顧隨是藝術和人生天真赤誠的熱戀者,所以他有骨氣、血氣、孩子氣而沒有仙氣,他說“人生最不美、最俗,然再沒有比人生更有意義的了”。從未讀過、聽過這樣徹底的話,用《紅樓夢》里的話說,真是叫人“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
“人要自己充實精神、體力,然后自然流露好,不要叫囂,不要做作。”謹記了。
可是“充實精神、體力”非一日之功,過了午,又倦怠起來,而且無端有點煩悶。何以解悶?唯有喝茶。
武夷巖茶吧,正好有極好的“牛肉”。牛肉?不飲武夷茶的人乍聽必定愕然:喝茶怎么喝出牛肉來了,難道還要喝馬肉嗎?正是,還有“馬肉”呢。其實“肉”是武夷巖茶中的一個品種“肉桂”,因產于牛欄坑和馬頭巖的均負盛名,熱衷者便以“牛肉”“馬肉”來稱呼了——“牛肉”,牛欄坑肉桂是也;“馬肉”,馬頭巖肉桂者也。這兩款茶,香氣和味道都很霸道,巖韻十足,喜歡的往往是老茶客。要說區別,“牛肉”采用傳統古法炭焙,像個上了年紀的江湖大俠,霸氣比較收斂,骨力蒼勁而持久,五泡之后骨氣不倒;而馬肉張揚爽快,是比較年輕的俠客,光明磊落,氣勢奪人。
武夷巖茶中的大多數,總有一股蒼涼山野的氣息,與江南綠茶的溫柔細膩,云南滇紅的甘甜圓潤很不一樣,飲之似有一股自由而開闊的山風迎面撲來,化作一股真氣灌注全身。
這樣的茶,在秋聲乍起的時節,尤其是有點困倦的午后,最是相宜。壺用一把曼生石瓢,簡潔的光器,一點裝飾也無,泥是八十年代的底槽青。注沸水,稍候,用濾盞濾進一個日本清水燒的小杯里,杯子里是純白的,茶湯的顏色看得很清楚,比大禹嶺的微黃要深得多了,光澤頗像琥珀,但色比尋常琥珀要深,讓我想起雨中山民穿的蓑衣。
武夷巖茶,最適合做午后的提神破悶茶。
到了晚上,茶都淡了,也不便再泡其他茶,怕攪了白天茶興的余韻,便淡淡泡了一壺正山小種,手握杯子站到陽臺上,發現不知何時天氣轉好,夜色清朗,有月,有云,云時籠月,而月有暈。不遠的地方,桂花開了,我看不見,但那種馥郁,一下子熏透人的魂魄。
明末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中有《此座》篇:“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碗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咿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鼾忽止。念既虛閑,室復幽曠,無事坐此,長如小年。”
寫這篇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盲人,但是對“虛閑”體味得比我們看得見的人更真切。
飲茶,其實是品味時間,浸在茶湯中的許多瞬間,分明感覺到:“時”是無“間”的。
一直喝著茶,卻已經是寒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