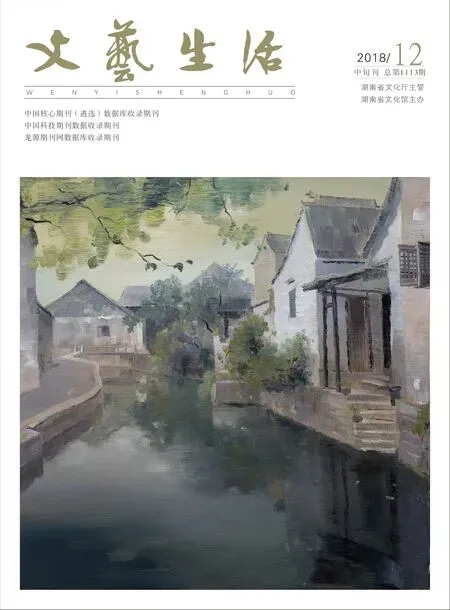淺探中國繪畫的師承
吳新榮
(上海電機(jī)學(xué)院,上海201306)
所謂“師承”就是某種藝術(shù)流派風(fēng)格繼承與流傳的線索。在具體實(shí)踐中,又有直接師承和間接師承之分。直接師承就是徒弟拜師,老師親自傳授;間接師承就是以再傳弟子為師或根據(jù)流傳作品進(jìn)行學(xué)習(xí)。老師帶徒弟教藝,徒弟拜老師學(xué)藝,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gè)傳統(tǒng)。
對(duì)于師資傳授的討論,始于初唐《后畫錄》。只有在了解師資傳授的基礎(chǔ)上,才能明了一個(gè)畫家風(fēng)格的來源,才能理解繪畫史上各種不同流派、不同風(fēng)格、不同門類的繪畫及與此相關(guān)的各種現(xiàn)象。不言而喻,初學(xué)繪畫的人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是在藝術(shù)上成功的捷徑。老師長(zhǎng)年累月的實(shí)踐,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提煉了某種物象的精華,創(chuàng)立了自具特色的學(xué)派風(fēng)格,通過老師的教導(dǎo)指點(diǎn),較快地明辨是非曲直,節(jié)省了大量的時(shí)間和精力,少走了曲折的“彎路”和“暗道”,快步進(jìn)入了藝術(shù)之門,拜上了良師,自是一大幸事。
當(dāng)然,老師的教導(dǎo)是外因,而學(xué)生的努力、悟性是內(nèi)因,外因通過內(nèi)因而起作用。孔丘是儒家之首,對(duì)他的兒子孔鯉能不悉心傳授嗎?非也。但是,孔鯉在學(xué)術(shù)上并無建樹,是他的悟性不高,缺乏創(chuàng)新能力的內(nèi)因所致。其實(shí),繪畫也是如此。
《宣和畫譜》載陸探微的兩個(gè)兒子綏洪、綏肅,因?yàn)榧覍W(xué)傳授,作畫也很工,不墜家傳的習(xí)慣,很有父親的風(fēng)度,但是終究趕不上。在學(xué)習(xí)的過程中,師承與創(chuàng)新是相對(duì)的范疇。首先,要汲取老師的經(jīng)驗(yàn)。俗話說:“名師出高徒,高徒宏師藝。”中國藝術(shù)源遠(yuǎn)流長(zhǎng),它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cái)富。師徒一脈相承,對(duì)繪畫的發(fā)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宣和畫譜》載李公麟的書畫成就并不是憑空習(xí)得。因?yàn)樗赣H喜歡藏法書名畫,從小就常常觀看,耳濡目染。他的書法作品汲取了晉、宋書法家的楷書風(fēng)格。繪畫方面學(xué)習(xí)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與吳道子及前世名手佳本,集合了各位老師的優(yōu)點(diǎn),融會(huì)貫通。
南宋的鄧椿曾在《畫繼》中把李公麟與“古今一人”的“畫圣”吳道子相題并論,可謂推崇備至。李公麟不僅能取百家之長(zhǎng),更重要的是能學(xué)為己用,推陳出新,因此既得其友人蘇軾的稱賞,認(rèn)為他是當(dāng)時(shí)畫壇“集大成”式的大家,并稱贊他“能于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
例如,李公麟《臨韋偃放牧圖》卷,則是臨摹前人之作。但是在“白描”的基礎(chǔ)上又稍作創(chuàng)新,略加色彩的渲染。傳為他所作的《維摩詰像》,從繪畫技法上說,李公麟在吳道子白畫形式上發(fā)展出了白描,他的線描簡(jiǎn)潔優(yōu)美,更著重表現(xiàn)文人士大夫優(yōu)雅的韻致。學(xué)生學(xué)習(xí)各家的優(yōu)點(diǎn),要消化領(lǐng)悟,自出新意,表面上并不像前人,而實(shí)則暗中效法他們的要點(diǎn),轉(zhuǎn)換成自己的藝術(shù)語言。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xué)習(xí)。因此,一方面老師為后來者提供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后來者發(fā)揮的余地。我們既要繼承、延續(xù)老師的優(yōu)點(diǎn),又要突破、變革老師的程式。
但是在拜師學(xué)藝的道路上,也會(huì)充滿荊棘。鐘隱為了拜師學(xué)藝,寧愿隱姓埋名到老師家服役。雖在困難之中學(xué)習(xí),仍堅(jiān)持不退。可見鐘隱為了拜在名師門下所做的努力。學(xué)到高的技藝,這點(diǎn)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在眾多畫家的師承中又有許多不同的情況,青出于藍(lán)的畫家也很多,但大都是在創(chuàng)新上下文章。
比如郭熙的山水畫本是取法李成的,但他不是自限于學(xué)李成,也不像翟院深那樣以學(xué)李成可以亂真為滿足,而是如《圖畫見聞志》所說,“雖復(fù)學(xué)營(yíng)丘,亦能自放胸臆,”終至能“于今之世為獨(dú)絕。”郭熙學(xué)李成畫法,且筆隨年進(jìn),愈老愈精,但在布置構(gòu)圖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另辟蹊徑,遂成獨(dú)步一時(shí)的畫家。
另一位是荊浩的得意門生關(guān)仝。關(guān)仝在題材上傾向秋山寒林以及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漁市山驛,景界越稀少而意思越悠長(zhǎng)。在筆法上脫落了筆墨紙張的痕跡,越簡(jiǎn)單而氣勢(shì)越雄壯。關(guān)仝在題材、筆法方面都超過老師并有自己的特色。還有石恪學(xué)張南本,技術(shù)有了進(jìn)步,便縱逸不守規(guī)矩,氣韻思致,較南本好得多。吳元瑜虛心向院畫家崔白學(xué)習(xí),取得卓越成就,他能改變富有世俗風(fēng)格的院體畫,稍稍放縱筆墨,自抒己臆,更是難得之舉。太監(jiān)樂士宣,開始獨(dú)愛金陵艾宣的畫。當(dāng)他胸中飽讀了書史,學(xué)問大進(jìn),而繪畫也趨于疏淡,乃覺悟到艾宣的畫太拘窘,于是舍去舊法,而筆遂能超越前輩。畫花鳥,尤能得其生意,艾宣比起他的畫來,就奄奄無生氣了。他們都是能突破老師的局限,自創(chuàng)新意的佼佼者。
師承對(duì)中國繪畫的繼承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畫家只有兼收并攬前人已有的成就,來提高畫家的繪畫本領(lǐng)。如果目的僅在于“留其真跡”,那么,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隨著自身藝術(shù)素養(yǎng)的豐厚,然后才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更進(jìn)一步。以繪畫傳統(tǒng)去充實(shí)畫家的藝術(shù)個(gè)性,而畫家又以自己的藝術(shù)個(gè)性去豐富傳統(tǒng),中國畫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從傳統(tǒng)中走來,從而又構(gòu)成新的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