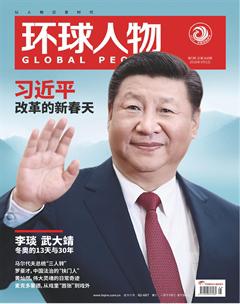陳楠把甲骨文“玩”成表情包
龔新葉
3600年前的甲骨文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都是陌生的,但如果腦洞大開,在這個全民皆用表情包的時代,把它和表情包“玩”到一塊兒,會不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呢?清華大學美院教授陳楠就做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2018年1月29日,陳楠在清華大學接受記者采訪。
研究甲骨文字體19年的陳楠,在2017年9月與漢儀字庫推出了國內外第一套“甲骨文設計字庫”,在此基礎上,他設計的《甲骨文十二生肖》和《甲骨有表情》兩套甲骨文表情包在網上意外躥紅。這套表情包將甲骨文擬人擬物,配合色彩、動畫,讓原本晦澀難解、拒人千里之外的甲骨文瞬間活潑可愛起來,其生動的形象也讓甲骨文的圖案意義躍然眼前,方便了讀者的閱讀理解。“白富美”“單身狗”“有木有”這些流行的網絡用語,紛紛用甲骨文呈現出來,令人會心一笑的同時,拉近了人與字的距離,也讓“3600年”兩端的時空更加貼近。
采訪前,陳楠將《環球人物》記者攜帶的雜志順手拿起,前后翻看,隨后他指著一個紫砂壺廣告對記者說:“‘僅有九把的‘九字特意做成棕色,因為那是紫砂的色彩;做成宋體而不是黑體,因為宋體更加傳統,能表現紫砂壺的歷史感。”當記者笑稱他“職業病不輕”時,他笑道:“這些在教學中都可以作為設計符號加以分析。”
鹿晗為甲骨文打“Call”
對于甲骨文表情包的走紅,陳楠始料未及,他的甲骨文視頻被偶像明星鹿晗轉發后,立馬引發了3400萬的閱讀量,轉發超14萬次。“我從1999年開始做甲骨文的傳播,直到前陣子才突然引起廣泛關注。我想是因為表情包是年輕人愿意接受的東西,他們的審美跟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說教式的教學他們一定會排斥。”陳楠說,“鹿晗、周杰倫這些年輕人的偶像關注了傳統文化,他們的歌迷也會順勢接受;《三國演義》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沒讀過,但通過各種三國游戲漫畫,他們也會重燃對傳統經典的興趣。甲骨文表情包走紅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陳楠和他在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秀我家鄉”設計大賽上設計的“福娃”創意產品。
“醉”字的部首“酉”本身具有酒的意思,在表情包中,酉字上方冒出幾滴酒后,醉字突然“倒下”,以示“醉了”;甲骨文里,“有”是一只手,陳楠在兩只手中間加入一個“木”字,又分別在左右手上標記“Yes”和“No”,便形成了時下的網絡用語“有木有”;而“上天”的表情,則是一個“人”字跳進“上”字后升至畫面外。網友紛紛表示“我已經不知道說什么才能表達我的驚訝了”“我去瞧瞧甲骨文的‘愛怎么寫”“寓教于樂,傳承文化,贊”……網友的反應讓陳楠感到欣慰,傳承文化正是他所期待的。“甲骨文不應該被束之高閣,想煥發傳統文化的活力,就要將它與當下人們喜聞樂見的東西相結合。”陳楠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漢字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文化脈絡不斷的保證。我希望我所做的事情能對漢字的傳承起到助益作用。”
在陳楠心目中,漢字是神圣的。在中國古代,寫過字的紙不能亂扔,要扔在紙簍里。許多村莊都會有一個“惜字塔”,專門用來焚燒寫過字的紙……“其實這些紙還能利用,比如擦拭臟物。但古人覺得這是對字的玷污,不能坐在上面,更不能踩在腳下,必須焚毀。”陳楠說,“我們不能只看到漢字記錄語言的價值,還應該關注它的文化價值。舊時過年,家境不寬裕的人家,不會鋪張浪費張燈結彩,只需幾張紅紙請村里長者或有學識的人寫上幾個墨筆漢字,對聯、福字、斗方、春條,往門上一貼,喜慶氣氛立馬就出來了。人幾乎是生活在漢字世界里的,結婚貼喜字、拜壽貼百壽圖,在商號牌幌、軍旗令箭等上面,漢字文化無處不在。”
十多年前,陳楠剛創意具有現代感的甲骨文字體時,曾設計過一套“甲骨文個性化電腦圖標”,也就是今天的UI設計:IE用象形的“網”字、搜索引擎是“鳥”字(意為尋覓食物);殺毒軟件是“盾”字、文件夾是“冊”字、音頻是“耳”字……“我做表情包的初衷是對文字做創意圖形解讀,這樣的話,傳播傳統文化的途徑更多樣也更接地氣。”

陳楠設計的甲骨文表情包。
陳楠覺得自己很幸運,趕上一個好時代。“擱30年前,表情包這事兒肯定做不成,技術是其次,關鍵是人們不會理解為什么要弘揚傳統文化、宣傳甲骨文。”他感慨道,“百年來,西方文明是世界的主角,記得上世紀80年代,剛剛打開國門的人們對西方文化充滿好奇,出國潮、現代藝術、西方文學、現代詩歌等都很興盛,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反而不夠關注。現在不同了,中國經濟文化迅速崛起,已經登上世界舞臺成為主角,民族自信也大大提升,所以大家對傳統文化也越來越關注,許多年輕人開始學習古琴、穿漢服、研習書法。我這個熱衷研究與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意人,真是備受時代的恩惠。”
為故宮搞文創設計
陳楠制作甲骨文表情包后,很多人誤認為他是甲骨文專家,事實上,他是視覺傳達設計專家。“每個行業都有它的基礎技藝,搞服裝的要懂面料,搞平面設計的基本功之一就是文字設計,無論是標志、海報還是網頁設計都離不開文字。”他說。

陳楠設計的“甲骨文不銹鋼鏤空模板”,可以讓兒童在描摹的同時,認識甲骨文。
身為清華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主任的陳楠,曾是北京奧運會吉祥物設計者之一,與韓美林等共同完成了福娃的設計工作,以“北京歡迎你”作為5個福娃的名字便是他的創意。其間有個小插曲,代表北方的吉祥物角色遲遲不能通過:虛構的“龍”與其他幾個真實的動物不搭;“仙鶴”脖子又太瘦長,難以設計成卡通Q版。最終,陳楠想到了北京胖乎乎的沙燕風箏,獲得通過。同年,陳楠受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的邀請參與可口可樂弧形瓶“秀我家鄉”設計大賽的策劃與評審工作,并設計了兩枚不同的高70厘米的立體弧形瓶作品,一枚選用 “福娃”形象,另一枚則用了甲骨文創意,用“日、月、山、水、鳥、魚、人、子”等甲骨文字組成文字畫,以此作為可口可樂(中國)贈送給北京奧組委的官方禮品,傳達對綠色奧運的詮釋和支持。
后來,陳楠將這些成功經驗也運用到故宮文創的研發中。“6年前,故宮還沒有真正意義的特許設計與授權管理系統,賣著像小商品市場一樣的低端紀念品,銷量完全不是臺北故宮的對手。我有幸接受故宮委托,從紀念品商店的形象與文創產品的包裝系統著手,塑造故宮的特許授權體系。”這些設計沿用至今,故宮文創已經遠遠把那些曾經的對手丟到了身后,這讓陳楠備感欣慰。
對“童心”情有獨鐘
完成過國家形象級的任務,出席過高大上的論壇,從事著為人師表的嚴肅工作,但陳楠骨子里仍是一個愛玩的“大孩子”。他的工作室里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玩具,令人誤以為闖入了玩具商店,“我想讓工作變得有趣,如果無趣的話,這件事一定有問題。”
在陳楠看來,他們那一代與長輩最大的不同就是,長輩們在年輕時就非常主動地想脫離兒童狀態,盡快成為大人,看新聞聯播與報紙,在房間里擺放屬于成人的家具、名畫、書籍并且不再看動畫片;而他們則不同,無論是在二三十歲的年紀還是將來成為六七十歲的老人,都愿意保留一部分兒童的氣象與心理。“其實簡單一句話,我的理想狀態就是將工作與娛樂合二為一。我們有權利,也愿意把童年的生活延續,這并不是長不大,而是藝術與生活結合的必然。”

陳楠設計的“卷軸手繪本”,顛覆了本子平整的傳統形式。
“愛玩”賦予了陳楠浪漫與開闊的心境,他是那種“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人。他會在晚上11點突然來了興致開車去天津,第二天清早逛兩個小時舊貨市場再返回北京繼續工作;他會在旅行中找一家咖啡館,喝著熱咖啡畫風景速寫;他會一邊手繪動畫片一邊給女兒講畫中內容;他會在廣州玩具城逛一整天淘貨……
在北京這個快節奏的城市,工作占據了陳楠的大部分時間,但讓他欣慰的是,在白天忙完工作后,晚上回到家,自己依然可以像個孩子似的仔細地涂裝、拼組心愛的玩具,打磨雕刻一塊小木雕。他的童心與玩心給他帶來了快樂,而當他把這種快樂通過自己的設計傳遞給他人時,獨樂樂便成了眾樂樂。這堆滿一屋子的“玩物”,也許便隱藏著陳楠作為一位設計師那充滿奇趣與驚喜的思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