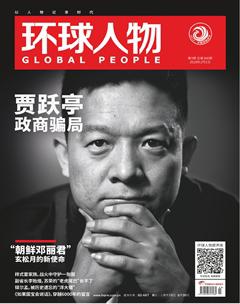劉軒:人生是一盒豆腐
王晶晶
劉軒身上,帶著多重標(biāo)簽:臺(tái)灣音樂圈酷炫的制作人,有“時(shí)尚電音之父”的稱號(hào);口才了得的主持人,4次入圍臺(tái)灣廣播金鐘獎(jiǎng),3次登上TedX的講臺(tái),還拿過大陸綜藝節(jié)目《我是演說家》的總冠軍;創(chuàng)意無限的廣告人,服務(wù)于瑪莎拉蒂、阿瑪尼等“豪門”。他瀟灑地穿梭于截然不同的領(lǐng)域,過著堪稱“花心”的人生。

而寫作則算是他“從一而終”的最愛:19歲起,他就寫出第一部作品《顫抖的大地》。這20多年來,每隔幾年,他必定會(huì)寫出點(diǎn)什么,至今已有10余部作品。
最新的書叫作《幸福的最小行動(dòng)》,“之前我寫的東西,屬于那個(gè)叛逆的年代,是在尋找自己,分享心情。但現(xiàn)在我把它整理成一個(gè)生活論,屬于有技巧、有方法、有理論的心理學(xué)書籍。”劉軒對(duì)《環(huán)球人物》記者細(xì)細(xì)解釋。
父親光環(huán)下的叛逆少年
在臺(tái)灣,《幸福的最小行動(dòng)》叫作《心理學(xué)如何幫助了我》。后一個(gè)名字,顯得很隨性,很個(gè)人主義。“因?yàn)樵谂_(tái)灣,大家都很了解我。”
劉軒的父親是大作家劉墉。這個(gè)作家父親把教育兒子的點(diǎn)滴寫成文章,出了書。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很多人說“某某家的小孩我是在朋友圈看著他長(zhǎng)大的”,劉軒就是所有人在他爸書里看著長(zhǎng)大的,說他是臺(tái)灣“最著名的兒子”,一點(diǎn)不為過。
因?yàn)檫@種熟悉感,“我可以從一個(gè)比較個(gè)人化的角度出發(fā),說心理學(xué)當(dāng)年如何幫助了我,但大陸讀者并不了解我的背景。所以我希望用一個(gè)幸福跟最小行動(dòng)的概念,明確告訴讀者這本書可以為你帶來些什么。”
對(duì)劉軒來說,成長(zhǎng)中最大的“煩惱”,應(yīng)該來自父親的陰影。他的父親不僅是暢銷書作家,知名攝影家、記者,也是藝術(shù)界很有聲望的中國(guó)畫畫家;他的母親曾是紐約圣約翰大學(xué)的入學(xué)部主任,手下管理著40多個(gè)秘書。父母的成功,對(duì)劉軒來說,是幸運(yùn),也是負(fù)擔(dān)。不知道自己要成為誰(shuí),又迫切想讓大家看到自己,他時(shí)常感到委屈,也很討厭“劉墉的兒子”這個(gè)稱呼。
從小,劉軒就被父親訓(xùn)練寫作文。出去玩都不能表現(xiàn)得太開心,否則父親就想讓他寫點(diǎn)什么記錄那美好的瞬間。22歲那年,他和父親敞開心扉。“你知道我高中時(shí)為什么那么叛逆嗎?因?yàn)槲矣X得我長(zhǎng)大了,不該什么都聽你們的。所以你叫我往左,我就偏往右。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該找到自己的位置!”父親建議他當(dāng)專職作家,他堅(jiān)決拒絕,跑去旅行、做公益,寧可把寫作當(dāng)愛好。
在跌跌撞撞中找到自己
小時(shí)候,劉軒很愛變魔術(shù)。他買來教人變魔術(shù)的書,還有一些道具,整天表演給大人看。“我覺得很酷。你明知道它不是真的,但卻可以用一個(gè)技巧讓它看起來就是真的,當(dāng)時(shí)小不理解,后來才明白這里面其實(shí)有一種心理學(xué),人都有盲點(diǎn),如果你發(fā)現(xiàn)了并善加利用人們的盲點(diǎn),就可以讓奇跡發(fā)生。”他對(duì)此好奇極了,甚至在考入茱莉亞音樂學(xué)院之后,又去哈佛讀心理學(xué)。
但心理學(xué)并沒有想象中美好。大學(xué)期間,劉軒有嚴(yán)重的拖延癥。他曾去學(xué)校的心理系圖書館借一本關(guān)于如何克服拖延癥的書,結(jié)果拖到過期沒還,被圖書館罰錢!
畢業(yè)之后,眼看其他同學(xué)都在創(chuàng)業(yè),成功也好、失敗也好,各有各的精彩,他自己似乎已與現(xiàn)實(shí)脫節(jié),在研究所里與書本為伍。在畢業(yè)5周年的同學(xué)聚會(huì)上,劉軒就在哈佛大學(xué)里住著,卻沒有參加任何活動(dòng),整天躲在房間里面,自卑得像個(gè)留級(jí)生。
第二年發(fā)生了“9·11”恐怖襲擊,劉軒加入了災(zāi)后幫人們走出創(chuàng)傷的心理咨詢團(tuán)隊(duì),結(jié)果更加受挫。他發(fā)現(xiàn)面對(duì)這樣巨大的苦難與憂傷,過去學(xué)到的理論與知識(shí),沒有一個(gè)能在當(dāng)下派上用場(chǎng)。他無法讓這些人停止憂傷,更無法讓他們重拾快樂,甚至他自己都受此影響,有了抑郁傾向。作為一名心理學(xué)博士,他去了心理門診尋求幫助。醫(yī)生是一位年輕女士,劉軒覺得應(yīng)該能談得來,一股腦把心事全倒了出來。醫(yī)生帶著憐憫的表情聽他說完,然后直接拿出了處方單:Zoloft(左洛復(fù))50mg,一天一粒。
劉軒遵照醫(yī)囑試了半年,感覺那段日子腦子里就像被蒙上了一層紗,不開心的思緒變得不重要,可開心的情緒也打了折扣。生活并沒有什么改善。他停了藥,決定徹底改變,搬回臺(tái)灣,換個(gè)環(huán)境,重頭再來。
劉軒就像換了一個(gè)人,他當(dāng)主持、玩音樂電臺(tái)、制作歌曲、做廣告,日子瀟瀟灑灑。他成了自帶光環(huán)的人,而且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去做,有什么夢(mèng)想就去實(shí)現(xiàn)。一路走來,也會(huì)時(shí)而迷惑:哪一面才是真實(shí)的自我?不惑之年的他,重新?lián)炱鹆诵睦韺W(xué)。
那樣的佛系不是佛系
哈佛此前有一個(gè)排名第一的選修課,在大陸被稱為“幸福課”。講課老師塔爾·班·哈沙爾,是劉軒當(dāng)年心理系的同學(xué)。“我們?cè)?jīng)有過幾堂課是一起上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gè)非常悶悶不樂的人。后來他有名了,自己也在書里寫以前如何悶悶不樂。他不知道為什么自己不快樂,于是去研究快樂是什么,幸福是什么,進(jìn)而得到體驗(yàn),分享給學(xué)生。”
劉軒的心理書籍也是自我的困惑和思考。2015年,他推出首部心理學(xué)作品《助你好運(yùn)》,如今又出版《幸福的最小行動(dòng)》。他說:“我的讀者應(yīng)該是二三十歲剛進(jìn)入社會(huì)、剛開始摸索的年輕人,學(xué)校的理論跟現(xiàn)實(shí)有了碰撞,產(chǎn)生了迷茫。我希望能給他們一些選擇,因?yàn)槲易约后w驗(yàn)了這么多種不同的處境,慢慢有了一些心得。”
他寫給年輕人的文字不同于雞湯,有心理學(xué)專業(yè)背景的依托——積極心理學(xué)。劉軒說自己很認(rèn)同美國(guó)心理學(xué)家馬丁·塞利格曼的學(xué)派。“過去幾十年,心理學(xué)家認(rèn)識(shí)到,心理學(xué)治療好一個(gè)人,并不代表他此后就能重新?lián)碛幸粋€(gè)正向的人生。心理學(xué)最大的成就,其實(shí)是幫助‘悲慘的人不那么悲慘。對(duì)個(gè)人來說,對(duì)社會(huì)環(huán)境來說,這就是一個(gè)正向的改變,一個(gè)良性循環(huán)。我發(fā)現(xiàn),這和我小時(shí)候變魔術(shù)一樣——讓奇跡發(fā)生在身邊。”
微調(diào),就是《幸福的最小行動(dòng)》里的核心觀念。比如,一個(gè)人想養(yǎng)成跑步的習(xí)慣,但一想到跑步那么累,就堅(jiān)持不了幾天。如果用“最小行動(dòng)概念”設(shè)定一個(gè)再簡(jiǎn)單不過的行為,簡(jiǎn)單到做不出來都對(duì)不起自己,也許就能起到一點(diǎn)幫助。劉軒建議:每天到了鍛煉時(shí)間,這個(gè)人只要穿上球鞋、系好鞋帶,走到家門口,就可以了。而奇妙的是,往往等他走到門口,就會(huì)順便走出去了。劉軒的一個(gè)朋友就是這樣,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挑戰(zhàn)馬拉松了。

2010年7月13日,劉軒(中)升格當(dāng)爸爸了,他與父親劉墉(左)、母親一起秀出小寶寶的照片,并開心地比出與照片中女嬰相同的勢(shì)。
已為人父的劉軒,不知不覺中還是被父親所影響。劉墉有一句名言:“我有一顆很熱的心、一對(duì)很冷的眼、一雙很勤的手、兩條很忙的腿和一種很自由的心情。”采訪中,劉軒也告訴《環(huán)球人物》記者:“我很難講自己是悲觀主義或者是樂觀主義,我是冷眼看真實(shí)生活,不憤世嫉俗,也不追隨他人。”
如今年輕人里流行“佛系”,在劉軒看來,“年輕人怎么可能沒有欲望、沒有夢(mèng)想,只是現(xiàn)在的變化太快,讓人很難去認(rèn)定什么。如果想要自在,還是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最怕的就是隨遇而安,什么都好。那樣的佛系不叫佛系,只是隨波逐流”。
電影《阿甘正傳》里有一句經(jīng)典臺(tái)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遠(yuǎn)不知道拿到的會(huì)是哪一種口味。在劉軒看來:人生就像一盒豆腐,好不好吃,看加什么醬料。這個(gè)醬料的選擇,來自你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