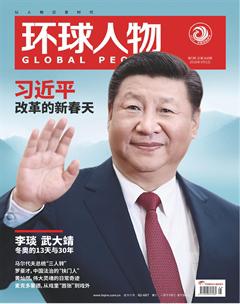鄭光先:匠人一生,珍酒一滴
肖科 大地
從2017年12月開始,《貴陽晚報》在兩個月內陸續刊發了一組共計10萬字的報道。這組報道揭秘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物資匱乏狀態下的一段“釀酒趣聞”。這件事開始于毛澤東的一句話,經過鄭光先、張支云等人10年參與,最終釀造出了一種“試制茅臺”,而這種“試制茅臺”在時任國務委員方毅的筆下有了自己的名字——“酒中珍品”,珍酒。珍酒,是國家“試制茅臺”的產物,是誕生于貴州浩瀚酒江湖的杰出代表。它的故事記錄下了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一群人的工匠精神。

上世紀70年代,參加易地試驗的原茅臺酒技術骨干。
萬噸茅臺夢從“易地試驗”開始
現代茅臺酒實際上是由“成義燒坊”“榮和燒坊”“恒興燒坊”這三家新中國成立前影響力最大的茅臺鎮老燒坊發展起來的,產量一直不高。
1958年,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把茅臺酒“搞它個10000噸”的想法,但當時茅臺酒的年產量基本維持在兩三百噸,到了1958年剛增至627噸。
1974年,“搞它個10000噸”的宏偉創想,終于被提到日程上來具體執行——“易地試制”,探索在茅臺鎮之外生產茅臺酒的可能性。這年冬天,貴州省科委提議,把“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作為“搞到10000噸”的重要措施之一。1975年《貴州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中試)》項目正式立項,并選定遵義北郊的石子鋪(現名十字鋪,今珍酒廠所在地)作為試驗基地。
但當時“文革”還沒有結束,“干革命”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哪有閑心釀酒?直到1978年,鄭光先被任命為“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項目的負責人,項目才正式啟動。早在1958年,28歲的鄭光先就已經在茅臺酒廠任黨委書記、廠長了。被“選將”調任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廠廠長、黨委書記后,他點名要當時已經是茅臺酒廠車間主任的張支云出任副廠長、總酒師,負責整個酒廠的生產,包括制曲、釀酒、包裝。
就這樣,以原茅臺酒廠廠長鄭光先、酒師張支云為首的28位技術精英,將窖石、窖泥、原料、設備等原封不動地從茅臺酒廠搬來——他們對茅臺酒,有一種信仰般的感情。

1985年,多位品酒師參加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產品鑒定會。
“試制酒”進京趕考
在一次公開活動中,時任貴州省科技廳計劃處處長的巫怒安回憶,他與“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項目負責人鄭光先在1985年9月帶著試制的最新產品,來到北京,進入中南海,拜訪了當過國家科委主任的時任國務委員方毅。
方毅聽取了他們對于“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項目的工作匯報,并支持他們在當年末舉行“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產品鑒定會”的安排。這為后來的鑒定會提供了巨大支持——當時全中國最優秀的品酒師和這個領域的科學家,都參加了這次“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產品鑒定會”。
巫怒安回憶,會見結束之后,方毅還現場喝了兩杯他們帶去的“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的試制酒,評價是兩個字:“好酒!”
1985年,是注定要載入中國白酒史冊的一年。在立項10年之后,在總酒師張支云的帶領下,經過9個周期、63個輪次試驗、3000多次分析研究,“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的試制酒終于準備好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考。
1985年10月20日,貴州省科委根據國家科委10月4日批準組織鑒定的函件和10月15日的電話通知,組織對試制酒進行鑒定。鑒定委員會由全國頂尖專家28人組成,周恒剛、曹述舜、秦京領銜。鑒定采用對照茅臺酒盲評打分的方式舉行。據鑒定委員會成員之一的巫怒安回憶,具體方法是先把酒和兩名工作人員關到一個房子里,然后通過抓鬮分別往1號杯和2號杯里倒入茅臺酒和試制酒。
據當時負責倒酒的貴州省科委辦公室副主任、鑒定委員會領導小組成員之一的陳光勝回憶,他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員被關在一間獨立的小屋里負責分酒,分好之后遞交給負責向外傳遞的一名女工作人員。為了避免評委們事先知道哪一杯是試制酒,中途還要再換一次。關在屋里的兩個倒酒人,在評委們評完之前都不準出來。那時沒手機,也沒其他通信設備,即使想作弊,也沒有辦法。
鑒定采用百分制,通過外觀、口感、回味、留香等指標,對1號酒和2號酒分別打分,然后加總求平均值。據巫怒安回憶,至少有兩位評委,給1號酒和2號酒打的分是一樣的——實在是區別不出,可能怕搞錯了丟人。
鑒定的結果是,試制酒得到了93.2分的高分,而作為對照品評鑒定的茅臺酒,最后得分是95.2分。鑒定委員會成員一致認為,試制酒在理化指標、衛生指標、新酒入庫合格率等方面均達到了合同要求。在感官指標上,鑒定委員會評酒小組品評認為,鑒定酒“色清,微黃透明,醬香突出,幽雅,酒體較醇厚……基本具有茅臺酒風格”,“盡管與市售茅臺酒仍有一定差距,但鑒定酒質量接近市售茅臺酒水平,同時有大量可靠的試驗數據及資料予以說明”。因此,鑒定委員會認為《貴州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中試)》完成了合同的要求。根據鑒定會結論,貴州省科委表示“同意鑒定意見”。
這時候,陳光勝被關在小黑屋里還沒有放出來,突然聽到樓下響起鞭炮聲,“知道鑒定成功了”,欣喜若狂,在小黑屋里拼命砸門要出來。陳光勝后來擔任過貴州省知識產權局副局長,對知識產權的理解非常深厚。這次密室分酒的經歷,亦是他“尊重知識產權”的一次歷練。
十年努力,終成正果。這個時刻成了鄭光先、張支云等人人生的一個分水嶺。特別是鄭光先,“找回了自己的生活”,這時候的他,已經55歲了。從33歲到55歲,22年的掙扎拼搏奮斗,生活終于還給了他一個圓滿的答案。

方毅題字:“酒中珍品”。
方毅題字:“酒中珍品”
鑒定成功后的1985年12月,在貴州省駐京辦事處接待處處長沈品剛的陪同下,鄭光先、巫怒安再次來到中南海。由于沈品剛已經有了方毅秘書張玉臺的電話,這一次他們走進中南海作匯報,相比第一次,方便很多。
意氣風發的兩個中年漢子,帶著鑒定完成后的試制茅臺酒,走進了方毅的辦公室。方毅品嘗了兩杯后,比上一次多說了3個字:“不錯,是好酒。”更令人驚喜的是,當巫怒安提出請方毅給試制茅臺酒寫幾個字時,方毅欣然同意了。他的評價簡單干脆,是4個大字“酒中珍品”,而題字的全文為:“祝賀貴州茅臺酒易地生產試驗鑒定成功 酒中珍品 乙丑冬日 方毅(圖章)。”
當時,試制茅臺酒在市面上以“茅藝酒”“貴酒”的名稱行銷。“茅藝酒”顯然不合適,“貴”字商標則已被別人注冊,賣的也是酒。
據當時的副廠長李永常回憶,在鄭光先的辦公室里,省科委副主任徐用武和鄭光先、巫怒安等人為試制茅臺酒的命名聚到了一起。他們想到了用方毅題寫的“酒中珍品”中的“珍酒”作為商標的創意。李永常記得,這個創意是由巫怒安首先提出的,但巫怒安“不記得這個細節了”。其實,誰提出的還重要嗎?關鍵是4個人一拍即合,當即拍板使用“珍酒”作為名字——這是個歷史性的瞬間,一個有意義的產品于這個時刻誕生。令人遺憾的是,他們沒有留下影像,甚至沒有留下日期,仿佛是1986年初,“大約在冬季”。
現在,珍酒的文字商標是“珍酒”,圖形商標則是方毅所題寫的“酒中珍品”那個“珍”字。
每一個人、每一代人的降生都是偶然,然而一個好產品的誕生是必然。正是那些智慧和勤奮的瞬間,照亮了創新與進步的道路,這正如珍酒的誕生和發展——它會是酒文明史中燦爛的一筆。
時光流轉,歲月變遷。經過近40年連續不斷地生產積累與沉淀,如今的珍酒廠,已經形成了非常適合釀造高品質醬香酒的微生物環境和場地,是少數能出品高品質醬香的酒企之一。珍酒始終堅守傳統大曲醬香白酒釀造工藝流程,堅守用陶壇貯存珍藏基酒,并創新瓶儲珍藏工藝,匠心釀造形成珍酒獨特口感,形象代表之作“珍酒·珍十五”,醬香柔雅,陳味舒適,細膩圓潤,諧調爽凈,回味悠長,空杯留香持久,飲用時甘甜爽口,飲后神清氣爽。

貴州珍酒釀酒有限公司酒廠鳥瞰圖。
未來,珍酒將繼續肩負消費者對美酒的希冀,堅守工匠精神,真心真意釀造高品質醬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