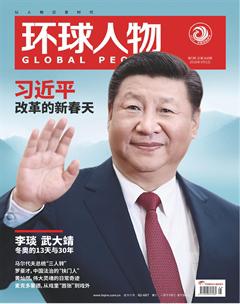商鞅的變法之道
張國剛
戰國時期,政治風云變幻莫測,這其中,各國的變法始終是最強音——魏國李悝、楚國吳起、韓國申不害、秦國商鞅都在國君支持下力行變法。若論效果,只有商鞅的變法影響深遠。它不但為秦國奠定了一統天下的政治基礎,更影響了后世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譚嗣同有言:“兩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澤東亦曾說,“百代皆行秦政制”,所謂“秦政”,指的就是商鞅變法后的新政。
兩次變法,立竿見影
商鞅本名衛鞅,出自衛國公室,最初在魏相公叔痤門下跑腿,任職中庶子(侍從官之類的職務),頗得賞識。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華,卻沒有向魏惠王推薦他,直到病重臨終時,才極力舉薦。但因為商鞅缺乏歷練,沒什么名氣,魏惠王沒打算用他。公叔痤于是發狠話說:“不用之,即殺之,為了魏國的國家安全,也不能讓商鞅到其他國家去。”沒想到魏惠王還是懶得理他。公叔痤死后,商鞅沒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發布《求賢令》,廣招人才,商鞅于是來到秦國。

商鞅(約公元前395年一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秦國政治家、改革家。
商鞅入秦后,其變法主張與秦孝公不謀而合,因此深得圣心。秦孝公安排他與國內保守派官員辯論變法利弊,一連好幾天,商鞅都沒能說服保守派,但辯論的過程卻進一步堅定了秦孝公變法的決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第一套改革政令。首先,他建立起一套基層什伍組織,制定了一套治安聯保制度,“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這實際上是對當時的社會基層管理體制的完善。其次,他制定了獎勵耕戰的激勵制度,“為國征戰,立功受獎;戮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經商或懶惰而致貧者,官府沒收為奴”。他還規定,“宗室若無軍功,不得列為貴族;普通民眾立軍功可以得到榮華富貴”。可見,這種激勵機制不僅有明顯的經濟與產業導向——重農抑商;還打通了平民通向貴族的通道,限制了宗室貴族的特權。
到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推出新一輪改革措施。一是進一步推廣縣制:與屬于封君的封邑不同,縣直屬中央政府,每個縣都設縣令、縣丞。二是廢除井田制: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制度,周王把土地分封給諸侯,庶民為其耕種,土地的產權不得轉讓,而廢除井田制后,民眾可以買賣土地,勞動積極性大大提升。三是頒布統一的度量衡標準:方便了各地物品的相互流通,也有利于各地方之間的交流,促進了經濟發展。
商鞅變法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史記·商君列傳》記載:“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法律有尊嚴,改革才成功
當然,之所以效果明顯,也因其特點明顯。
為了變法成功,商鞅首先注意建立法令的信譽,“徙木立信”就是一個例子。他命人貼出告示說,如果有人能將立在南門的木頭搬到北門,就可得到賞金十鎰(音同義,古代重量單位,一鎰為二十兩)。當時,十鎰金相當于一個普通人家的全部財產,百姓議論紛紛,不敢相信是真的。商鞅又把賞金加到五十鎰金。終于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了過去,商鞅兌現獎金,由此,百姓確信政府的法度可信。這一觀念得到強化后,商鞅才開始頒布改革法令。
法令既頒,嚴明賞罰就是成敗的關鍵。太子駟在貴族的鼓動下犯了法。商鞅認為,太子是嗣君,不能對他施加刑罰,但是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要為此承擔責任,便將他們分別處以割鼻、臉上刺字的刑罰。高官違法,同樣處置;庶民有功,兌現獎賞。法律有尊嚴,改革就能成功。
商鞅改革的政治原則是“尊君”和“平民”。“尊君”,即認為君主有至高無上的權威,要絕對遵從,這樣才能構建不容挑戰的社會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會結構,即王權之外的一切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榮譽對所有的民眾開放。普通士兵若有軍功,百姓若有才能,都可以獲得政府職位。同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一斷于法”的法治第一主義,否定了貴族血統的特權,也要求君主“以法治國”。平民主義、法治主義與君主獨尊相輔相成,對于秦漢以后中央集權制度的發展與強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商鞅變法不僅講求原則,還有著詳盡的實施細則,有很強的可操作性。以獎勵農耕而論,法律對于播種時下種的數量都有詳盡的規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種稻,每畝用種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麥子每畝一斗;黍米每畝三分之二斗;叔(同菽,即大豆)每畝半斗”。法律還規定,地方政府要定期向中央詳細匯報農作物的生長情況,包括受雨分數、抽穗的田畝數、水旱之災等。牛是農耕之本,秦國每季舉行一次耕牛健康評比會,優勝者有賞,低劣者受罰。如果耕牛的腰圍瘦了,主事者將獲鞭笞之刑。政府用法律指導農民種田、養牛,以保障先進農業技術得到推廣,令人嘆為觀止。
在軍功授爵制度方面,商鞅將爵位與戰績掛鉤,內容非常細致:士兵斬獲一個敵人首級,就可獲得爵位一級,田宅一區,仆從數人;斬獲兩個首級,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在軍隊生活中,還有更具體的規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三級爵位士兵的伙食標準是每天精米一斗,醬半升,菜、羹各一盤;兩級爵位的士兵只能吃粗米;沒有爵位的大約僅能填飽肚子。
商鞅變法與梭倫改革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是為秦惠王。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舉報商鞅謀反,商鞅因此被殺,尸體被車裂。對于商鞅之死,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
第一,他能否逃脫被追殺的命運?
秦國的統一大業發軔于商鞅變法,商鞅的貢獻無可置疑。但改革必然會得罪既得利益者。與沉默的大多數相比,被損害了既得利益的貴族群體具有更大的反對改革的動力,以及針對改革者本人的反撲能量。加上商鞅本人有行事霸道的瑕疵:法令推行后,有人對新法先是抵觸后又轉為贊揚,而商鞅把這些人盡數發配邊疆。這種鉗制輿論的做法,自然不得民心。
公元前341年,齊魏馬陵之戰后,魏國損失十萬大軍。商鞅欺騙公叔痤門下舊交公子卬,致使秦國對魏不戰而勝,收復了西河之地。不擇手段的行為對他的“國際形象與聲譽”造成損害。
作為“空降兵”的客卿,商鞅既侵害了本國既得利益集團,又在“國際上”陷于孤立,必然難逃悲劇的命運。
第二,處死商鞅的秦惠王,為何沒有廢除商鞅制定的法律?
首先是法令確實推動了秦國的發展,有利于富國強兵;其次,變法中的許多內容在秦獻公(公元前424年—公元前362年)時期已實行,重視農耕和軍事防御等思想也為秦國王室所熟悉。在秦人看來,秦孝公才是變法發起者,商鞅只是孝公意志的堅定執行者,甚至是具有創造精神的執行者。
關于商鞅改革的實質,可以將之與古希臘城邦改革做比較。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4世紀,雅典是古希臘境內最強大的城邦(一個城邦就是一個國家)。公元前594年,梭倫在雅典實行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權力制衡,鼓勵工商業發展。梭倫改革中,按一年農產品收入的總量把公民分為4個等級,各等級的政治權利依其財力之大小而定。例如,一等公民可任執政官等重要公職,而四等公民一般不擔任公職,最多充當陪審員。
同樣是打破貴族血統,梭倫改革突出的是按財富劃分社會等級,商鞅改革則是按照軍功劃分政治地位。前者承認并鼓勵私人創造財富,后者引導國民埋首農田或撲向戰場。商鞅變法之后,很多平民開始走向政治道路,張儀、范雎、呂不韋、李斯等來自他國的“移民”躋身卿相。在這一點上,商鞅變法比梭倫的改革更徹底。但這種平民化的政治,使王權變得不可挑戰。而社會層級的過度平面化,也只有通過不斷強化君主權威,才能阻遏混亂,維護社會秩序。
可見東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異,一是產業方面:地處關隴的秦國以農業為主兼及畜牧業,而雅典瀕臨海洋,以工商業立國,因此兩國對各自產業的發展思路不同,激勵重點不同;二是民眾與人口方面:秦國的百姓多是父祖相傳,而雅典居民多是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移民。公元前500年,雅典人口約為20萬,秦國人口有四五百萬。誠如孟德斯鳩所言,小城邦容易實行民主制;人口眾多的國家則多實行君主制。
無可否認,梭倫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商鞅變法則影響了此后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