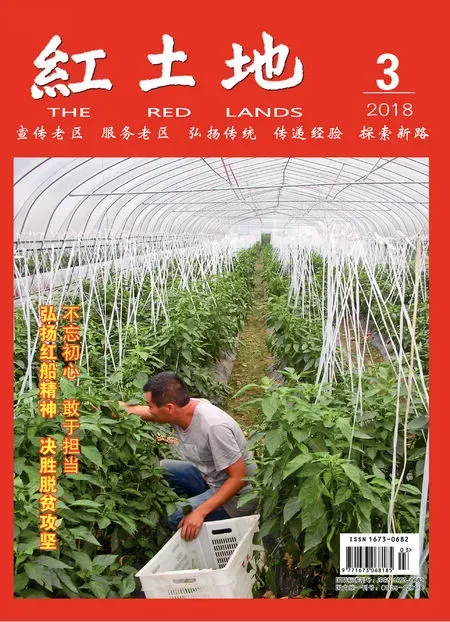閩西黃花香
黃鎮坤

毛澤東舊居臨江樓(圖片來自網絡)
國有國花,市有市花。那么,如果要選出一種最能代表閩西這塊土地上獨具特色形象和內涵的花卉,你會選哪一種呢?山茶花?蘭花?三角梅……
依我看,菊花最契合了。
雋美多姿,不以嬌艷姿色取媚,而以素雅堅貞取勝的菊花是中國十大名花之一。一直以來,作為傲霜斗雪之花的菊花總為國人所愛。國人賦予它高尚堅強的情操,并以民族精神的象征被視為國萃。梅蘭竹菊——中國文人還把菊花看作“四君子”之一,以菊明志,比擬自己的高潔情操。歷代的文人墨客,甚至唐末農民起義領袖黃巢把菊花寫進了詩詞歌賦里,傳誦千古。毛澤東也把菊花寫進了他的一首詞里,而且就在閩西這塊土地上寫就。
1929年10月初,毛澤東來到上杭——這是他第四次來到這里,住在臨江樓二樓的東廂房里。翌日,恰逢農歷重陽節。清晨,臨江樓庭院里點點黃花盛開,心情沉重的毛澤東佇立臨江樓上,迎著深秋的勁風,心潮澎湃,于是,寫下《采桑子·重陽》這首詞: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詞中的黃花就是黃菊花。
詩言志,歌詠言。毛澤東是在怎樣的情境里寫下這首詞的呢?
1929年6月22日,在閩西龍巖召開了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被黨內的幾位同志批評搞“家長制”,因此在選舉前委書記時,他落選了。之后,毛澤東不得不離開紅軍,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隨后,毛澤東患上惡性瘧疾,病情一天天加重,全身浮腫,幾次徘徊在生死邊緣。他只得從上杭蛟洋轉移到蘇家坡,再轉移到永定縣金豐山區等地,一邊養病,一邊指導地方工作。當年10月初,幾個赤衛隊員用擔架抬著他,又從永定來到上杭縣城。可以說,《采桑子·重陽》是在他歷經磨難后心力交瘁之時所作的一首不可多得的詞。
白居易有詩云:“愛菊高人吟逸韻,悲秋病客感衰懷”——對于一般的文人墨客來說,在他們眼里,菊花多半是東籬秋叢或庭院盆景的小花小草,面對菊花,他們能做到的更多是“吟逸韻”“感衰懷”。可偉人畢竟是偉人,他不似一般的文人墨客,他在詞中雖然也反映了病中的心情,但更多的是從大處著眼,從人生感悟落筆,擺脫了個人的榮辱得失,站在歷史的、人類的、宇宙的高度抒發一個革命者的壯志豪情。他把“黃花”與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聯系在一起。面對經過硝煙炮火洗禮卻依然在秋風寒霜中綻放吐芳的菊花,偉人是懷著欣悅之情來品味的。黃花裝點了戰地的重陽,重陽的戰地顯得更美麗。“戰地黃花分外香”“分外香”寫出了偉人當時的感受。這首詞有情有景,有色有香,融詩情、畫意、野趣、哲理于一體,構成生機盎然的詩境,既歌頌了土地革命戰爭,又顯示了作者詩人兼戰士豪邁曠放的情懷。盡管時光易逝、“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戰斗、戰場、解放全人類的崇高事業聯系在一起的,他們不嘆老懷悲,蹉跎歲月,而是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為革命而戰,一息尚存,奮斗不止……詩人在詞里營造了一個恢弘開闊的藝術境界,使人讀后,毫無肅殺之感,反而受到無限鼓舞。
因了毛澤東的這首詞,我更喜歡菊花了;因了這首詞,菊花與閩西這塊紅土地聯系得更緊密了。
說起菊花,種類繁多,單是顏色,就有紅、白、紫、粉、橙、黃……無論哪一種,都好看。在閩西大地上,最常見的菊花就是黃色的野菊花。這種野菊花除了被一些有心人種在庭院或陽臺上供人觀賞外,更多的是長在田間地頭、荒郊野地里,在那兒寂寞著、自生自滅著。我的鄉人稱之為“田頭菊”,是一種非常接地氣的花。把野菊花與毛澤東詞里的“戰地”聯系起來,容易讓人聯想到為歷次革命戰爭建功立業甚至犧牲的無數閩西籍子弟兵,他們就像這野菊花一樣,大多來自鄉野山村,踴躍地走進革命隊伍,又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散落在革命隊伍的各個“角落”,像野菊花一樣用青春熱血綻放在各戰場上……
閩西是一塊紅土地,是革命老區,是紅軍之鄉,是將軍之搖籃。這兒也是一塊溫潤的土地,春夏時節,菊花草青綠著;秋天,菊花點點開放;到了冬天,點點菊花仍閃耀著、芳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