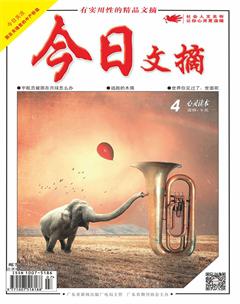挑刺
豐方
狗年開春,一幅狗狗和小女孩的圖畫,令我注目良久,思緒翻飛,繼而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我沒去考究畫的來龍去脈,更沒有打探作者姓甚名誰。我妄自為其命名——《挑刺》。
思緒帶我回到1966年。春節后不久的新學期,中山大學搞教育改革試點,六五級的文史哲學生北上到粵北山區坪石建分校。諸事未備,第一階段分散到四鄉與貧下中農“三同”,接受艱苦生活煅煉,行革命青春的洗禮。
我們這個小班,被分到一個長期吃救濟糧的生產隊。那是武江江面上一個石山小島,島上草木稀疏,打柴割草都需涉水到對岸山嶺,十幾戶人家變無可変,遷無可遷,僅靠些薄田過日子。
“三同戶”朱大叔,五十開外,妻亡故,大女兒早早遠嫁,同八歲小女相依為命。大叔多病纏身,長期缺糧,雙腳黃腫。幸好生產隊安排他擺渡,又常有搭客舍他些許魚蝦,勉強撐持著。
小女孩命苦,三歲喪母靠父親和鄰居拉扯大。身形嬌小,面黃肌瘦。女孩家貧未上學,但生性聰慧,天真無愁。我們這十個八個大哥哥大姐姐的到來,打開了她的生活視野,從鄰居我的同學處,她借到小人書,立地捧看,自看自笑。在我班女同學這些大姐姐那里,她學扎小辮子,大姐姐們有時還給她插朵小花。
小女孩懂事,打小就學會飼養葵鼠幫補家用,每天都上山割飼草、挖野菜、拾枯樹枝,風雨無阻。她家窮,沒有媽媽做鞋,無論上山還是在家,終日都打赤腳。自小艱辛生活磨煉,女孩不識憂愁,雖說練就一副鐵腳板,人畢竟是血肉之軀,常見她捧腳挑刺,一如這幅狗年見的彩圖,痛時呲牙裂嘴,讓我不忍卒看。對小女孩的同情、喜歡、甚至佩服,讓我更深刻理解生活的艱辛不易。她從山上采到的野蘑菇常帶蟲,我不挑剔,閉上眼睛把蟲子當肉吃了。那時提倡到群眾中去“滾一身泥巴,踩兩腳牛屎”,我把蟲子吃肚里,算是潛移然化的世界觀改造成果。
小女孩良善,哪家大人外出,找她看管小孩,甚至喂雞、喂豬等雞零狗碎,她從不推托而樂于幫忙。也因此她的人緣很好,甚至同鄰居家的狗狗混熟了,形影不離。
“三同”也真能煅煉人,第一關就是饑餓。“三同戶”家是沒有午飯的,這對我來說就更嚴峻。記得那一次,我們爬山送農家肥下地,肚中無食饑餓難忍,五步一歇、十步一停。恰遇我家小姑娘也上山,她硬是把(可能是鄰居剛送她的)一塊紅薯干塞給我,我當時的窘迫、羞愧、感激,就是現在,都難以再言。
一月艱苦的“三同”過去,我們回到坪石鎮新修葺的簡陋校舍。飽食安眠,躺在木樓板上就寢,心中常戚戚,三同戶父女倆的艱辛讓我心里不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時起就思考社會問題。后來,五六月,一紙《通知》下發,我們匆匆卷鋪南返廣州,行前竟無法過江去見一見這父女倆一面。
若干年后,我和幾位同班學友重返坪石,再尋“三同戶”,遺憾的是,我家的朱大叔早離人世,我家的小姑娘遠嫁難覓。
我很后悔,雖然我只是個領助學金的窮學生,當年怎不去多買兩瓶大叔喜歡的樂昌燒酒?我更后悔,小姑娘的光腳丫從未穿過鞋,怎么就沒想到給她添雙鞋子。
又過去多少年了,“我家小姑娘”始終是我的一塊心病,猶如心頭一根刺。不過我常想,她能遠嫁,說明她在文革的苦難中成人了。而我也堅信,以她的聰明伶俐,以她的勤勞堅韌,以她的厚道和善解人意和豁達樂天,她定會經營出一個美滿的家,一番富足的生活。
朋友,也許,您會與我有同感,《挑刺》這幅畫,訴說著孩子的艱辛,也表現了孩子的不屈與堅韌;在今天這樣美好的藍天下,絕大多數孩子都穿上了鞋子,他們的家庭也過上小康生活。但是,生活中,仍然還有“挑刺”的光腳孩子,受困于貧簍落后艱難荊棘。這艱難困頓是我們國家的一根刺,民族的一根刺,不把這根刺挑出來,無法談國家強盛民族復興。
2018年是扶貧關鍵年,習主席發出了“言必正,行必果”的攻堅號令。但愿在脫貧攻堅的猛錘下,砸碎人民致富道上的障礙石,迎接國家民族的美好明天!
責編: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