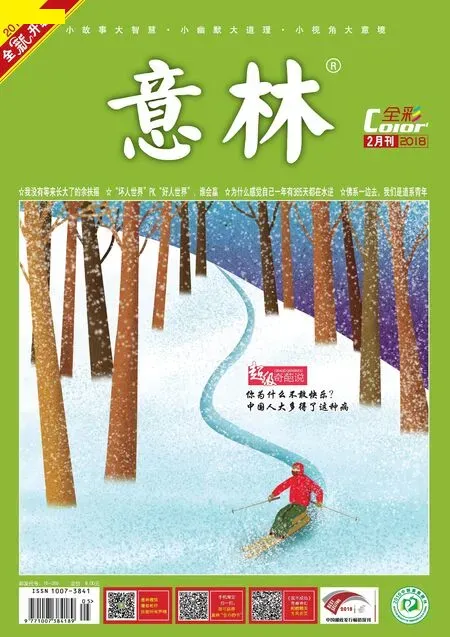共享好時光
□鐵 凝

我記事以來的第一個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鄰居,我叫她大榮姨。
那時候我三歲,生活在北京。大榮姨是個中學生,有一張圓臉,兩只細長的眼睛,鼻梁兩側生些雀斑。我不討厭她,她也特別喜歡我,經常在中午來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覺,同時還給我講些啰唆而又漫長的故事,也不顧我是否聽得懂。念小學以后我隨父母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榮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們。
小學二年級的暑假里,我和奶奶去她家時,見她正坐在一只馬扎上編網兜,用紅色透明的玻璃絲。她問我喜歡不喜歡這種網兜,并告訴我,這是專門裝語錄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為語錄本編織小網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開會,很帥,正時興呢。
我請大榮姨立刻給我編一個小網兜,大榮姨卻說編完手下這個才能給我編,因為手下這個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環(huán)顧四周,這才發(fā)現(xiàn)在不遠處的一把椅子上,坐著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大榮姨手中的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這使我有點別扭。不知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這個女孩子面前顯示我和大榮姨之間的親密,用現(xiàn)在的話講,就是顯示我們的“夠哥兒們”。我說:“先給我編吧。”“那可不行。”大榮姨頭也不抬。
“為什么不行?”
“因為別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還是我的大榮姨呢。”
“所以不能先給你編。”
“就得先給我編。”我口氣強硬起來,心里卻忽然有些沉不住氣。大榮姨也有點冒火的樣子,又說了一個“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兒了。
第二天早晨,當我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枕邊有一只嶄新的玻璃絲網兜,那網兜的大小,恰好可裝一本64開的《毛主席語錄》。保姆奶奶告訴我,這是大榮姨連夜給我編的,早晨送過來就上班去了。
那么,我是大榮姨的“自家人”了,我們是朋友。因為是朋友,她才會斷然拒絕我那“走后門”式的請求。
我把那只小網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時。雖然因為地理位置,因為局勢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榮姨見過面,但我們共度的美好時光卻使我難以忘懷。
打那以后,直至我長大成人,便總是有意躲避那些內容空洞的“親熱”和形態(tài)夸張的“友好”。每每覺得,很多人在這親密的外殼中疲憊不堪地勞累著,你敢于為了說一個真實的“不”而去破壞這狀態(tài)嗎?在人們小心翼翼的疲憊中,遠離我們而去的,恰是友誼的真諦。
一位詩人告訴我,當你去別人家做客時,給你擺出糖果的若是朋友,為你端上一杯白開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開水的清淡和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間無所旁顧地共享好時光。
每當我結識一個新朋友,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賣醬油的大榮姨和那一對北歐的姑嫂,只覺得能夠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絕和真切的清淡,實在是人生一種美妙的時光。
- 意林·全彩Color的其它文章
- 規(guī)矩的邊界
- 梅塢尋茶
- 意粉求上墻
- 調查小問卷
- 測試你患了哪種年底焦慮癥
- 編內編外大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