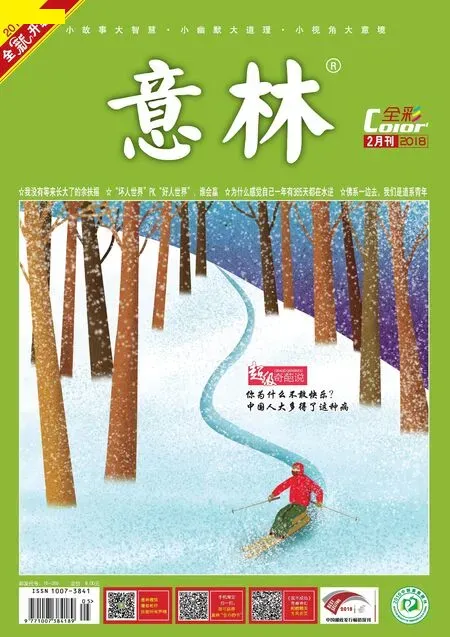狗葡萄
□照日格圖

十歲之前,我并不知道葡萄還可以長那么大。我對葡萄的印象,完全來自一種叫龍葵的小野果。因為這種野果有一個我們早已叫慣了的蒙古語名字:狗葡萄。大概是因為它雖然形似紫葡萄,卻比紫葡萄黑很多,又不像葡萄那樣有專人為它支架,梳理每一條藤蔓的走向,如若遇到好的主人還可以給它施肥澆水,百般呵護。
狗葡萄沒有這種命,只要雨水充足,院子、田地、溝邊、屋后都是它的家鄉。
手和嘴巴寂寞相交的時候,我們幾個坐在屋檐下聊天的孩子就會從身邊采幾顆綠綠的狗葡萄扔進嘴里。扔進嘴里也不會急著嚼、急著吞,我們把它放嘴里不為吃,只是為了緩解來自嘴巴和手的寂寞。綠色的狗葡萄在我們的嘴里被呼來喚去,變得和嘴里的味道一樣時我們就把它吐出來,繼續聊我們的天。
狗葡萄是野路子,從結果子到成熟也不按照套路出牌。一株狗葡萄的枝枝葉葉間,總有幾顆小果子還沒來得及成熟,那是它不想讓我們看到自己成熟的一面,看上去還綠綠的,用手一摸才知道背著太陽的那一半已開始變黑。狗葡萄這樣羞澀的性格倒是不太像野果。那些平時對狗葡萄不理不睬的麻雀和喜鵲此時早已搶在我們前面,最大最甜、果汁最多的幾個早被它們吃完了,吃完它們就飛走了。于是,我們還要等待余下的綠果子快點成熟。
臨近開學,我們的作業壓力也越來越重,沒有幾天清閑的日子了。最忙的時候,我們派一個小伙伴守著那株狗葡萄,好讓它在最好吃的時候落入我們的嘴里。
除了守住陣地,我們也積極探索新的領地。哪里長了一株狗葡萄,哪里就是我們的陣地,等我們幾個每人都有一株狗葡萄時,一切就像蘇木里的秋天一樣安靜了。在一個陽光依然灼熱的下午,我在一個自認為偏僻的地方小解后,突然發現那里長了好多株狗葡萄。趁大人不注意從家里拿一個玻璃杯出來,把自己認為成色最好的狗葡萄摘了放進玻璃杯里,直到再也放不下。我就像在品一杯葡萄酒,拿著一杯狗葡萄舉杯。在陽光的幫助下,一杯成熟的狗葡萄和一杯紅酒還真有幾分相似。我卻忘記了喝紅酒時的優雅,頭一仰,把狗葡萄灌進嘴里,滿足地嚼幾下再咽下去。吃上兩杯,就再也吃不動了。接著,我才呼朋引伴,告訴他們我發現了一個足以讓他們興奮好幾天的“寶藏”。
后來我去旗里上學,再去市里,又到首府求學和工作,吃了包括紫葡萄、馬奶提子等在內的不少水果,總覺得那個顆粒小、顏色烏黑的狗葡萄比現在的任何一種葡萄都好吃。
或許,只有我們叫它狗葡萄,而它本身可能并不是葡萄家族的一員。物品的名稱和實質有時會有很大的差別,就像我每次回家,親戚們都喜歡說我是城里人。其實,到現在我也不曾適應自己生活了15 年的這座城市,在這里我經常迷路,偶爾迷茫。當我暫時離開這里回到草原,聞到混合著牛糞味兒的草香時心境才能回到孩提時代,回到兒時的草原。
前幾天,我下班后步行回家,在路邊看到了一株狗葡萄,它還沒有開花。我在它的周圍找了半天,也沒找到第二株狗葡萄。狗葡萄的種子一定是在某一只鳥兒的腹內生活了一天半天,才“移民”到城里來的吧。一株狗葡萄孤單的狀態竟然有點像現在的我。
長大之后,我也被一只神奇的鳥兒帶到城市里,過上了沒有兒時伙伴的生活。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經常聽見他們在呼喚我,叫我回去尋找一株狗葡萄背后的童年。
狗葡萄沒有葡萄架,所以一直在我們觸手可及的地方,而家鄉呢,我一直將它放在心里,卻一天天地聆聽著她漸行漸遠的腳步聲。
現在的我需要那么一個下午,陽光依然強烈,我手里拿著玻璃杯,里面裝滿了兒時的狗葡萄。我舉起杯,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