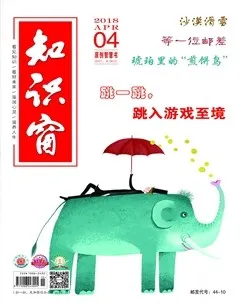我曾“歸逸”茶山中
宗家拙
某次外出旅游,我的住所在一片茶山里,它的訂房鏈接躺在住宿網站乏人問津的角落里,歷史記錄顯示,只有二十多人曾光顧過它。或許因為顧客少,縱使這間民宿的名字——“歸逸”頗不流俗,它卻依然十分廉價,而我恰恰是因廉價訂了這里。
由于飛機晚點,我到住宿地所在的茶山時,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了車,我伴著道路兩旁的路燈和隱約可見的茶樹走了百十來米,便看到了前方的“歸逸”。“歸逸”是一座中式別墅,與眾不同的是,它如一顆珍珠般嵌在微微陡峭的半山腰上,隱映在一片郁郁蔥蔥的茶樹中。就著月色和沙沙的晚風聲,白墻青瓦的“歸逸”靜謐安詳。“歸逸”門前有個站得筆直的年輕人,他身材高大,穿著亞麻質地的白色短褐,襯著瑩白的燈火和月光,竟有些出塵的韻味。看到我來了,他踏著如水般的月色走來,微笑著接過我沉重的旅行包,迎我進了“歸逸”,和善熱絡得仿佛舊友。
迎接我的此人正是房主,因名字中有個“士”字,又長我幾歲,我便叫他士哥。原來,士哥根據我告知的航班信息推測出了我來的大致時間,又怕我找不到路,便站在別墅的路口等我。隨他進了“歸逸”,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客廳兩面墻的書架,密密麻麻放置了好些書。粗略看去,有古典文獻、西方哲學、世界歷史……甚至還有商學和社會學的著作。我忍不住贊嘆,士哥卻不以為意,笑著引我走上了二樓,說完住宿的事項便離開了。
我的房間是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臥室。臥室中有兩面窗戶,一面是竹桌正對的木窗,此時木窗未合上,微風拂過桌上的池坊流插花,搖曳的花枝抖落一桌月色。另一面窗戶則是一整面落地窗,坐落在矮棋盤和蒲團邊。透過窗望去,頭上的月光、面前的山色、遠處的溪流皆入眼底,有此三者相伴,這一晚想必不會孤單了。
第二天,當我睡足走下樓時,發現客廳早已擺好了早餐。士哥早已用過飯,見我在餐桌落座,便準備泡茶。等我差不多吃好了,他便招呼我過去喝一杯茶。他還開玩笑,說是以茶代酒,祝我今天旅行順利。
“歸逸”離鬧市區其實并不遠,我順著茶山間的路走了約莫10分鐘,便到了茶區和市區的交界處,繁華由此映入眼簾。回頭一看,“歸逸”也不知何時兀自隱在了山中,我竟看不到了。可眼前的繁華實在是太吸引人,我未多想,興奮地尋了處熱鬧便投身其中。所以再次闖入“歸逸”時,已然夕陽西斜,我背了滿包零食,兩手拎滿了五顏六色的綢緞禮盒,腋下還夾著把印著某景區標志的油紙傘——這些都是我當天的“戰利品”。
我進入客廳一轉頭,發現士哥正在彈琴。見我回來了,他便招呼我坐過去聽琴。他彈著琴,沒說話,我便更不好意思發聲,摩挲著手中的綢緞,沒來由地有些不好意思。琴彈畢,他笑著調侃我今天收獲頗豐,我也不自覺地被他感染,笑著接話。聊著聊著,便聊到他在此地建別墅的原因。士哥曾在北京的大學讀金融,后來到了美國留學,畢業后進了大摩總部,用五年時間成了中層管理。可由此而來的壓抑卻快將他拖垮,于是一次大病之后,他徹底看開,隨后辭職回國,建了這座山間別墅。如今的他每天彈琴、泡茶、讀書,有了感觸便隨手記下,現在已經出版了數本作品。偶爾興起時,他便關了別墅,去別處做旅行義工。我聽著他娓娓道來的故事有些失神,只覺得他的那身短褐太無暇、太沉甸,我手中的那些絲綢太斑斕、太輕薄。
我是在第三天早上離開“歸逸”的。說他送我到門口時,我打趣他,說他是與眾不同的妙人,要不要送我點獨一無二的東西作紀念。他想了想,隨即笑著欠身,摘了茶樹上一片葉子給我。我握著那片葉子,一步步走向前方的大道,一步步走向川流不息的人潮,一步步看著“歸逸”越來越小,終于在一個拐彎過后消失不見。
“歸逸”離鬧市區其實并不遠,只是鬧市的人們看不到它,而它也未曾祈求過別人的垂青。只有那些偶然憑借機緣的碌碌過客,方有機會一窺它的風姿。至于一手打造出“歸逸”的那個人,多年過去,他的樣貌我有些記不清了,只記得他的名字中的那個“士”字。
士大夫的“士”。